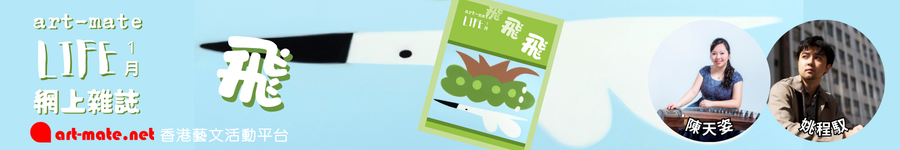有時我覺得自己像是博物館裡的工作人員,三不五時把先聖先賢大師們的頭像拿出來,撢掉上面的灰塵,讓它看起來光鮮亮麗,有時在晚上當指揮舞動起他的指揮棒,鋼琴家舞動起他的十指,頓時就像施展起招魂術,先聖先賢們突然活了過來,魔法般地再次指引我們奏出那些經奏過、聽過千百次的樂音,有時好像真的活了過來,有時則半死不活。
有次陪著一位高齡九十、舉世知名的鋼琴家去金門演出,搭飛機回來的路上我們兩個人變成了無話不談的麻吉,一會兒聊到艾瑪.史耐德(Alma Schindler,1879-1964)(編按),因為他那時候有一陣子待在紐約,他說他認識她,他認為她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我心想,就我所看過艾瑪一九五○年代的照片來說,他的評語似乎有點眼光獨特,他再三跟我保證說她超越年歲與外在形體容貌,乃是至高靈性所流露出的無比美感,我則是滿心好奇想打聽說,不知道她有什麼關於她兩位前夫的軼事,可以讓我八卦一下這位我衷心喜愛的作曲家,或是那位建築大師,接觸到他們身為人類的人性那一面。
古典音樂 = 古人的音樂?
我們的話題一轉,接著聊到了一位這幾年紅透半天邊的超級中國男鋼琴家,因為這是一個很獨特的音樂現象,掀起古典音樂界陣陣旋風,我提起我曾經拿這問題就教於一位知名俄國女鋼琴家時,她很巧妙地回答說,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想看看因為他的緣故,中國不知多了多少渴望學習鋼琴的年輕人,這對於現今學音樂人口愈來愈少的全球趨勢而言,這真是不錯的好事。
老鋼琴家則提到有次他人在巴黎,剛好這位鋼琴家要在巴黎演出,知道他人在巴黎,特別過來看他,並且邀請他去聽演出。我追問說:結果你有去嗎?老鋼琴家停頓了短短一陣子,低聲回答說:「我沒有去,因為我覺得這位鋼琴家比較在乎他自己,而不是他所彈奏的音樂。」
有次在做某場交響樂團音樂會的海報時,我跟平面設計師溝通後,決定把曲目裡的兩位作曲家上半身像左右對峙當作主要背景,以單色處理,然後把指揮與演奏者較小的彩色照片壓在上面,讓他們跳出來的同時,也直接帶出主要的曲目。獨奏家來了之後跟我說,他的朋友在說怎麼海報上看不到他的照片,我跟他說明設計構想,他說:「音樂會應該賣的是活人,而不是死掉的人吧?」這答案會讓我想會想起某個小學生回答我的問題——「為什麼這叫古典音樂」的回答:「因為作曲家都作古了,所以叫做古典音樂」。
用指揮棒施展「招魂術」
有時我覺得自己像是博物館裡的工作人員,三不五時把先聖先賢大師們的頭像拿出來,撢掉上面的灰塵,讓它看起來光鮮亮麗,有時在晚上當指揮舞動起他的指揮棒,鋼琴家舞動起他的十指,頓時就像施展起招魂術,先聖先賢們突然活了過來,魔法般地再次指引我們奏出那些經奏過、聽過千百次的樂音,有時好像真的活了過來,有時則半死不活。然而當指揮棒停止舞動後,他們的魂魄就消散並再次逝去,只留下頭像站立在博物館裡,直到下一次有人動起十指或是揮舞起雙手,他們才會再次被召喚而復活,其後他們又將再次死去。這反覆再三、一次又一次的生生死死,難道不會讓音樂家們或聽眾們疲乏?難道這就是「永恆」?
存在並不表示就是活著,況且現今我們都可以在數位世界的亂葬崗裡永存,永恆也往往只是令個人終生難忘的感動片刻;或許該像楊納傑克的歌劇《馬可波羅秘方》裡的女主角Emilia Marty一樣,領悟到永生使她喪失了人類的真情,最後決定不再服食秘方,坦然接受死亡。
推廣的重點不在於數字
古典音樂會死嗎?看來似乎一時三刻不至於,不過百足之蟲正在老化、僵化,需要蛻變重生。然而,新血未必是把古典鋼琴家當作rock star來行銷與崇拜,也不見得是以show biz的理念來經營它。數字不是這世界的全部,市場機制更不是價值體系,推廣的重點不在於數字,而是在這愈發娛樂化、商業化、市場化、物質化的新世界秩序中,以亙古樂音為我們帶來反省,啟迪人心,再次述說現已幽微的古訓——「人生追求的是真、善、美」。
金錢、物質、聲名是手段,而不是這追求的最終目標;「我們都是宇宙過客;藝術家當是神諭的解謎者,造物者卑微的僕人」!
編按:曾是作曲家馬勒、建築師格羅佩斯的妻子。
文字|陳樹熙 熱愛飛行卻又不太會降落,矛盾但真誠,好奇又武斷,希冀引起您微笑並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