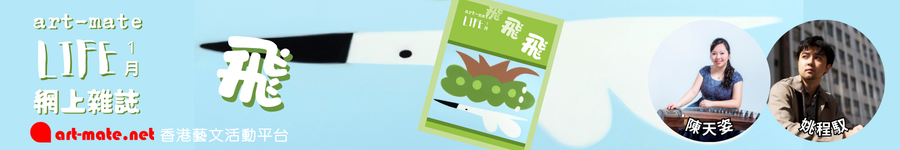在处理地方纹理的剧场制作中,剧场创作者与在地环境、文史、住民的互动关系是多样的,地方纹理不是铁板一块,它或被改造以融入剧场,或与剧场发生协商关系得以对话,甚至也可能被完全架空、挑战,重新赋予新的叙事。在这样的过程中,剧场的生命与地方的生命,也因此有了平实的交会与生发。
美国戏剧理论家理查.谢喜纳(Richard Schechner)在构作「环境剧场」(Environmental Theater)一词时,提出两种剧场理解环境的方式:改造与接受。在改造的情况下,人们「改变一个空间来『创造』一个环境」;在接受的的情境中,「人们与一个环境『协商』,与一个空间进行一种布景对话。」(注1)虽然谢喜纳的理论对象主要为真实地理空间,但从他出发,我们亦能试图从类似的区分方式,掌握一种思考地方纹理如何出现在剧场制作中的切面,换言之,地方纹理是得到改造以融入剧场,或是剧场与地方纹理间发生协商关系,而得以彼此对话;两者不是差异之分,有时可能更接近光谱两侧的程度之别。
沿这条理路前进,值得注意的是,对谢喜纳来说,无论改造还是接受的互动方式,在环境剧场中都不存在一种纯粹、透明的空间,因为它们已在与剧场的互动中成为「环境」,这意味——套句谢喜纳的话——它们都成为「处于转化的复杂体系中的主动运作者」(注2)。同理,若地方纹理要与剧场发生有效的互动关系,其实亦代表,地方纹理不是如铁板一块静止不动,而是活生生地处于运动关系中,有待创造、改写,甚至挑战。
剧场对地方叙事的不同介入
在此基础上,也许能试图谈论近来一些处理地方纹理的剧场制作。山东野表演坊在花莲县富世村的《富世漫步—有火的地方就有故事》对笔者而言,主要的未竟之处便在,即使地方纹理内在的复杂、不稳定、矛盾与持续发展中的本质几乎快满溢出演出主体,但这些皆非制作本身著意处理的对象,所以观众表面上得到的是对地方怀旧式的温情凝视,以及一种叙事观点对地方发展的统摄,但它却无法完全使观众信服,因为观众始终能感觉到,在演出之余、叙事之外,存在某种为了使地方纹理能被演出把握,而被排除的地方脉动。
对地方空间的改造可见于今年举办进入第三届的南投「鱼池戏剧节」,各档制作在市场里、废墟墙边、夹娃娃机店等空间发生,完全不掩饰其空间改造意图,各个作品几乎是直接就地发生,空间是它运作的具体条件,剧场思考的是已存在、具有空间意义的物理条件如何影响或不影响演出的进行,使其得以安置观看者的凝视。当主创者表示戏剧节的目的是「想要让家人有戏可看」,那在此层次上,「鱼池戏剧节」的明亮欢快,的确达成目的。
相较之下,斜杠青年创作体于屏东海口村演出的《迷走计划:做伙来去踅海口》则是技巧性地,展现剧场如何将地方纹理作为再创作的生命体,海口居民的话语既被重录在耳机中出现,也在演出后段现身说法,虚实交错中,剧场毫不隐瞒它对地方叙事的介入,包括声音、地景、人物的再创造,却也要说,剧场的生命力亦来自与地方的时空与感官配置互动。
创造新叙事 拒绝地方纹理
前述两个作品本质不脱谢喜纳区分的两种关系,可是,有没有一种剧场演出,能够断然拒绝地方纹理?
二○一九年于台南艺术节演出的《咖哩骨游记 2019.旅行装》便是完全拒绝地方纹理,却反而得以借此,开拓我们对地方纹理的想像范围。本作也以耳机剧场形式演出,观众在台南市吴园附近的城市空间游走,但耳机内却是一组全新、虚构的故事,在已层叠覆盖历史的城市景观上,《咖哩骨游记 2019.旅行装》无意重塑历史,它大逆不道地创造一层新的叙事和历史,故得以彰显空间与感知意义间之武断性,这组关系其实本身有著开放流动的可能。
《咖哩骨游记》等作,皆多少揭示地方之流动,但舞蹈家周书毅在新北金瓜石的驻地创作展演《无用之地:身体录像展演 金瓜石》 却借对「死」之追溯,让我们能进一步推进地方纹理之「生」的内涵。周书毅的《无用之地》系列皆是为被城市抛弃的空间而作,今年选在金瓜石矿场旁的百年石梯、民宅菜园中废弃的理发厅遗迹、水湳洞选炼厂遗址三地演出,身体在这些空间中游走,隐约有曾在此地生活的人们的身体样态:矿工、理发师、老人、军人……虽然当周书毅的身体愈舞动、愈徒劳无功地撞击包围遗址的铁丝网时,象征的不是这些与体感紧密相连的地方记忆之所是,而是记忆的不在场、无法靠近,但《无用之地》的存在本身,却也是对地方纹理最终极的继承与实现,消逝的记忆经过转换成为身体态势,成功地在舞者身上、在舞蹈影像中找到了载体。至此,表演艺术走向,地方纹理与剧场/舞蹈间已不再有别,而互为共生,彼此铭刻。
在那里,剧场的生命与地方的生命,可以有了平实的交会与生发。
注:
- 《环境戏剧》,理查.谢喜纳著,曹路生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页14。
- 同注1,页5。
文字|洪姿宇 剧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