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廷
序场剧本发展中心文学经理。国立台湾大学毕业,主修外文,辅修戏剧。关心翻译、评论、编剧、构作等剧场创作与文字工作。
-
 艺@书
艺@书女神下狮城
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于晚年所写的《梦幻剧》(A Dream Play),以印度神祇因陀罗(Indra)之女阿格尼斯(Agnes)下凡一遭的游历,探讨苦难的本质与生命的意义。其中奇幻的角色、破碎的场景虽打破了20世纪初工整严谨的剧场惯例,却也创造纯粹如诗、流动如梦的质地,在剧作上另辟一条更奔放无拘的道路。新加坡剧作家亚非言(Alfian Saat)看见抵抗建制的潜能,便以史特林堡的结构概念为基础,写出《梦幻剧:亚洲男孩三部曲之一》(Dreamplay: Asian Boys Vol. 1),照见新加坡不可言说的男同志历史。 审查制度的眼中钉 最早,亚非言其实是位诗人。1998年,他出版诗集《激烈时刻》(One Fierce Hour),其中一首〈新加坡你不是我的国家〉(Singapore You Are Not My Country)表达了一位青年对国家爱深责切的情感。这首诗宛如平地一声雷,宣告著一位文坛新星的诞生,却也因其强烈的措辞让亚非言从此陷入爱国与否的争议。 之后,亚非言的身分渐渐过渡成编剧,社会关怀不减反增。他熟稔地操持英文与马文,瞄准多族裔的剧场观众,更藉著双语乘载的不同观点增添剧作的辩证层次。但,正是剧场这种公共性与政治性,让新加坡政府找到向他设限的借口。在《梦幻剧》送审时,政府便以剧中探讨同性恋主题为由,祭出R18级的限制,以此箝制曝光与收益。2024年,亚非言更将与审查制度的长期恩怨写成《新加坡剧场之死》(The Death of Singapore Theatre)。 老派女神下凡乱救人 如同史特林堡的原著,亚非言的《梦幻剧》以女神阿格尼斯下凡开篇,不过这次她以分不清是选美佳丽或变装皇后的姿态降生人间。一登台,女神发觉比赛已来到问答环节,便顶著浮夸假发义正词严地说,夺冠之后,她计划把男同志从以芭芭拉.史翠珊(Barbara Streisand)为首的伪女神崇拜中拉出来,变回阳刚的异男,导回快乐的道路。语毕,掌声如雷。女神下凡一席话,竟变成带著保守任务的环球小姐。 一个转身,女神发现身边是4位年龄、族裔各异的跨性别变装皇后。皇后们听闻女神的来历
-
 艺@书
艺@书木造的船,伞造的花,人造的梦
当代媒体所描绘的北韩,往往是个独裁、专制且审查制度铺天盖地的神秘国度。若不是脱北者转述,外界可能难以想像那里是个高官吃香喝辣、百姓食不果腹的人间炼狱。不过,即使希冀逃出北韩的人数愈来愈多,正如历史上所有一夕之间紧急宣布的分裂,住在南韩且迈入老年的长者,会不会至今日仍盼著回到两韩分裂前的北乡?南韩剧作家尹美贤(윤미현,Yun Mi Hyun)便在北纬38度线的历史裂缝中找到戏剧的破口,以此为题,写下剧本《木舟》(목선,The Wooden Boat)。 从诗人到编剧的帅气转身 成为剧作家之前,尹美贤其实一直以诗人与小说家的身分自居。对她而言,文学是由诗歌与小说共创的景致,而剧本并不在视野里,一直到研究所时期她才有了与这个文体的初相遇。可惜,没有剧本让她动心,于是她决定提笔写出自己喜欢的作品,独幕剧本《我们可以见个面吗?》(우리 면회 좀 할까요?)如此诞生。 尹美贤本想浅尝即止,回头徜徉在诗歌与小说的世界,没想到《我们可以见个面吗?》夺得2012年韩国剧作家协会(한국극작가협회,Korean Playwrights Association)剧本奖。自此,新欢变正缘,她便在南韩剧场以剧作家的身分打滚至今,10几年间也陆续发表了横跨话剧、歌剧、音乐剧的作品,包含《菜园杀手》(텃밭킬러)、《德州姑姑》(텍사스고모)以及《木舟》。 死前,能不能回去北方? 《木舟》的故事源于90几岁的老蔡。老蔡在两韩分裂前将妻小留在北韩,只身一人跨过停战线,不料一别就是一生。纵使物是人非,他在死前的遗愿还是与家人相聚。但,不论老蔡申请官方的南北离散家族重聚计划,或找上已有30多年偷渡经验的仲介,最终屡屡败露。某天,新闻报导日本大和堆海域停了几艘北韩漂来的渔船,闻此,老蔡决定剑走偏锋他要想办法搭上这些幽灵船。船怎么来,他就怎么去。 老蔡的思乡之情蒙蔽了他的双眼,看不清邻居老马正在暗处动著歪脑筋。老马是80几岁的诈骗惯犯,出狱后虽开了一家房屋公司,但一锁定目标就想敲一笔。老马嗅到老蔡身上的商机后便开始找队友,第一个对象是无名的「运动服青年」,善于读书考试,却因太内向而无法上班,只能以出租证照度日;第2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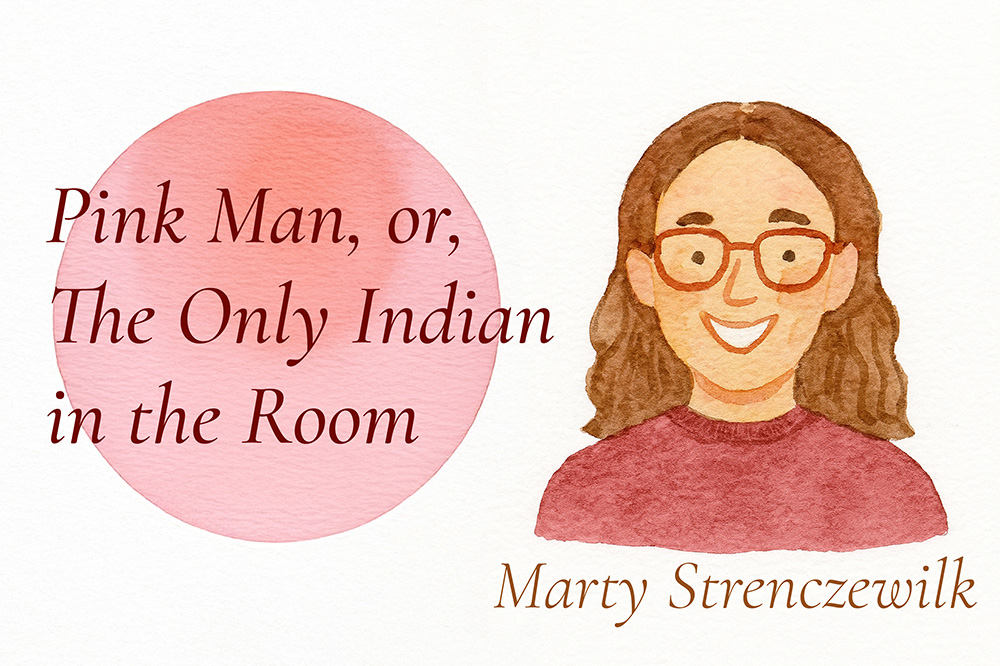 艺@书
艺@书粉色的认同
在美国这个种族多样的国度中,身分政治一直都是剧作家亟欲探索的主题。近年来,除了非裔剧作家之外,也有愈来愈多原住民剧作家以种族的角度切入书写剧本,奥吉布瓦族(Ojibwe)剧作家马蒂・史特伦兹威尔克(Marty Strenczewilk)便是其中一例。他凭著《粉色的人或在场唯一的印第安人》(Pink Man, or, The Only Indian in the Room,以下简称《粉色的人》)从2023年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多元之声剧本竞赛(Diverse Voices Playwriting Initiative)脱颖而出。藉著这个类自传、类单口的喜剧作品,观众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看见原住民这个身分所蕴含的美丽与哀愁。 「内化的种族歧视」 史特伦兹威尔克成长在白人小孩才有权利平安健康长大的时代。镇上,两名非裔与亚裔小孩因外表不同而被霸凌。他看著自己的白皮肤与褐头发而感到幸运至少他可以藏起自己的原住民血统,伪装成白人,全身而退地度过大学以前的时间。 但,他凭著少数族群的身分拿到大学奖学金后,「可以伪装」便成了问题。当他顶著白人脸孔走进满是少数族群的新生教室,非裔、拉丁裔、印度裔的恶意齐发「白人又来偷我们的奖学金。」另一边,即使其他原住民朋友第一次给了他归属感,但相比之下,他受过的苦难似乎太少,少到他不够格自称一位原住民。 日后,一次在诊间,咨商师剖析道,他对自己有种「内化的种族歧视」。这句话划破了幻象。他的童年幸运不是真的幸运,安然无事长大成人的代价,是对母系原住民血脉的纠结与不愿理解。咨商师的无心之谈,逼著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出身,却也燃起写作的火种,焠炼出如今的《粉色的人》。 类自传、类单口的喜剧作品 《粉色的人》以类自传、类单口的体例写成,角色有印第安人(Indian)、纳纳博佐(Nanabozho),以及穿梭在各场景间,时而评论、时而扮演的歌队。 印第安人是剧作家在剧本中的化身,向观众说一则又一则个人史与家族史故事,但有趣的是,剧作家只给予角色「印第安人」之称。没有名字,是因印第安人/剧作家曾逃出命名仪式;用贬义词则突显了他们内
-
 戏剧 变形成人的代价
戏剧 变形成人的代价《羊之歌》 以寓言叩问人的盲目欲望
羊群中,一只羊两脚站了起来。与低头吃草的同类相比,牠显得更有定力与决心。毕竟,牠想从「牠」变成「他」。 牠有变形成人的欲望。 比利时柏格曼剧团(FC Bergman)的《羊之歌》(The Sheep Song)便在这般怪诞的设定中展开了。一只羊踏上变成人的旅途,路上所见虽有人有兽、有男有女、有善有恶,但牠还是毅然走完整趟旅途,变成新造的人。 回顾西方文学史与戏剧史,羊的旅途一点都不新,但柏格曼剧团善于以经典挖掘灵感、发展作品,「不新」恰是他们的专长。《羊之歌》中,羊的所求就是文学中常见的「变形」。当牠走在《圣经》的意象上时,身后一幕幕掠过的场景,也如中世纪剧场的戏车。 旅程的开端:变形的欲望 《羊之歌》最初,羊就有变形成人的欲望,推著叙事前进的也是这股驱动力。 西方文学中早有「变形」的概念,《木偶奇遇记》就是一例。如《羊之歌》的羊得看透世事,皮诺丘也得越过重重试炼。两名角色都得通过考验,才会有超个人力量(如仙女或人类社会)认可成人的资格。但,两者不同的是,皮诺丘变形成人不是出于己愿,而是仙女给他的额外奖赏。最初,木偶不知道他有变真人的可能。 再探源一点,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是西方文学中更古老的例子。奥维德从希腊罗马神话中采集与「变形」相关的篇章,编写成诗,而他笔下角色变形的驱动力五花八门。少数如宙斯,追爱的欲望可转为变形的驱动力,化作天鹅,但更多的是神祇等超自然力量操弄的结果。 《羊之歌》中的羊何来变形的欲望?或,人或兽为何想变成另一族类?英文中,欲望(desire)、想望(want)与匮乏(lack)是近义词。变形的欲望,是我族匮乏漫延成的他者想望我不够好,我多想变成他。但,羊在人身上看到什么长处?柏格曼剧团只呈现了,当两族的界线变得模糊,人与兽变得没有太大区别。在贬己抬人上,人与羊似乎一样不遑多让。
-
 艺@书
艺@书打造一本属于每个人的马戏书
对于身在台湾的我们而言,第一次接触「马戏」的契机或许藏在电视机或游乐园内,而我们对马戏的记忆便停留在那些丢瓶子的杂耍者与跳火圈的狮子上。不过,这种单薄的想像很快就会被《火箭发射:24位当代马戏大师的创作方程式》(后简称《火箭发射》)打破了。
-
戏剧 王嘉明vs.理查三世 Round 4!
声响涂鸦 制造「真相」
王嘉明前几次执导《理查三世》,「声音」是他始终著迷的元素。在玩过「身声分离」、现场乐队与演员人声撞击之后,这回的《混音理查三世》,王嘉明说要让听觉元素有更多「街头、涂鸦」的质地,不只让多位演员以不同声调扮演同一角色,还让演员同时斜杠当乐手,毫不避讳地向观众展示这些角色与声响被「制造」出来的过程,因为这些人造感、加工感,正是王嘉明研究《理查三世》的体会,也是他创作《混音理查三世》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