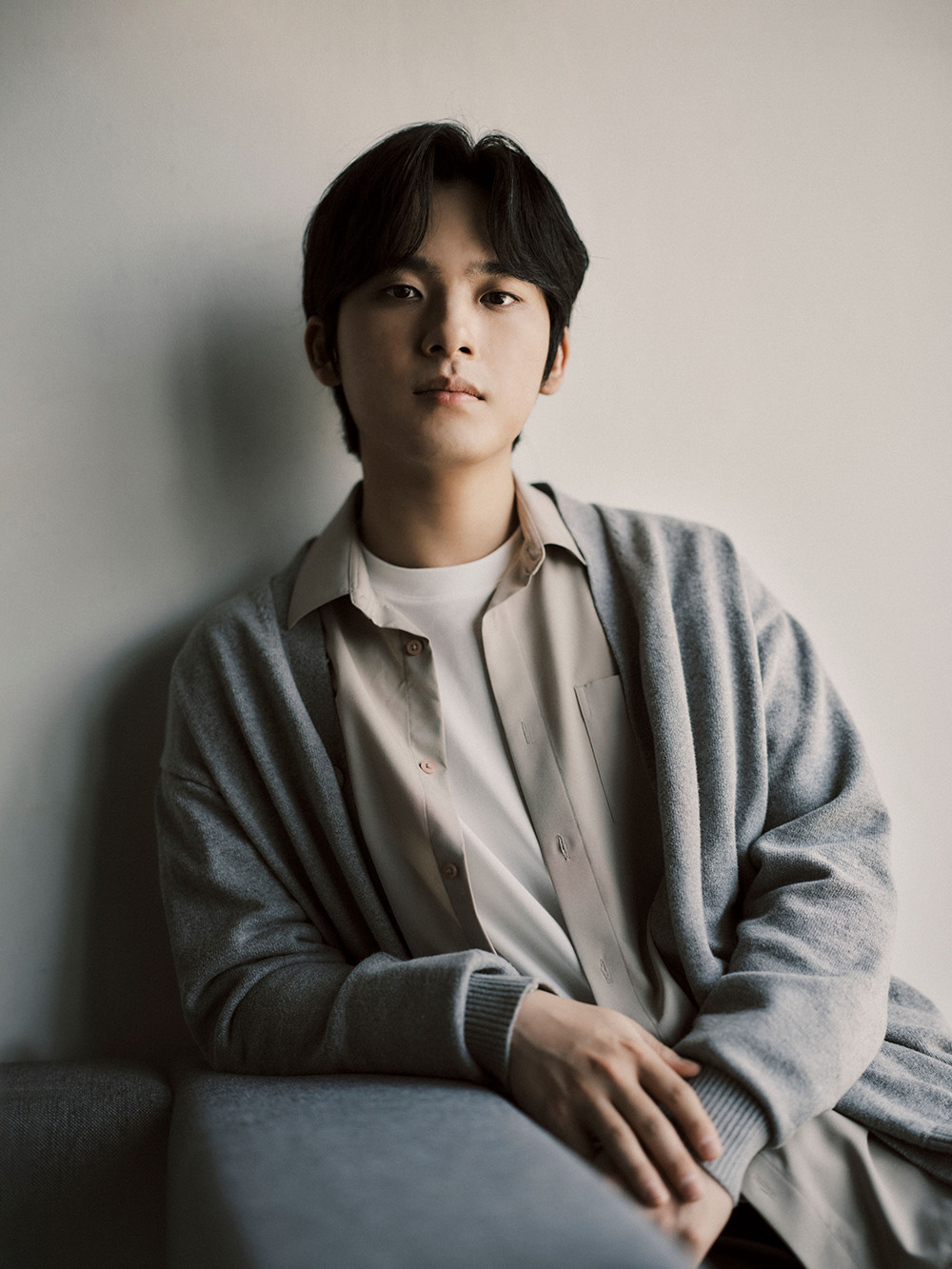「场地伙伴计划」有改动 受欢迎剧团遭到排除
香港的表演艺术工作者经常诟病本地的演艺场地数量不足,近年随著西九文化区和大馆等场馆启用,好像缓解了一些问题,但这些场地不属政府管理,即使有空档,但租金对团队来说不是容易负担的事,要多做几场和提高票价才有机会收支平衡。然而能有长演可能性的作品,和能够承担长演节目的本地团队,真的屈指可数。 长期依靠政府资助运作的经营策略是发展的困局。长演制作过去10多年有较多讨论和实践,目前仍然是以有明星参演、且有商业制作公司愿意投资的作品较有成功的可能。不过曾是葵青剧院演艺厅17年场地伙伴的风车草剧团,在2025年底公布最新一轮的场地伙伴名单时就不再入选,这场地会由本来与风车草共享场地的中英剧团独家获得。 「场地伙伴计划」从2009年起开始推行,对政府场地来说,可说是一次与演艺团队同行的突破,除了发展场地形象和伙伴团队特色,在观众拓展的长期策略方面,亦能让场地和团队双方受惠。风车草剧团是当年第一轮获入选的演艺团队之一,当时与W创作社一同申请成为场地伙伴,两团在当时都是新进专业剧团,在艺术方向上以本地原创和贴近年轻人心态和关注的题材出发,累积了一群同代的观众群,并成功建立几位创团成员梁祖尧、汤骏业、邵美君的独特的舞台魅力,在演艺厅这个900席位的场地深耕出他们和观众对这地方的归属感,让这个位于新界的场地的活力不逊色于市区内的场地。 近年,风车草剧团每年平均制作3至4个作品,在演艺厅上演两星期的票房都爆满,有些受欢迎剧目甚至另觅场地接连演出,可说是场地伙伴计划推出以来的一张亮丽名牌。不过近年很多香港场地常常出现很多不可抗力的原因,让作品未能顺利上演,其中由政府管理的场地自然会有更多人关注。另一方面,政府既期望在「促进表演艺术的多元化、专业化、产业化及盛事化发展」,在场地上如能把握更多可控元素,似乎应该更容易管理,但场馆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也让团队发展受到影响。 风车草剧团作品能引起大量观众共鸣和支持,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能说出观众的心声,但这些心声是否人人有感,则难以估计。去年公布表演场地租用政策和措施的改革方案时,已减少了伙伴计划的场地数量(绝大部分场地不再会同时有两个团队进驻),及减少获选艺团使用场地的日数,部分评选委员说是希望资源能让更多团体使用,然而这样的调整是否已偏离计划的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