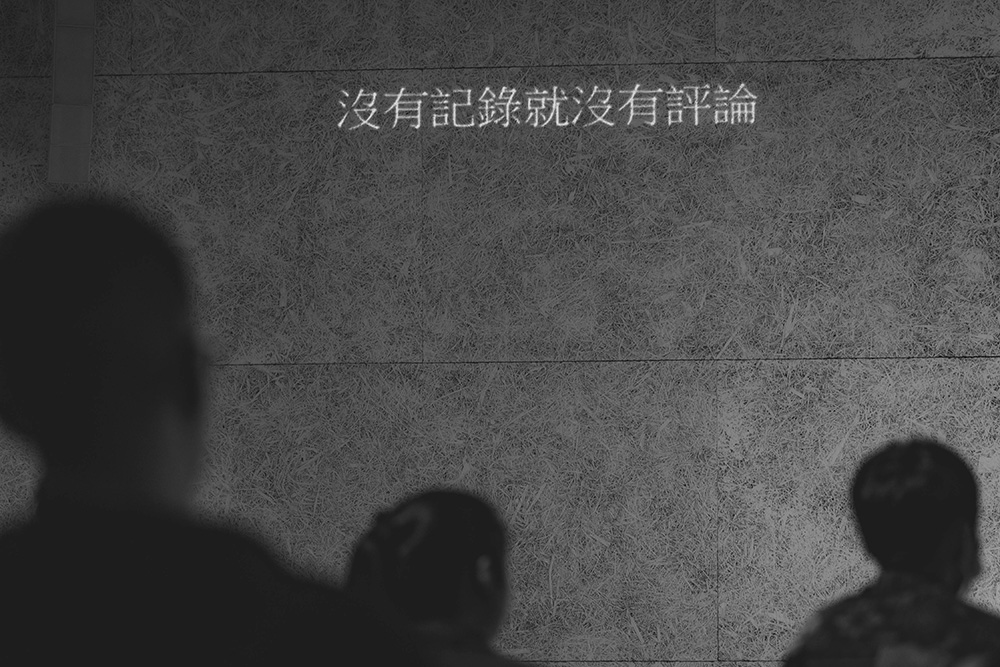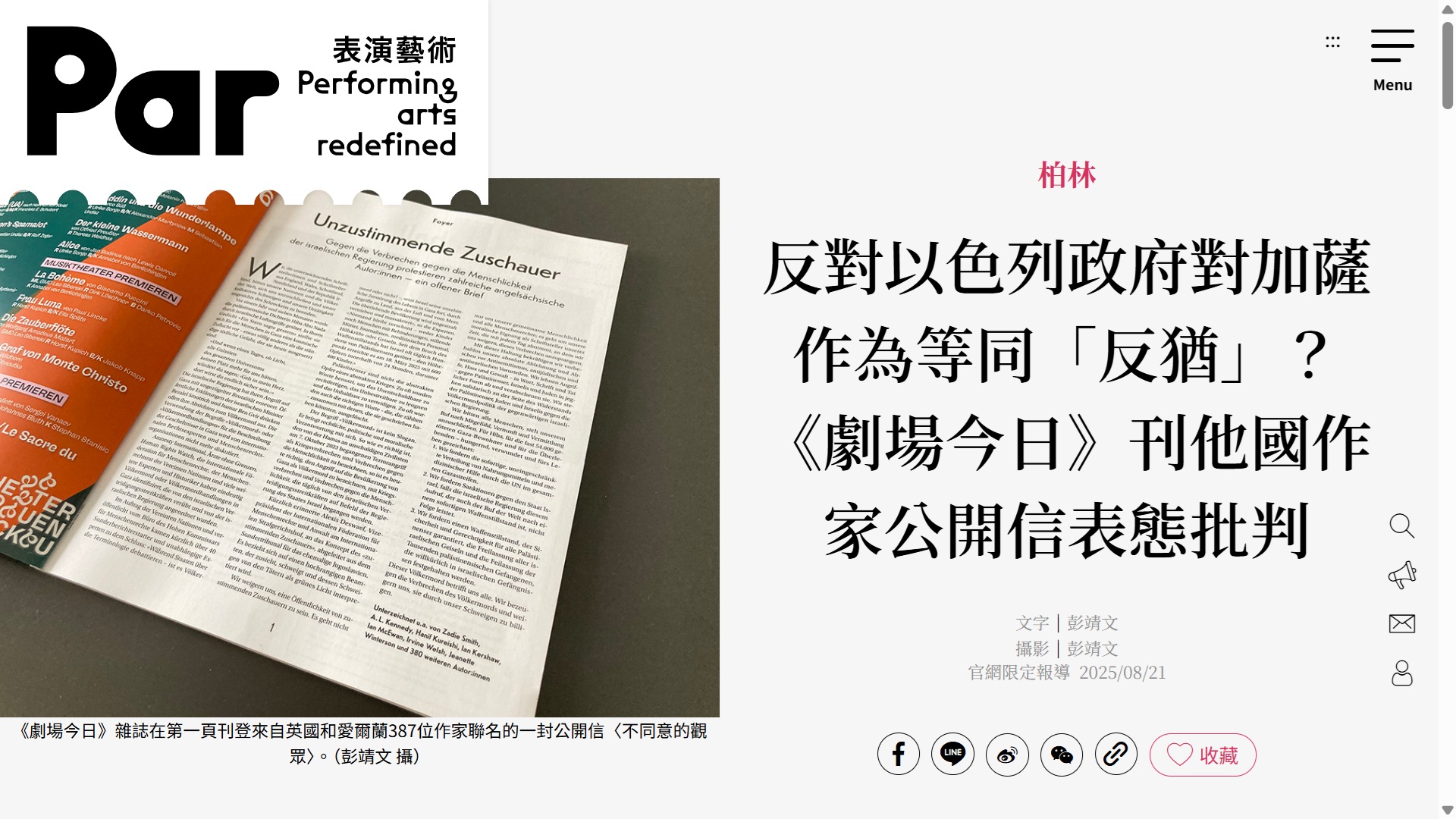味蕾在歌唱,窒息后发酵
评《超辛奇小熊软糖》舞台上,一辆布帐马车静静伫立于黑暗之中,两侧的萤幕播放著韩国的画面。当帆布被掀开,食物的气味随之涌出,气味作为记忆的招唤,并在演出过程中不断改变。演出中邀请两位观众成为顾客,亲口品尝一道道料理。虽然坐在台下的观众无法实际品尝,但那股气味仍悄然弥漫于空气之中。 Jaha Koo身兼说书人与厨师的角色,以料理作为叙事的媒介。这场演出可说是一种「三重奏」:口白的叙事、料理的叙事、以及萤幕上的影像,同时唤起听觉、嗅觉(与味觉)、视觉的想像。 同样将「饮食 文化 剧场」并置,我想起今年(2025年)台大游心剧场的《旅行的舌头》。演出者一边讲述、一边烹调,带领观众理解食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传播与演变,探讨跨文化背景下的身分认同与饮食的关联。味觉本身具有社交的特质,在观众共同品尝、描述的过程里,我也重新界定了自己对这些食物的情感连结。那张长桌又被称作「中岛」,仿佛是一座漂浮的岛屿,象征味蕾在不同文化间的流动与漂泊。 然而,《旅行的舌头》虽在文化层面横跨多国,形式上却略显平面,更像是一场带有深度谈话的烹饪节目。相较之下,《超辛奇小熊软糖》以韩国小吃为出发点,从个人经验切入,却能深刻挖掘情绪的转折,使观众更容易进入其叙事之中。 《超辛奇小熊软糖》在视觉与形式上皆采取可爱、鲜艳且富感染力的风格。然而,文字与影像间不时透露深层而悲伤的底色。整场表演如同一场比喻的游戏:Jaha Koo反复抓住又放生的蜗牛,是背负重担、迁移至陌生之地的象征;小熊软糖成为旅居柏林时的慰藉;鳗鱼的洄游则更明确诉说:家并非固定的地理位置,而是一种持续移动的状态。 以食物为主题的演出,往往同时涉及文化与历史的层面。此作的结构可分为个人自传式的旅程,从韩国到柏林,以及关于父亲、食物与光州事件的连结。那么,这场演出的受众是谁?若观众期待的是关于食物文化与历史的深度探讨,可能会觉得其力道稍弱,每个段落停留的时间不长。但或许,这场演出更想指向离散者的处境,一个人如何在文化、家与适应之间寻找回应。 演出末尾,所有食物的气味交叠在一起。蜗牛、小熊软糖、鳗鱼以机械般的音调歌唱。看似冷静疏离的表述,反而创造出情感投射的空间。哪里是家乡?也许家乡正是人终将回归、甚至死亡的地方。那些歌词如幽灵般盘旋脑中,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