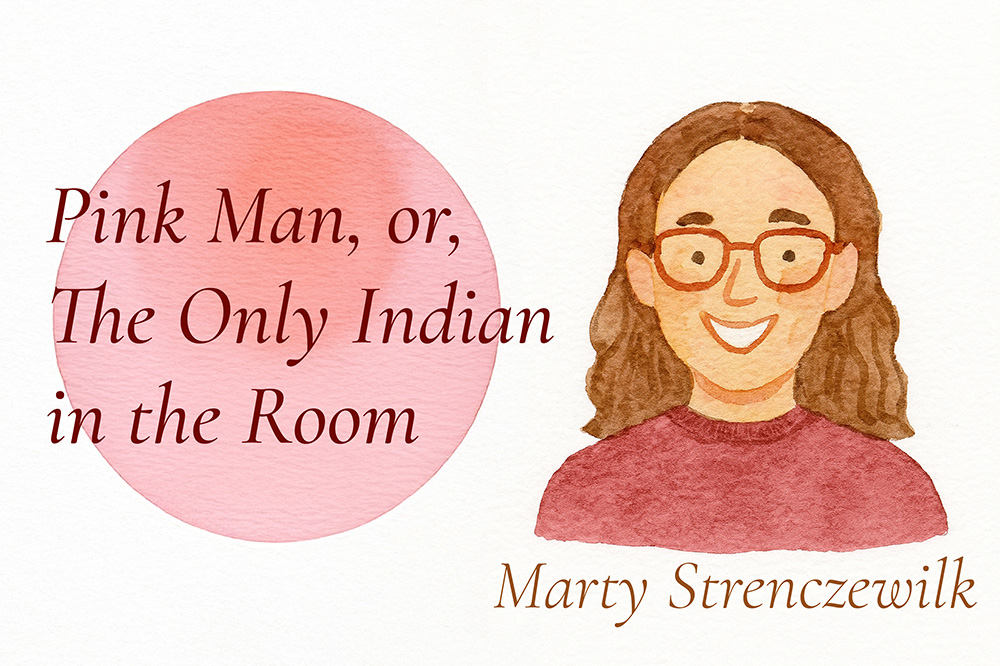在美国这个种族多样的国度中,身分政治一直都是剧作家亟欲探索的主题。近年来,除了非裔剧作家之外,也有愈来愈多原住民剧作家以种族的角度切入书写剧本,奥吉布瓦族(Ojibwe)剧作家马蒂・史特伦兹威尔克(Marty Strenczewilk)便是其中一例。他凭著《粉色的人或在场唯一的印第安人》(Pink Man, or, The Only Indian in the Room,以下简称《粉色的人》)从2023年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多元之声剧本竞赛(Diverse Voices Playwriting Initiative)脱颖而出。藉著这个类自传、类单口的喜剧作品,观众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看见原住民这个身分所蕴含的美丽与哀愁。
「内化的种族歧视」
史特伦兹威尔克成长在白人小孩才有权利平安健康长大的时代。镇上,两名非裔与亚裔小孩因外表不同而被霸凌。他看著自己的白皮肤与褐头发而感到幸运——至少他可以藏起自己的原住民血统,伪装成白人,全身而退地度过大学以前的时间。
但,他凭著少数族群的身分拿到大学奖学金后,「可以伪装」便成了问题。当他顶著白人脸孔走进满是少数族群的新生教室,非裔、拉丁裔、印度裔的恶意齐发——「白人又来偷我们的奖学金。」另一边,即使其他原住民朋友第一次给了他归属感,但相比之下,他受过的苦难似乎太少,少到他不够格自称一位原住民。
日后,一次在诊间,咨商师剖析道,他对自己有种「内化的种族歧视」。这句话划破了幻象。他的童年幸运不是真的幸运,安然无事长大成人的代价,是对母系原住民血脉的纠结与不愿理解。咨商师的无心之谈,逼著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出身,却也燃起写作的火种,焠炼出如今的《粉色的人》。
类自传、类单口的喜剧作品
《粉色的人》以类自传、类单口的体例写成,角色有印第安人(Indian)、纳纳博佐(Nanabozho),以及穿梭在各场景间,时而评论、时而扮演的歌队。
印第安人是剧作家在剧本中的化身,向观众说一则又一则个人史与家族史故事,但有趣的是,剧作家只给予角色「印第安人」之称。没有名字,是因印第安人/剧作家曾逃出命名仪式;用贬义词则突显了他们内化的种族歧视。
纳纳博佐则是在奥吉布瓦族口述传统中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角色。他可以是渡鸦、兔子、郊狼或人类;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可以是精神领袖也可以是捣蛋人物。如此无法定义,剧作家于是将纳纳博佐设定为咖啡厅老板,在因缘际会下将印第安人从「白种人」、「红种人」的僵化定义中解放出来,带著他走上粉色的和解之路。
不是红色也不是白色
剧本的时空设定在一个大雪的冬夜。星期五,咖啡厅的麦克风属于有故事的人,但眼下没有志愿者,纳纳博佐便瞄准了印第安人。挡不住邀请,印第安人站到麦克风前,开始说他的故事。
童年时,印第安人的朋友发觉他的原住民身分后,往往以刻板质疑回应:为什么他那么白?为什么他没戴羽毛?为什么他没骑马?这些排山倒海、未经修饰的讪笑都让他厌恶自己的奥吉布瓦族血统,也排斥每年跟著母亲回到保留地参加庆典。
他也记得以前坐在白祖父的大腿上看西部片,跟著约翰.韦恩(John Wayne)一起喊「杀死那些野蛮人」。与此同时,他的奥吉布瓦族祖母正在厨房里为他们煮饭。多年以后,他才发现自己天真又无知。他里外都太白了,白到甚至愿意为电影里那些开枪杀死族人的牛仔喝采,也不感到冒犯。
但,以原住民的身分进入大学后,印第安人认知到族裔也不是非白即红那么简单,有时他像个冒牌者,有时他又是个原住民。但,更多时候,他卡在一个少数族群争取少数资源的环境里,而在「少数」的标签下,一条食物链串起各个族群,所有互动都是尔虞我诈。此时,身分政治的复杂性再度加深了他的自我认同障碍。
看著印第安人说著这些无益于建构身分认同的故事,纳纳博佐决定点出问题的核心,挪移时空,带著印第安人重返那个他决定断根的场景。当年的命名仪式前一晚,印第安人把自己灌醉,觉得生为原住民简直是场闹剧。一气之下,他放火烧了仪式的服饰、头饰、乐器,并在愤怒与羞耻中离去。
但,既然有第二次机会,印第安人踏上自我和解的旅程。他不再避讳在社群媒体上公开身分,并发现网路上的同温层比质疑者还多。同伴的力量也给了他勇气,在纳纳博佐的引领下,他见到祖母、回到当年中断的命名仪式,而就在奥吉布瓦族旅行之歌的陪衬下,他取回姓名、找回身分,完成建构自我认同。
交叉性引出跨文化共鸣
身分政治是相对沉重的剧本主题,剧作家能否以轻驭重便可见其功力。除了印第安人的复杂身分可以让剧作家呈现相反观点而不偏倚,纳纳博佐无疑是协助制造戏剧节奏的最大功臣。承袭自奥吉布瓦族的口述传统,纳纳博佐有时加快故事,有时减缓节奏,是印第安人的导师兼反派,甚至可以灵活调度歌队,让场上随时准备从多焦的大乱斗变成个人的脱口秀。他的存在,再辅以咖啡厅开放麦克风(open mic)之夜的设定,便是《粉色的人》可以用喜剧写身分政治的关键。
《粉色的人》的核心概念是「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分,而这些身分的交织会形塑独特的生命经验。当看似冲突的身分共存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往往会引发认同上的拉扯。比方说,印第安人的白人外表与原住民血统让他经历了强烈的自我认同拉扯。不过,这种经验其实具有普世性。因此,虽然《粉色的人》是奥吉布瓦族的故事,但任何经验过身分冲突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
在众人仍为「艺术是否该为政治正确服务」而争论不休时,史特伦兹威尔克就先以他的亲身经历反映了当代身分政治的复杂性。《粉色的人》中,印第安人的外表让他能够体会身为多数与少数各是何种感受,并在看似相反的两种经验中窥见同样存在的偏见与歧视。而,或许处理复杂的方式就是承认复杂。承认后,印第安人才能从白或红的选项中找到出路——他选择打破单选的机制,粉色才是他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