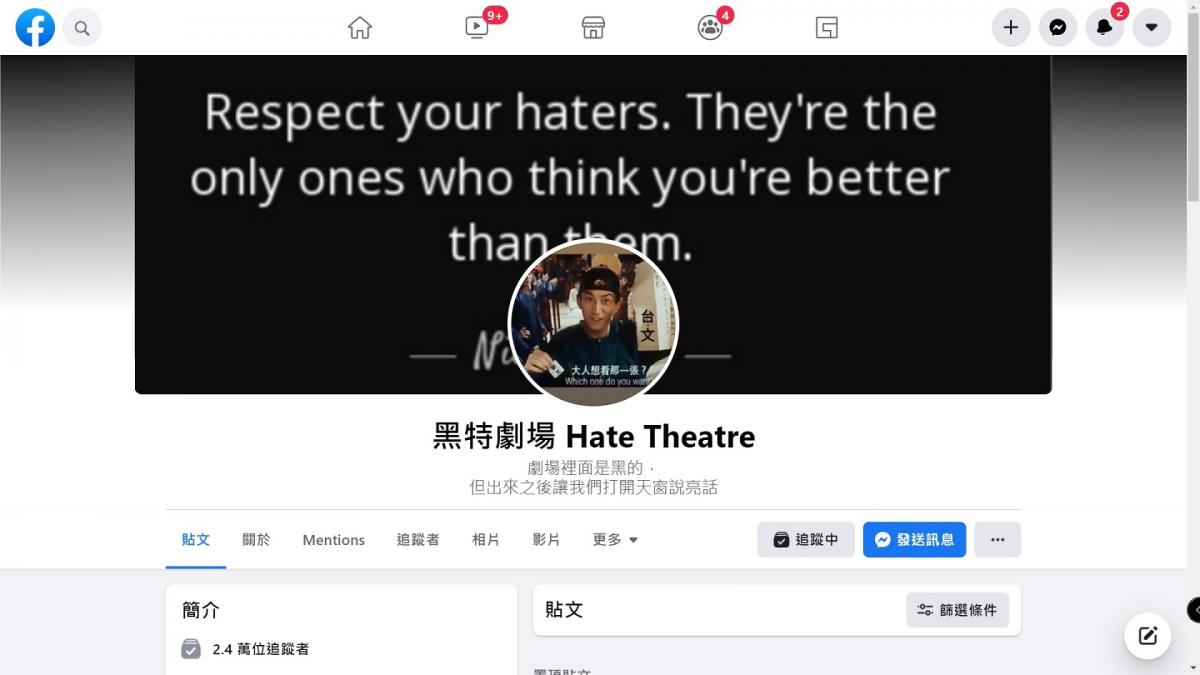蔡孟凯
艺文工作者
-
 戏剧
戏剧从「沉浸式剧场」到「剧场里的沉浸式」(上)
需要写在最前面的是,近年由大型场馆或艺术节主导,并于专业剧场空间发生的「沉浸式」展演,大体可以分成:一、主打扩充实境(AR)或混合实境(MR)科技,以穿戴式装置为载体打造数位化的沉浸式体验;二、不倚赖前述设备,单纯以空间调度、舞美设计及声音影像达到沉浸效果的展演制作。本文主要讨论之案例为《侦探学》(2022)及《Sucks in the Middle》(2024),其范畴属后者。 沉浸式展演约莫在2015年前后逐步进入观众视野,这些展演大多采高单价、多场次、少人数的销售策略,主打结合餐饮、互动游戏、游走式参与的复合式体验。同时多以餐酒馆、高级旅店、咖啡厅等非典型场地作为演出空间,既可让观众身历其境地感受整个作品,又能摆脱繁冗的剧场规范。同时,这些非典型空间所带来的亲密感、话题性、甚至是异业合作的潜力,都让沉浸式展演近年在艺文市场占上一隅,成为表演艺术一个新形态(重点是有效)的营运模式。 近几年,大型场馆也开始试著打造独家限定的沉浸式展演,从发生在剧场外建筑空间(例如国家两厅院《神不在的小镇》、台湾戏曲中心《和合梦》),到发生在剧场空间内,但不使用原有的舞台镜框及观众席的沉浸式展演(如台中国家歌剧院主办,本文主要探讨的对象《侦探学》、《Sucks in the Middle》),虽然数量尚不算多,但演前演后也确实收获了不少回响及讨论。 从主事者和创作方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制作趋势或许反映了艺文场馆对于节目的多元、场地的实验及受众的开拓,所展现的积极与实践。但同时令人好奇的是, 一个从成形到成功都在剧场外的非典型展演空间里的关键字,是为了什么原因会让我们试著把它放在剧场里?而观众和创作者又希望从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沉浸式展演获得什么?
-
 戏剧
戏剧从「沉浸式剧场」到「剧场里的沉浸式」(下)
拆掉观众席,然后呢?沉浸式展演制作对剧场本位的意义 「打破镜框」对于剧场来说早已不是新命题,如果单纯讨论观演距离的试探或是场地结构的改装,那其实还有更多、更久的作品应该被提到。表演工作坊的《如梦之梦》(2005)、当代传奇剧场的《水浒108I上梁山》都曾对国家戏剧院加以改造,将表演区延伸到观众席内。但在「沉浸式」一词定义成型的今日,《侦探学》、《Sucks in the Middle》所打破的不只是作品之外的镜框,而是作品之内的第四面墙;也因此,所谓的「沉浸」才得以成立。 回到本文开头的提问,当艺术家大费周章地让观众席从剧场里消失、将前后台空间打掉重练,把剧场费心改造成适合演出的结构,那使用「剧场空间」作为场地的用意是什么?而就剧场本位出发,这样的作品对剧场的意义又在哪里? 这里我想再拉进来一个作品,是与《Sucks in the Middle》同一周于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演出的《感觉的边界》。这是台中国家歌剧院2024年新艺计划甄选的两件作品之一,由新兴数位艺术团队SYNZR(吴秉圣、邱俊霖、刘承杰)呈现。《感觉的边界》是一个音像艺术作品,观众与表演者被数公尺高的数位屏幕和多声道音响环绕,辅以剧场灯光设计及动态捕捉技术建构出奇幻的视听体验。 观看《感觉的边界》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有某种沉浸式的效果,它同样没有明确的观看区与观看方向、观演距离极近,同样有种整个空间都被作品填满的感觉。但它并没有《侦探学》或《Sucks in the Middle》那般,将剧场空间改造成另一种场景的企图,也没有前述二者所具有的、类似限地创作(site-specific)的理念、为特定表演空间量身打造它的内容,这个作品在其他场所(暂且不论设备条件或是技术规模)同样可以成立。 我想要特别指出的,是创作团队在演后座谈中的一句发言。当创作团队被问到,如果这个作品在美术馆或是其他多功能、非典型场地也能演出,「那么剧场空间对这个作品的意义是什么」?而创作团队表示,相对于音像艺术过往以户外空间或视觉艺术展场作为展演场地,剧场提供了相对专业、弹性、多元的技术条件及设备环境。更重要的,剧场本身是一个具独立性的空间,可以避免作品受其他环境因素譬如声音、光线(可能来自于场地外部环境,或是同
-
新锐艺评 Review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我没有在装疯的错觉?
一踏入「芝山疗养院」的大门,戴著圣诞帽的「院长」满面笑容地与探访疗养院院友的「亲友」们寒暄。我一面参观这个喜气洋洋的疗养院,同时感受到一股违和感缓缓浮现,我突然惊觉:为什么「院长」没有戴口罩?所有场内的「亲友」和「医护人员」都戴了口罩,为什么他可以不用?现场敞开嘴呼吸的除了他,就是床上五花大绑的病友了这是我在《宇宙疯》第一个获得的提示。
-
 回想与回响 Echo
回想与回响 Echo「超亲密想像」的落幕、还是播种?
在踏入云门剧场、欣赏第9届超亲密小戏节那天的上午,我参与了一个以互动式及沉浸式展演为主题的线上讲座现场。主讲人如数家珍地细数国内近几年沉浸式展演的佳作和趋势,彷若这就是国内表演艺术产业的未来式,是剧场艺术在疫情持续冲击、娱乐型态改变等各方逆境夹击之下的突围之道。而令人省思的是,同样是以高互动、近距离、非典型演出形式为号召的超亲密小戏节,今年却已是最后一届。 首发于2010年的超亲密小戏节,可说是国内非典型剧场和实验性展演的指标品牌。从最初结合微型剧场与街区导览的概念,将数个小型的物件、偶戏作品放置在咖啡馆、图书馆,甚至是宫庙、巷弄老屋之中;到今年结合线上与线下,划出「包区」(晴光市场周边)、「包厢」(云剧场),以及解构云门剧场空间,以动态美术馆为概念策画的「包栋」。第9届超亲密小戏节透过不同层次的观看距离回应被疫情时代打乱的剧场生态,同时维系多年如一日的关照让观演双方保持著「亲密」的距离,在空间与时间皆「小」的篇幅里,经历作品的诞生与覆灭。 2014年之后超亲密小戏节改以双年展的形式运作,自认剧场常客的我总是与它擦身而过,直到今年,我才终于赶上第9届超亲密小戏节的「包栋」。没想到这唯一的一次拜访,竟已是这场奇幻旅程拉下终幕的时候。 结合各种观看角度的「动态美术馆」 因为节目序与动线规划的关系,演出时间最短(仅约10分钟)、位置离验票入口最近的《茧》(余孟儒作品);和放在相对位置、可不限时间体验的《肌构》(郑嘉音作品),很自然成为大多观众最先选择欣赏的展演。 《茧》中,饰演工匠的表演者一边工作,一边不自觉地唤醒一个四肢不全、消瘦如枯枝的偶,流转出人、物之间的幽微情感;《肌构》则引导观众把一个个鲜红地吓人的血包放上秤盘,恣意摆弄人偶的四肢,营造诡谲又趣味的黑色幽默。 这两个作品或许最为符合一般观众(譬如我)对于亲密小戏节的既有期待精巧但完整的篇幅、物件与偶与演员编织的多元视角、和极近距离的观演关系。他们温柔地将观众的视线收束在戏偶与物件的细节处,让情节与表演者不再是唯一的焦点。那些文本之外的机关部件、滑轮绳索,被自然地拉抬至与文本之内的事物同样的观看高度,让这些冰冷的造物透过观众的
-
戏剧
黑特剧场Hate Theatre所折射出的剧场面貌
在脸书的搜寻栏打上「黑特」或是「靠北」,不难发现社群平台上充斥著许多匿名评论平台,它们大多以学校、公司、职业、产业为单位的匿名粉专或社团。
-
新锐艺评 Review
当表演不作为舞台里的主角
《惊园》透过装置及视觉建构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并透过跨文化╱跨形式,不同元素的调度达到舞台呈现上的均衡,进而对剧场的概念本身提出诘问。而考量马文的专业背景,或许表演在《惊园》里的「被稀释」也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惊园》绝对是一个值得一看的优秀作品,在跨界已成显学的今日艺坛,《惊园》对表演形式的叩问确实给出了一个令人惊艳且振奋不已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