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Pi的奇幻漂流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當青年文學躍然舞台
在快速變遷的時代中,青年文學始終以其獨特的純粹性與想像力,扮演著一種跨越年齡與時間的橋梁。它不只是寫給「年輕人」的文本,更是一種提醒提醒我們曾經年輕,也仍舊渴望相信世界的可能性。 當這樣的文本被帶入劇場,它所開展的不只是另一種敘事形式,更是一場跨媒介的靈魂對話。本焦點專題以3篇不同視角的文章,探索青年文學如何在劇場中煥發生命,從幻想到現實,從童年到死亡,勾勒出一條想像與情感的動線。 第一篇〈無論如何,不要失去想像力〉,我們邀請作家陳思宏談論經典作品《少年Pi的奇幻漂流》。這是一部看似充滿奇想的小說,但在陳思宏的眼中,卻蘊藏著對人性最赤裸的凝視。他指出,動物世界的暴力其實是單純的,但人類的世界,則透過擬人化投射了複雜的情感與倫理。這種由獸性映照人性的書寫,提醒我們:想像力不只是逃避現實的手段,它是一種深入現實的方法唯有保有想像力,才能直視殘酷,也才能重新定義何為「人」。 而在第二篇〈劇場裡的魔法與成長〉中,記者尹俞歡遠赴東京觀賞《哈利波特:被詛咒的孩子》,記錄了魔法世界如何隨觀眾一同長大。這齣作品不只是粉絲向的續作,更是一封寫給成長與親子關係的情書。當年的少年讀者,也許如今已為人父母,帶著自己的孩子再次走進劇場。哈利與阿不思,父與子的距離、焦慮與修補,成了許多觀眾的自身映照。正如飾演海格的演員羅比.寇特蘭所說:「50年後我不在了,海格還會在。」魔法的意義,從來不只是奇幻的咒語,也能是一種能代代傳承的情感與記憶。 最後,在〈用14年的時間,學會一個擁抱的方法〉中,深刻記錄《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這本暢銷巨作、被帶上台灣劇場舞台後,回望2025年最終巡演場的印記。本戲由資深演員金士傑與卜學亮共同演出,他們在這部講述師生、生死與遺憾的作品中,展現出劇場最深沉的力量。金士傑談到這齣戲如何讓他反思演員的神聖性 一種在舞台上承接、傳遞與釋放情感的責任感。而「擁抱」,成了這齣戲最深的意象:14年的理解、14堂課的學習,最終只是為了真正地擁抱對方,擁抱人生,使得這篇訪問像是一種續作,記錄了第15堂課的師生情誼。 這3篇文章,從不同的語境與作品切入,但共同勾勒出「青年文學」在劇場中展現的多重面向。它不只是關於年齡的文學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無論如何,不要失去想像力」──陳思宏談《少年Pi的奇幻漂流》
讀到《少年Pi的奇幻漂流》裡的狐獴島段落時,作家陳思宏到圖書館借了一本動物圖鑑。 那是網路還不普及、台灣寵物店還未引進狐獴販售的2000年初,他從未見過狐獴這種動物。圖鑑上寫著:狐獴分布於南非地區,以草原為棲地,群居動物,性情溫和。回到小說,住滿狐獴、提供水源與食物的小島,湖水卻在夜晚變成酸液,蓮花裡藏有人類的牙齒,他才意識到,可愛的狐獴島,原來也是一座吃人之島。 多年來,這段情節一直留在陳思宏的閱讀記憶裡。某年他到日本奈良旅行,公園裡有野生鹿群散步、與人互動,他原想與鹿互動,鹿卻一口咬住他的屁股,他大叫,除了是痛,也是驚訝鹿並不如想像中溫和。「我被咬了一口才知道,鹿終究是動物,有野性存在,不像人類期待的那麼溫馴。就和狐獴島上的狐獴一樣。只是動物來到了人類的想像力裡,總是要很可愛,去除全部的野性,但為什麼動物一定要可愛,才能符合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想像?」 由加拿大作家揚.馬泰爾(Yann Martel)所寫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於2001年出版,講述16歲的印度少年皮辛.墨利多.帕帖爾(Piscine Molitor Patel),在與家人搭船前往加拿大的過程中發生船難,倖存的Pi意外與一隻孟加拉虎乘上同一艘救生艇,在海上共渡227天。作者透過一名印度少年的海上漂流,討論野性、信仰與真相,小說出版隔年獲得英國文壇最高榮譽「曼布克獎」,至今銷量超過1,400萬冊。隨後導演李安將小說翻拍為電影,全球票房超過6億美金,還獲得第85屆奧斯卡最佳導演、最佳攝影、最佳配樂和最加視覺效果等4項大獎。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劇場的延續性與可能性
劇場與電影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當我們談論「改編」案例時,相對於一百多年的電影,擁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劇場直覺上似乎較容易是被改編者,例如希臘悲劇、莎劇等影像化,或是百老匯音樂劇如《歌劇魅影》、《悲慘世界》之電影版,更有由著名流行歌曲延伸的「點唱機式音樂劇」(Jukebox Musical), 如《媽媽咪呀》、《萬世巨星》等;而多對話及室內場景,較上述案例稍微小眾一點的現代戲劇,富有文學性及考驗演員功力的性質,則成了影迷印象中的「奧斯卡最愛」,上世紀中葉有伊莉莎白.泰勒主演的《靈慾春宵》(又名:《誰怕吳爾芙》),及馬龍.白蘭度和費雯麗主演的《慾望街車》等,近年安東尼.霍普金斯及布蘭登.費雪也分別以當代劇本翻拍的《父親》和《我的鯨魚老爸》封帝。 劇場演出具有實時性與現場性,無法利用剪接快速穿梭不同時空,場景較縮限且需重複利用,通常製作成本也比電影小,邏輯上而言,應該較適合做為一個樸實的基底,讓改編的影像添上花樣;然而,隨著各種形式的娛樂展演逐漸混雜,分眾狀況不再那麼明顯,再加上新的科技和技術引進劇場,也不乏反過來的例子電影先獲得成功後,再改編成劇場作品。 《舞動人生》:從電影、劇場再回到大螢幕播映 以《時時刻刻》、《為愛朗讀》及影集《王冠》為人所知的英國名導史蒂芬.戴爾卓(Stephen Daldry),其首部劇情長片《舞動人生》(Billy Elliot,2000),講述渴望學習芭蕾舞的礦工之子比利,克服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及家裡給予的陽剛期待,在舞蹈老師喬治娜的幫助下參與甄選、進入專業學校就讀,逐漸改變父親的反對態度並獲得肯認,一步步成為耀眼的芭蕾舞者。 該片將男孩成長心境放置在1984至1985年英國礦工大罷工的社會脈絡中,藉少年柔軟卻堅韌的氣質,撫慰緊繃過勞的藍領階級家庭,取得1億票房佳績。14歲新人傑米.貝爾更是擊敗羅素.克洛、湯姆.漢克斯等資深男星,成為史上最年輕的英國影藝學院電影獎(BAFTA)最佳男主角獎得主。 導演戴爾卓在拍電影前已有劇場經驗。從青少年時期接觸劇場作品並擔任學校話劇社幹部,取得文學學士後,還考進東15表演學校主修表演,並在曼徹斯特、利物浦、愛丁堡等地發表劇場作品。他曾於倫敦的Royal Cou
-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請回答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請回答當大船入港……商演浪潮下的台灣劇場現場(上)
Q7:大型商業劇場大量來台,對其他類型表演藝術及國內團隊是否產生排擠效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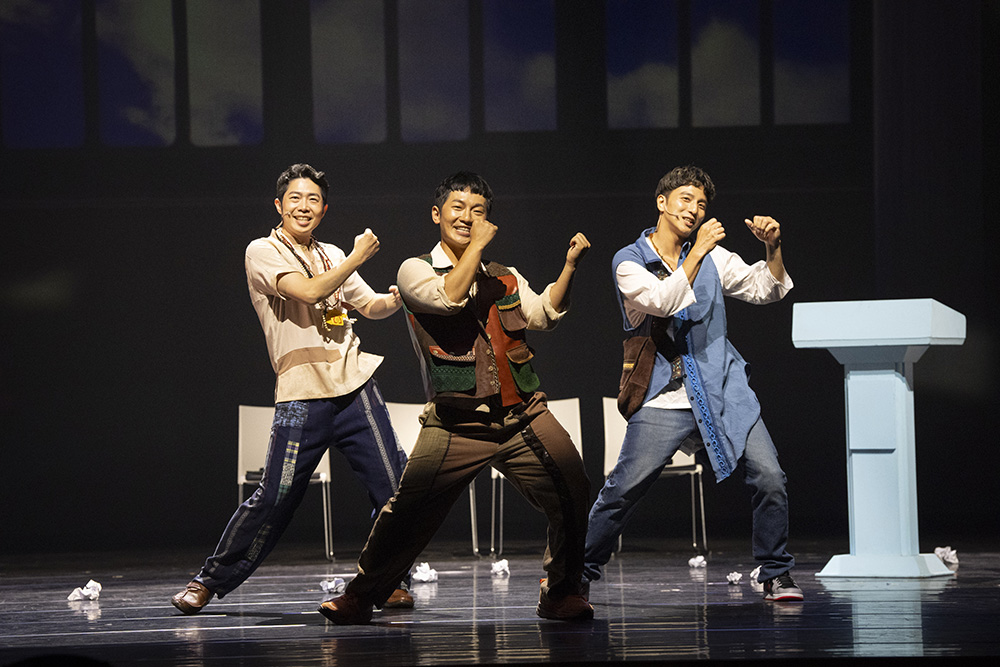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請回答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請回答當大船入港……商演浪潮下的台灣劇場現場(下)
Q7:大型商業劇場大量來台,對其他類型表演藝術及國內團隊是否產生排擠效應?
-

2025國家兩廳院展現劇場多元性 聚焦國際交流與臺灣當代議題
國家兩廳院2025年將聚焦於永續發展、多元節目製作、國際交流合作、培養藝術家與開拓觀眾族群等層面,展現表演藝術對社會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