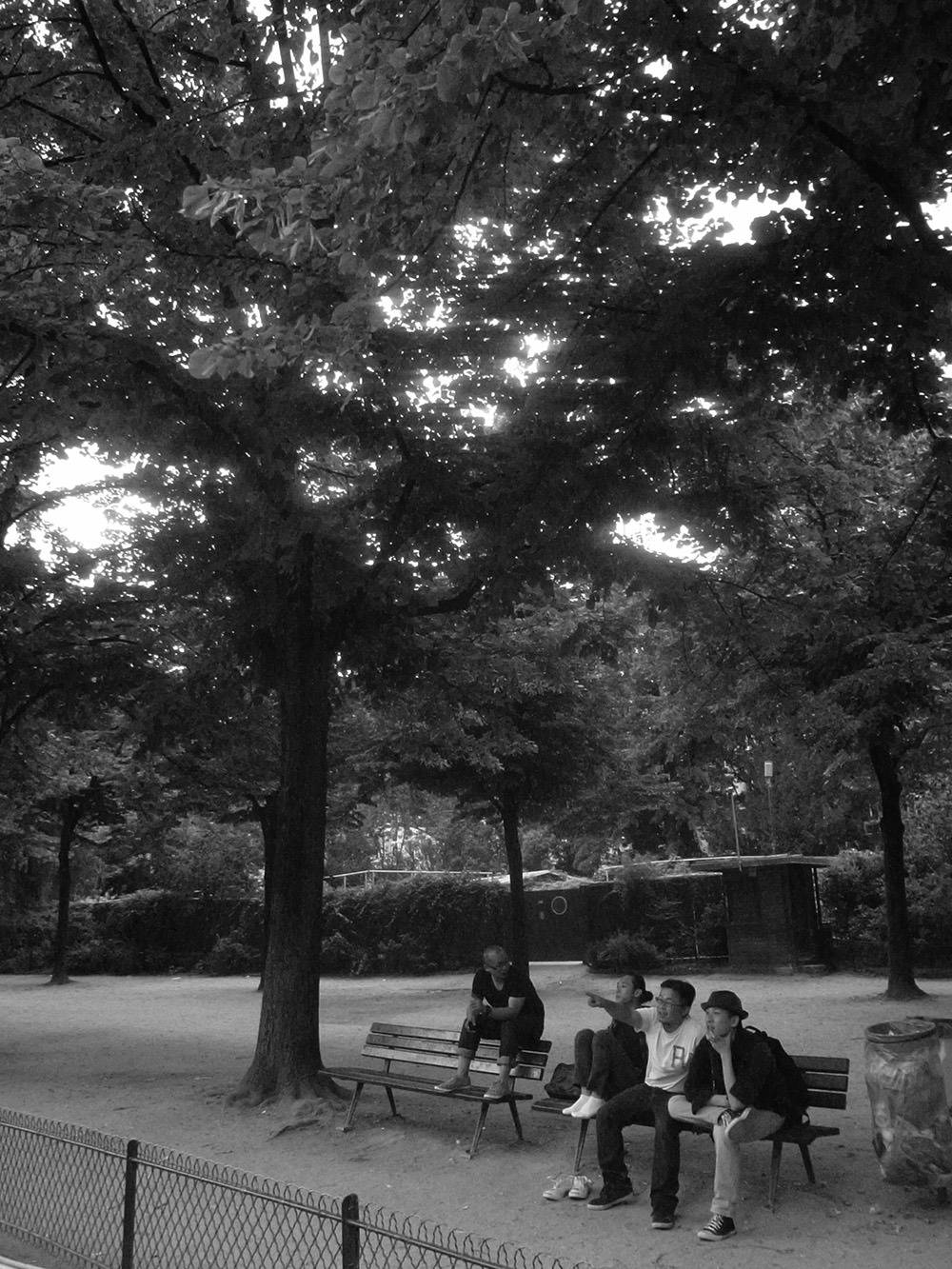Search 搜尋
-
 烏鎮
烏鎮第12屆烏鎮戲劇節閉幕 狂歡之後卻見困境?
掛滿大街的劇碼海報,街巷、河岸邊的精彩表演,人流如織的古鎮嘉年華剛閉幕的第12屆「烏鎮戲劇節」再次將這座江南水鄉變成了巨大的文化引力場。來自10個國家的25部特邀劇碼,117個古鎮嘉年華表演,超過1357位演職人員參與了這場秋日的藝術盛宴。 然而,在這繁華景象之下,一種莫名的失落感卻在熱愛戲劇的人們心中蔓延。當玩偶小黃人IP形象在古鎮嘉年華中穿梭,當9小時的馬拉松式劇碼將普通觀眾拒之門外,當戲劇節的夜生活被盛大的音樂派對接管,人們開始疑惑:烏鎮戲劇節,究竟是在藝術堅守中野蠻生長,還是在商業浪潮中亂花迷眼? 烏鎮模式:極致精緻的美學悖論 烏鎮是中國文旅產業中最成功的商業化案例,它用現代資本和技術能力,把一個瀕臨衰落的傳統水鄉,打造成了無與倫比的精緻產品。烏鎮的統一營運模式達到了登峰造極的水準:收購所有房產,遷出原住民,以「修舊如舊」的標準修復重建。 「一店一品」政策杜絕了基層的重複業態,服務員、船工統一培訓之後上工,連影響空間流暢性的電線杆也被全部拆除。這種極致的管理美學,使遊客能夠獲得標準化的完美體驗,但也徹底犧牲了一個活態社區的草根性、有機性和真實性。 在烏鎮,所有驚喜都是被設計好的,所有探索都是在既定規劃路徑上進行的,但生活的真實感卻消失殆盡。這種物理真實與生活真實之間的悖論,正是烏鎮模式的根本困境。
-
 藝號人物 People 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劇場導演
藝號人物 People 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劇場導演呂柏伸 創作與教學共振 見證不同階段的戲劇之路(上)
「如果我們對外徵求藝術總監,你覺得會有人來應徵嗎?」身為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的呂柏伸話鋒一轉,提出這個疑問。 真的,是個問句。 「沒有人做過這個事情吧?我一直很想,但怕大家覺得我在開玩笑。」呂柏伸說得頗嚴肅,也坦然地說:「我現在眼睛不好,不過演員們反而覺得我好像聽力變好了。」看似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看似雲淡風輕,卻難掩在年紀增長之時,更代表他已在這個職位超過20年。 比劇團藝術總監更久的是,他在大專院校任職的時間,從兼任到專任於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創作與教學,兩條生命軌跡彼此交疊,似乎構成「呂柏伸」,同時也見證他在不同階段的自己。
-
 藝號人物 People 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劇場導演
藝號人物 People 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劇場導演呂柏伸 創作與教學共振 見證不同階段的戲劇之路(下)
「戲劇創作、或藝術創作這件事情,經驗傳承是很重要的。」呂柏伸或許在劇團與學院擔任不同角色,但兩者有明顯交會。但現在的他,似乎更強調的是「陪伴」,「看學生創作時,就是給意見,陪伴他們。」他也說這是自己面對學生的不同階段,「以前比較看不開,對他們的要求很嚴厲,但這幾年已不是這樣,有時候覺得不是你選擇劇場,而是劇場有沒有選擇你?」而呂柏伸認為,不是非得做劇場不可,很多學生未來有不同出路,「戲劇訓練不一定是人才培訓,而是在訓練他們像是如何跟人合作之類的這些事情。」(註1) 另一個角度則是在劇團裡頭提供新一代創作者接軌實務的空間。 比較久之前的案例,是在中山大學時期,讓黃建豪加入《K24》,成為他表演經驗快速累積的關鍵(註2);另外像是即將於台南人劇團版《服妖之鑑》中飾演許湘君的演員陳映亘,就是參與臺大戲劇學系2023學期製作《服妖之艦》後,被挖掘的新生代演員,呂柏伸說:「她今年剛畢業,讓她可以跟崔台鎬、楊迦恩等這些成熟演員一起工作,進步絕對是比在學校來得快很多。」還有與青年導演、編劇的合作,也間接改變了台南人劇團本身的創作軌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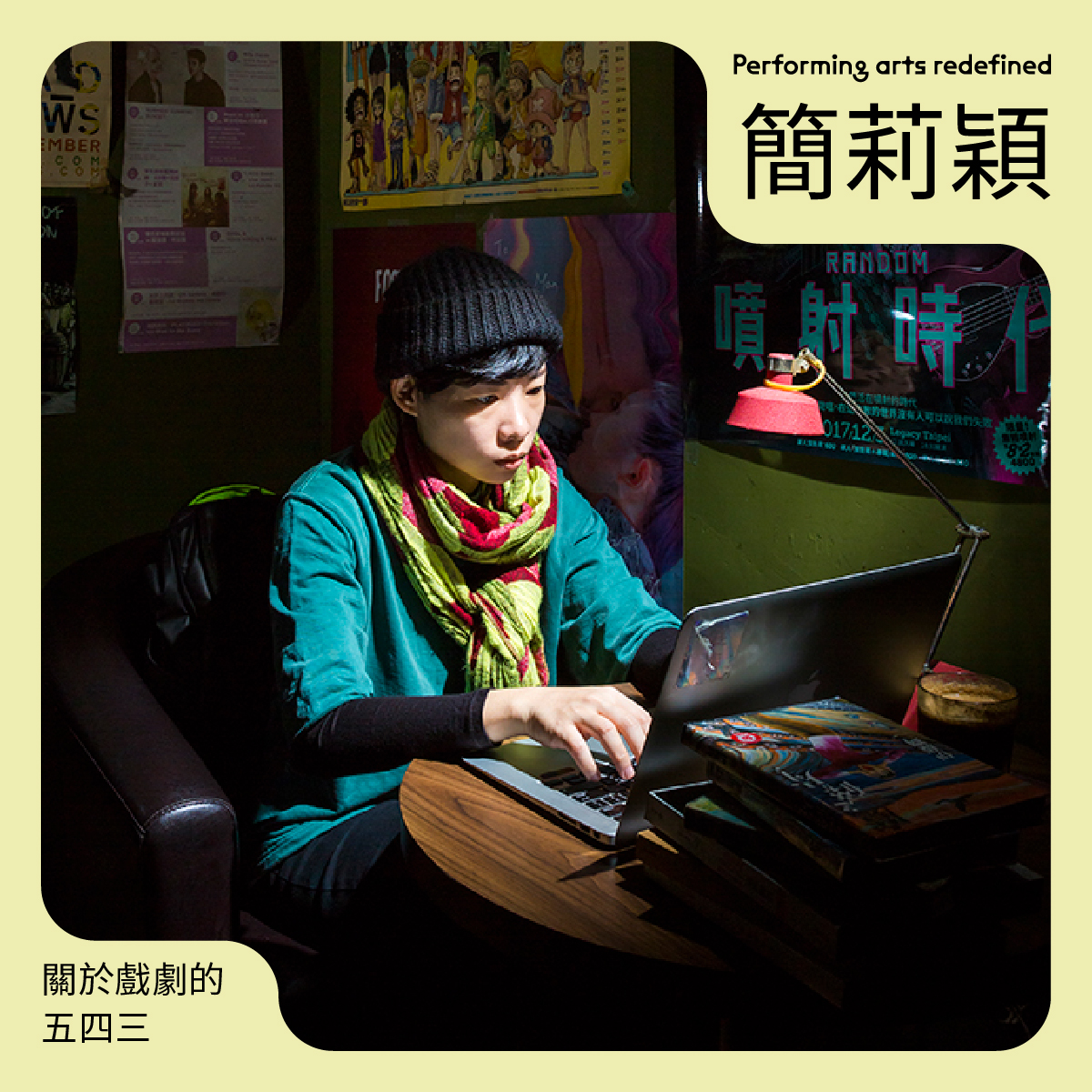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喜劇與恐怖一線之隔
(黑畫面)「這是個真實故事,兩年前就發生在我的小鎮,很多人以奇怪的方式死掉這個故事從我的學校開始。」(學校畫面)「梅布魯克小學從幼稚園唸到5年級,一個平常的禮拜三,有一位新來的老師。」(主角跟拍畫面)「她的名字是潔斯汀.甘迪,她在那一天走進她的教室,就像每個早上一樣,但今天不一樣。」 「別班的孩子都到了,就連貝爾老師教的另一個3年級班都坐滿學生,但甘迪老師的班級空無一人,除了一個男孩,他的名字是艾力克斯.利里,他是班上18個孩子中,唯一去上學的小孩,知道為什麼嗎?」 (家中畫面)「因為前一晚,凌晨2點17分,每個小孩都醒過來,」 「下床,走下樓,打開前門,走出前院,走進黑暗,再也沒有回來。」 伴隨著小孩說故事的童音,音樂進,暗夜籠罩的美國郊區住宅,一群孩子以類火影跑(漫畫火影忍者的跑姿)之姿,衝出前門,在空蕩蕩的大馬路上狂奔。 恐怖電影《凶器》(Weapons)的開場,今年看的新片中,最喜歡的開場,沒有之一。 整部片從學生失蹤的那個早晨開始,以人名字卡切換,第二段跳到尋找孩子的父親、接著是偵辦此案的警察、商店門口無所事事的毒蟲、校長、男孩艾力克斯,帶出一個看似老掉牙的吹笛人故事。在看完全片後,讓人驚覺原來整個失蹤案的兇手早就出現了,是一部值得回頭二刷發現細節的電影。 順敘會讓這個故事普通,但敘事的形式即是內容,伊底帕斯王的故事若從頭開始講易流於流水帳,且犧牲了最懸疑的部分,正是這種敘事的巧思,視角的跳躍使得《凶器》免於大多數恐怖片會有的問題:主角降智,看起來詭異的地方硬要進去,無止盡的嚇人鏡頭(Jump Scare),《凶器》展示出真正恐怖的事情 「當人們平靜日常被破壞的瞬間」。 看完《凶器》,立刻找了編導的首作《宿劫》(Barbarian)來看,驚為天人,用3個主要角色,把「地窖裡有怪物」這類經典的恐怖片類型做出新意,一棟普通的民宿,有多少暗黑的過去,編導Zach Cregger非常擅長沉浸的鏡頭、恰到好處的劇情斷點,透過鏡頭外的聲音,想像力營造出巨大張力,透過多線,怪物出現就卡掉鏡頭,跳到下個角色,完美避免角色如何逃過怪物攻擊的疑惑,掛心角色之後的命運。本
-
 話題追蹤 Follow-ups
話題追蹤 Follow-ups與時間賽跑!! 衛武營啟動「臺灣舞蹈記憶地圖」4年測繪計畫(上)
「2008年雲門大火後的那一個月,我的領子裡全是燒焦的煤炭味。」 舞評人陳品秀在「臺灣舞蹈記憶地圖」座談會上回憶起那場燒去許多珍貴文物的大火,談當年如何與雲門夥伴分秒必爭地從火場中搶救一張張因熱火黏糊在一起的老照片等各種文物,將眾人拉進了驚心動魄的歷史現場,也直接陳述了要保存稍縱即逝的舞蹈,是一項極度物理性、技術性,甚至是與時間賽跑、帶有災難搶救性質的文化工程,經不起任何意外與延宕。 在文化部「重建臺灣藝術史 2.0」政策支持下,2025「臺灣舞蹈記憶地圖」計畫正式於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啟動,4年計畫將從「舞蹈家口述歷史研究」、「人才培育與作品轉譯」、「線上及實體成果展示」、「大眾推廣與舞蹈欣賞」等4大面向,書寫、繪製、推廣台灣舞蹈記憶座標。藝術總監簡文彬表示,該計畫將以文建會時期的「台灣大百科舞蹈類詞條」、國藝會「臺灣當代舞蹈年表」,還有台灣舞蹈研究學會等中央與地方機構、民間團體的研究與發表為基礎,繼續進行台灣舞蹈家的口述歷史還有主題式研究,並「延伸為人才培育和推廣活動,活化台灣舞蹈歷史,讓舞蹈的故事、知識普及」。
-
 話題追蹤 Follow-ups
話題追蹤 Follow-ups與時間賽跑!! 衛武營啟動「臺灣舞蹈記憶地圖」4年測繪計畫(下)
陳雅萍指出,過去無論是文建會主導的舞蹈史研討會還是口述歷史出版物,多半是點狀的、單打獨鬥的,台灣至今缺乏像紐約公共圖書館表演藝術分館那樣具備系統性蒐集、分類、並能支援研究與教育的舞蹈專門檔案中心。她強調第一手資料的保存至關重要,呼籲台灣應開始思考並努力建構能夠讓舞蹈研究深耕、推廣的檔案機構,從歷史連結、形塑未來。
-
 宇航的戲曲手記
宇航的戲曲手記戲劇的陽光評論
藝術評論遠不止是藝術評論家的專利,無需組織文章,從興趣盎然國中生到看戲半輩子的資深觀眾,更多的普通戲友拾起筆來,就他們感興趣的藝術作品評頭論足,甚至有小論文般的長文,更不要說其中上下5千年引經據典的知識含量,讓專業人士大開眼界,讀一篇文章,長一番見識。讓我或者說讓更多的藝術從業者領略到善良的藝術評論對藝術創作的正面推動作用。
-
 戲劇
戲劇一場重新編織的夢,讓你看到窗外了嗎?
1963年,時年25歲的瓊瑤(本名陳喆)以當時仍為社會禁忌的「師生戀」為題,寫出一鳴驚人的處女作《窗外》,自此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豐富創作生涯,以浪漫愛情為題的長篇小說,和據以改編的影視作品,都廣受閱聽大眾喜愛。瓊瑤女士的小說與影視作品,無論各方評價如何,對台灣當代社會的影響,有成篇累牘的研究論文為證,對許多1960、70年代的青年學子來說,閱讀瓊瑤小說,也是重要的啟蒙經驗文學的、情感的、自我意識的。即使年歲漸長,美好記憶漸漸褪色,但曾經有過的guilty pleasure卻也不容否認。 由寬宏藝術與美亞娛樂共同出品,表演工作坊文創製作的《你的故事我的夢》,首度將瓊瑤作品搬上舞台。編創者以「解構與重構」之名,從《窗外》與《一簾幽夢》取用主要角色與部分故事內容,用平行剪接概念串聯分段場景,構成相互呼應的雙重敘事。《窗外》中的江雁容在暗戀的老師康南被迫離開學校之後,大學落榜,決意自殺卻又未遂,之後與父親愛徒李立維結識成婚,婚後生活不順,兩人矛盾日深,終至離異;離婚後的雁容走尋康南行跡,卻只瞥見他的憔悴身影,醒悟青春不再,毅然出國。《一簾幽夢》裡的汪紫菱是江雁容高中同學,雖然自小因為姊姊汪綠萍的耀眼光彩而被忽視,但之後與綠萍的青梅竹馬楚濂暗自相戀,又在家庭宴會上吸引父親事業夥伴費雲帆的目光,相對的,原本要風光出國留學習舞的綠萍,卻在一場嚴重車禍中失去左腳。綠萍在夢碎的悲痛中接受了心懷愧疚的楚濂求婚,心碎的紫菱則答應了費雲帆的求婚,並與他遠走歐洲旅居。綠萍與楚濂的婚姻,成為彼此的煎熬折磨,終於在紫菱返國探親時,於父母面前爆發無可挽回的衝突,離異之後的楚濂對紫菱提出重新開始的試探,卻反而讓紫菱與費雲帆更深刻理解彼此真心,互許「共此一簾幽夢」,綠萍也終於能放下痛苦怨懟,遠走海外尋夢。
-
 話題追蹤 Follow-ups
話題追蹤 Follow-ups踏上古老且陌生的國度 敲響傳統與創新
朱宗慶打擊樂團(以下稱朱團)明年1月即將邁向 40 周年,這無疑是值得慶賀的里程碑。然而回望過去,這段歷程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無數努力與奮鬥而來。作為一個民間團體,樂團甚至一度思考過存亡的問題。朱宗慶坦言,樂團的價值「不能以數字衡量,而應從歷程來看」。 回顧全球發展歷史,打擊樂團能延續至 40 年者極為罕見。朱宗慶指出:「從歷史法則來看,全世界的打擊樂團幾乎沒有超過 40 年的例子。」他回憶 2022 年赴美時,曾親眼見證過去極具代表性的阿馬丁達打擊樂團(Amadinda Percussion Group)在一場演出結束後,當場宣布解散。自此之後,除了已走過 63 年歷程的史特拉斯堡打擊樂團(Les Percussions de Strasbourg)之外,以職業型態運作超過 40 年仍持續運轉的團體,放眼全球也僅有史特拉斯堡打擊樂團與朱團。 3年疫情時期,朱宗慶打擊樂團同樣受到嚴苛的考驗。直到 2022 年赴美巡演時,他深受鼓舞:「那次演出共有5首作品,每一首都獲得全場起立鼓掌。那兩千位觀眾不是一般民眾,而是來自世界各地頂尖的打擊樂家。」然而回台不久後,樂團便遭遇火災。朱宗慶回憶:「當我們以為終於站上高峰時,一場火災發生,但我們第一個決定就是不打悲情牌,要勇敢活下去。」 2022 年 4 月 2 日,朱宗慶卸下國表藝董事長之職回到樂團,立下決心要陪伴團隊完成轉型與再生。他推動名為「動能循環」的計畫,花了半年時間,要求所有團隊成員每日撰寫公務日誌,從中徹底了解樂團內部運作狀況。朱宗慶坦言:「朱團表面看似良好,實際上包含基金會、教學總部等,加起來約兩、三百人,內部挑戰非常大,這對我而言是極大的考驗。」 在這樣的覺察中,他開始思考如何帶領樂團走向下一階段。於是誕生了所謂「倒數 1000 天」的行動計畫(編按:從40周年倒數),其核心是一次根本性、革命性、翻轉性的改變。不僅要翻轉朱團的歷史,也要翻轉整個系統,包括樂團、基金會與教學體系的全面革新。 創團以來,朱宗慶始終以「現代與本土、傳統與現代」為藝術核心理念,並認為唯有主動尋求與世界的交會與創新,才能推動藝術永續發展。他說:「我們的改變,就是想辦法從世界各地匯集、交流、創新。」因此,他們在多重事物的進行之中,以「奧德賽計畫」為名出發,
-
 藝@書
藝@書公共性的臨界:劇場在制度與資本之間的未來考驗(上)
由本刊所出版的《表演藝術年鑑》系列專書,長期以來透過每一年度資料的積累整理,呈現該年度的表演藝術生態樣貌,同時,也期望透過年鑑所彙集的資料與數據,作為現況分析的基礎,並邀請專人透過資料與事件的爬梳撰寫專文,提出對當年度的整體觀察與思考。 在今年本刊更是將已出版的歷年《表演藝術年鑑》共31本,進行數位轉型,以版面資料庫的形式供讀者閱讀。而最新的《2024年表演藝術年鑑》已於近期完成製作並上架,本站特地轉載書中年度觀察專文,以饗讀者。
-
 藝@書
藝@書公共性的臨界:劇場在制度與資本之間的未來考驗(下)
資本化觀察(1):創業語境下的台灣劇場生態 當文化政策以「創業者精神」或「文化內容產業」作為推動劇場生存的口號時,實際構成的是一種「無資本的資本化想像」:表團被鼓勵登記立案、建立品牌、提出營運計畫、發展收入來源,彷彿只要具備創業語言就能進入文化市場。但台灣劇場的現實是:缺乏風險資本、觀眾市場小、製作成本高,幾乎所有創業想像都僅存在於補助表格裡的模擬現實中。 如哈拉瑞在《人類大命運》中所言,現代社會的主導邏輯早已從政治轉向資料與資本。創作者若無法產生可轉換的資產(如平台流量、投資回報),就無法在經濟秩序中擁有位置。劇場團隊被當成創業者,卻從未獲得創業該有的「風險共擔機制」與「中介投資結構」,只能年年提案、補助、結案、歸零。 從傅柯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資本化治理」實則是一種規訓:劇場團體被制度要求逐漸內化特定的行政語言與產業符號,進而生產出制度預期的文化表現樣貌。 換句話說,劇場團隊變成了制度內部的文化生物:不是真正的產業主體,也無法成為純公共性實踐者。他們以產業語言包裝補助行為,以品牌外型取代文化意圖,以營運策略裝載創作焦慮。這樣的資本化是幻象,但這幻象卻逐步塑造了劇場的制度現實。 資本化觀察(2):補助與自籌下的治理日常演變 公共場館與劇場團體,在今日的文化治理邏輯中,被要求同時扮演補助接受者與自籌責任人的雙重角色。一方面依賴補助完成製作、支持營運、支付人事與場地,另一方面又被要求提高自籌比例、發展收入策略、證明非依賴性與市場整合能力。表面上,這似乎是一種漸進式的財務責任轉移;但實際上,它構成了文化場域中資源合法性與治理主體模糊的關鍵矛盾。 補助款究竟是什麼?是政府的資產?是人民的稅收?是公共預算?還是社會投資?這個問題看似會計性質,實則是國家與人民之間使用權與分配權關係的核心問題。當文化單位接受補助時,往往被告知必須負起更多營運自主責任。但若補助是來自納稅者、來自全民的公共預算,那它便不是國家的私產,而應是一種代行信託的使用權責。這也突顯一個制度深層的治理問題:誰擁有文化資源的分配權?又是誰定義「合理使用」的標準?
-
 戲劇
戲劇在現身與再現之間
從「南洋姐妹會」到「南洋姊妹劇團」,夏曉鵑帶領的外籍新娘草根社會團體,1995年開始的識字班,2003年成立南洋姐妹會,2009年成立劇團,透過劇場訴說姊妹的生命故事,至今走過22個年頭,算是台灣從社會草根組織發展成民眾戲劇團體的重要案例,除了實踐民眾戲劇作為一種文化行動之外,在歷年的展演下來,她們也發展出從真實自我生活提煉而來的獨特美學。 此次的《渡海.度老》由帶領石岡媽媽劇團的李秀珣擔任導演與劇本改編。從演後談分享的工作方法與展演的全貌來看,編創排練過程還是依循民眾劇場方法,以導演帶領大家共創共制為主軸,從各自的生命體悟出發,最後彙整出了一台素樸但卻動人的好演出。 演出雖然以雷蒂娜女士跟女兒李曉婷為主軸,但中間穿插多人多線平行交織的情節,形成一種多音複調,眾生百態的展覽式結構,而非一個單線起承轉合的閉鎖式完整結構。演出尚未開始,姊妹們合唱的歌謠便迴盪在劇場裡,滄桑的聲音追問著:「天茫茫,地茫茫,無邊無際太平洋,月光光,心慌慌,故鄉在遠方」歌謠唱出外配離鄉背井的辛酸,也對現場的觀眾們訴說身無可棲的淒涼。然而歌聲不僅只要訴說情感,還要追問,帶出演出作為一種提升社會意識的訴求。燈亮,演員姿態萬千地從舞台的不同方位登場走位有的滑直排輪移動過場,有的枕著枕頭用身體毛毛蟲一般橫斜過去;有的戴著面具,有的穿著水袖;有的仗著輔具單腳行走,有的推著輪椅出場。最後眾人匯集到了舞台中央,圍繞著輪椅形成一幅靜態的塑像群,演員爬上了輪椅,手持釣竿釣著前方的紙鈔。這個頗具詩意的開場明顯是從民眾劇場的「慾望彩虹」、「靜止雕像」與「意象劇場」發展而來,演員登場並非只是代言角色,而是在演員自我和創造的角色之間,打開了現身的空間,讓觀眾看到各自紛呈的慾望彩虹,以及在這個彩虹光譜背後無形的社會結構力量。新住民及其二代,在這個現行社會結構下,往往被到台灣撈金的刻板印象所烙印,在夾縫裡求生的非戰之罪往往是主流社會凝視之眼下的壓迫結果,從輪椅起身爬上釣錢,這個靜止的意象作為開場的定鑼聲,搶眼是搶眼,卻令在觀眾席間凝視他們的我們感到深深不安。
-
藝@展覽
在宇宙寫生找尋共鳴的心跳
成軍15年的「豪華朗機工」是台灣視覺藝術界的異數,4位成員:張耿豪、張耿華、陳乂和林昆穎都是藝術家,各自創作風格鮮明,當「合體」為團隊時,作品既呈現多樣面貌,同時又具有「豪華朗機工」的辨識度。這次以團隊「個展」為名舉辦展覽「宇宙寫生」,透過14+1件作品梳理創團15年的軌跡之外,也清晰勾勒出他們的創作關懷,這些融合音樂、科技、文本、影像、裝置等元素的作品或流露日常抒情,或回應公共議題。 「宇宙寫生」開展以來吸引觀展人潮絡繹不絕,特別是年輕族群。而究竟,主觀意識強的藝術家如何達成「4 in 1」的多功與分工?想必是不少觀眾內心的疑惑。
-
 新銳藝評 Review
新銳藝評 Review被遺忘的女性到被召喚的身體
當觀眾脫鞋、存放隨身物件、穿上黑襪,並在紙片上簽名、握住一把米、飲下通寧水時,整個入口儀式(ritual)就已經運轉起來,觀眾由「外界」切換至「儀式場域」內,其身體從觀看者轉為參與者。身體放下日常的厚重標識鞋襪、包袋、身分象徵以極簡行動(簽名、握米、飲液)作為進場契機,從而提醒:今天你將被邀請進入敘事、身體與記憶的複合體。 米在台灣文化中積累了豐富的意義:農耕、餵養、飢餓、生產與生存。當觀眾握著米時,不僅是物質接觸,也是時間與身體記憶的觸動,作品以米為物質載體,在場域中鋪陳出大量米堆,並讓舞者從米堆中「浮現」。這提醒我們:記憶、生死、愛、失落、身體或靈魂之間的纏繞是物質感的,是握在手心中的細顆,是舞動中飛散的瞬間。
-
 延長音
延長音我們與蕭邦鋼琴大賽的距離(下)
然而,成為「王者」的代價,往往是孤獨與爭議並存的。本屆蕭賽結束後,社群與媒體上的討論聲浪沸騰。有人偏愛詩意內斂,有人崇尚璀璨奔放;而更多人,其實在尋找那位能真正「征服」我們的鋼琴家。這或許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大眾的耳朵並不盲目,我們對藝術的敏銳與渴望,超乎想像。正因為如此,當結果與期待不符時,爭議便難以避免。 在如次大賽的舞台上,「冠軍」從來不只是技巧與風格的總和,更是評審、觀眾、時代審美與舞台魅力的交匯點。人們期待的不只是正確的蕭邦,更是一位能以靈魂、氣場與聲音征服時代的音樂家。這樣的魅力,也許不屬於一時的評判,而屬於長遠的記憶。畢竟,比起獎項的光環,能留在人們心中的音樂才是真正的永恆。 而這一切,也讓我們重新思考:當我們回望台灣的全國音樂比賽時,我們又在尋找什麼?是無懈可擊的技巧,還是能觸動人心的聲音?在我們的評審體系中,是否過度追求「正確彈奏音符」的思維,而忽略了藝術最珍貴的個性與靈魂?或許教育第一線現場的品味與傳承,才是我們與大賽真正的距離。 鴻溝:交錯的品味與制度 如果把任何一位蕭賽冠軍,甚至是入圍決賽的選手,放到台灣的全國音樂比賽裡彈奏蕭邦,就必然能拿到冠軍嗎?恐怕答案是非常不可能。我仔細翻閱記錄,過去10年全國音樂比賽的歷屆得獎曲目中,以蕭邦作品奪冠的選手,幾乎沒有;大多數獲獎者的曲目集中在浦羅柯菲夫、鮑文(York Bowen)、貝柯維奇(Isaak Berkovich),甚至蒙薩爾瓦捷(Xavier Montsalvatge),清一色是外向、炫技、節奏鮮明的作品,更不是古典曲目中最有深度的選擇。 在這樣的評審體系裡,參賽者追求的已不再是藝術表達,而是升學的通道。這場比賽成了「正確音符、精準節奏、夠快夠響」的競技場。音色的層次、語法、詮釋品味幾乎不在評分範圍內;反倒是誰彈得更大聲、更炫技,誰就更接近「完美」。能夠進入國際大賽如蕭賽這等水準的台灣選手,幾乎在全國賽都很難拿到冠軍,或更甚早被淘汰。這樣的標準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地方品味」一種被習慣化的錯覺。當一代又一代評審與學生在同樣的審美框架下輪迴,我們便離美的追求愈來愈遠。「對的音」取代了「美的聲音」,技巧成了唯一的語言,而靈魂
-
 延長音
延長音我們與蕭邦鋼琴大賽的距離(上)
每隔5年,當波蘭華沙的舞台再度亮起,那場專屬於蕭邦的光芒便俯瞰全球。該賽事的線上直播及頻道觀看次數屢破紀錄,2021年蕭邦鋼琴大賽(後簡稱蕭賽)的 YouTube 觀看便累計至3750萬次瀏覽、近800萬小時。媒體鏡頭從後台到舞台無孔不入,決賽門票甚至於開賣後數分鐘內售罄。這是全世界最受矚目的鋼琴比賽,也幾乎是鋼琴家一生所追求的最高殿堂「蕭邦大賽冠軍」幾乎等同於「時代鋼琴家」的代名詞。從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到齊瑪曼(Krystian Zimerman),無不因蕭賽而一舉成名,立為典範。 事實上,不只蕭賽,全球每年有超過300場國際大賽,規模、獎金與音樂會機會不遑多讓,例如伊莉莎白大賽與范.克萊本大賽。但許多同時獲得多項國際賽入選資格的選手,最終可能還是選擇只參加蕭賽,就為一搏全球最大能見度。它不僅是比賽,更是「成為世界級鋼琴家」的象徵儀式。 我們與蕭賽的距離 如此盛會,台灣自然不能缺席。以我自己的經驗為起點:2000 年,我曾參與蕭賽並進入第2輪。當年評審之一阿格麗希,還特別對許博允老師提到對我的演奏印象深刻。早期資料不易考證,但據我所知,前輩如陳宏寬、陳瑞斌等人,也都在蕭賽中創下不凡成績。 但是顯然的,能夠獲得參加蕭賽的資格就已難如登天,更不用說能夠得獎。2015 年,台灣僅有兩位選手晉級錄影預選輪(註1),其中一位是我的學生詹心柔;2020 年,已有9位台灣選手進入錄影預選輪,其中數位曾受「國際大師鋼琴藝術節」(International Maestro Piano Festival)(註2)的洗禮,最後3位晉級至第2輪;到了 2025 年,有3位台灣選手進入第一輪,張凱閔最後挺進第2輪。可見,基層的音樂教育與國際連結還是進入國際舞台的重要推手。若說這代表我們與蕭賽的距離愈來愈近,也無不可。 最難的一關,是踏進第一輪 不為人知的是,大賽中最艱難的關卡其實是「進入」比賽本身。我曾擔任多場國際比賽的預選評審,例如韓國的「尹伊桑國際音樂大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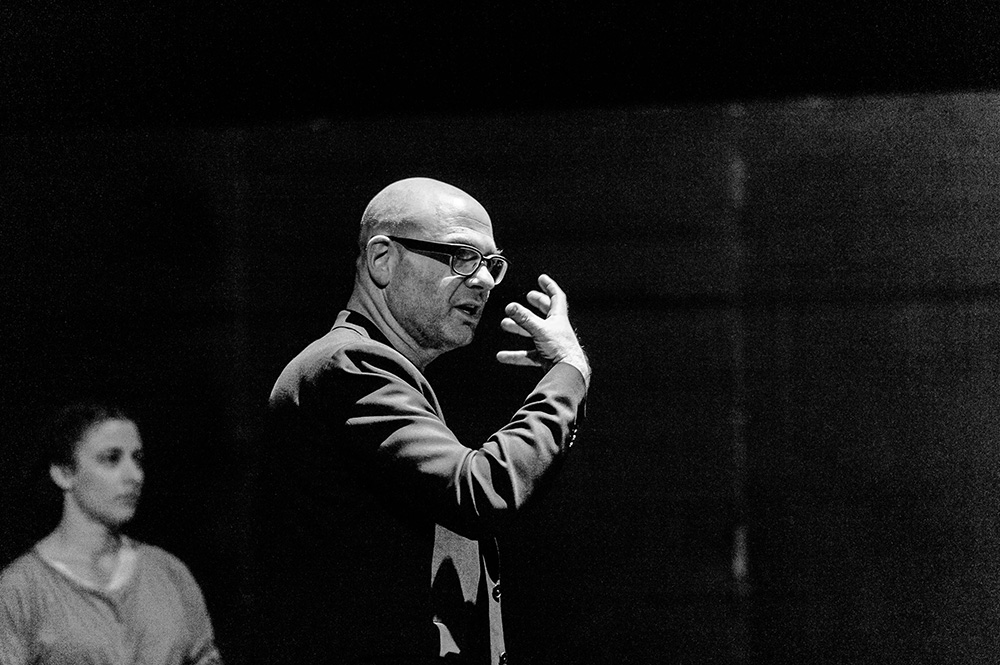 藝號人物 People 澳洲瑟卡馬戲團藝術總監(上)
藝號人物 People 澳洲瑟卡馬戲團藝術總監(上)雅倫.萊弗許茲 從局外人到專業馬戲之路
接受視訊採訪的這一天,雅倫.萊弗許茲(Yaron Lifschitz)正處在兩場排練的空檔。鏡頭裡的他一邊吃著簡單的午餐,一邊侃侃而談,顯得忙碌卻絲毫沒有疲態;語速敏捷、思緒清晰,在長年創作與營運壓力下,仍充滿感染力與能量。畢竟,他所領導的「瑟卡」(Circa),是一個擁有近 70 名藝術家與工作人員、足跡遍布全球的當代馬戲團隊。 瑟卡誕生於 1980 年代的澳洲布里斯本,它的前身「搖滾馬戲團」(Rock n Roll Circus),是一個標榜「不守規矩、略帶叛逆」的小型團隊。1999 年,剛從澳洲國家戲劇學院(NIDA)畢業的萊弗許茲以門外漢之姿加入團隊,並在 2004 年推出3人作品《空.間》(The Space Between),逐步改寫團隊的發展方向,也奠定了今日瑟卡 的創作軌跡。 在萊弗許茲的帶領下,瑟卡展現了一種跨越馬戲、舞蹈、劇場與音樂的身體美學:編舞式的鋪排、極簡的視覺、強烈的當下性與體能真實。此外,更持續跨界合作,拓寬馬戲的邊界,例如《Opus》(2013)讓4位絃樂手在雜技演員之間移動演奏蕭斯塔可維奇的樂曲,《回歸》(The Return,2015)重新詮釋了蒙台威爾第(Claudio Monteverdi)歌劇,回應當代難民議題。 將在台灣上演的《Humans 2.0》延續 2017年《Humans》的提問:「作為人類,我們究竟能承受多少?我們能背負多少重量?我們能信任誰來支撐我們的負荷?」特別在疫情後,「接觸」(touch)變得倫理化、政治化的世界,萊弗許茲重新審視人類的脆弱、秩序、混亂與連結。11位馬戲演員在3幕結構中,交織身體與情感,以彼此的重量述說信任,以危險的邊緣探問自由,以節奏與呼吸塑造人類最原始的互動。
-
 藝號人物 People 澳洲瑟卡馬戲團藝術總監(下)
藝號人物 People 澳洲瑟卡馬戲團藝術總監(下)雅倫.萊弗許茲 動作、音樂、舞蹈、敘事與馬戲
Q:身為導演,你的作品橫跨不同領域。是什麼驅動你持續創作?在每一部作品中,你始終關注的核心議題是什麼? A:我創作,一部分因為我熱愛它;另一部分因為我不安全感重,我想確保我們有作品可以做。而且我永遠對自己的作品不滿意,所以想做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們也有很多人要養活,所以我們不能只靠現有作品,市場對新的東西永遠有需求,而我們也想回應。 我覺得大部分的創作反應都來自「質疑」,或一點「不滿」。我常覺得:「上一個作品很好,但我們可能沒有找到足夠的美,那下一個作品要不要更美?」像《Humans》比較溫暖、慷慨,我就想:「那我們做一個更犀利、要求更高的作品吧。」於是做了《Wolf》。現在我又覺得我需要更多美,但不能俗氣那要怎麼找到?於是這推動我做下一個作品。 基本上每個作品都在問問題,而下一個作品試圖回答它。 Q:瑟卡的演出常以編舞邏輯思考馬戲,但你並無舞蹈或編舞背景,如何引導表演者將動作轉化為語言? A:這是一種合作。我覺得知道自己「不擅長什麼」很重要,但現在我做這行很久了,也對動作如何組合、哪裡可能有機會產生新的東西有一定感覺。 我看世界的方式和其他人不同。在芭蕾或舞蹈裡,有某些固定步伐、固定節奏,那不是我的節奏,也不是我的路徑。因此我反而學會擁抱它,那可能也是我能提供的東西。 有時候,接受自己「就是不擅長某件事」,會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
 學習老人轉彎的隱喻
學習老人轉彎的隱喻走出隧道
lhngaw(洞)之後。bqlit(膝蓋)lglug(搖晃,不穩)。a! qlahang wa (啊!要小心)。這不是 dma(夢),這是sayang(現在)。他以為lhngaw(隧道)是mhuqil(死亡,結束)。aji(不)。它只是bling(一個洞),一個bhruy(彎曲)的elug(路)。 在月球的飛船,或許還未毀滅。 那是一個石頭般的念想,懸在病態的、黃色的天空中。 它不再移動。它在等待。 啊,好可惜,如果錯過。 可惜只是一點點的感覺,更多的是驚惶。 這是唯一的洞,唯一的出口。 他們扛起土地。 他們行走不再輕盈。他們背負。 背負的不是衣服,不是食物。 他們帶著部落的記憶去看。 他們背負著部落,那片如今已是灰燼的家園。他們背負著母親和祖父的名字,那些在山中成為石頭的人。 記憶是肉,沉重。 他們在尋找最後的門。 啊!已經走了。 舊日的靈魂已經走了。 它被拋棄在隧道裡。 hngak(氣息)。第一口氣,是鐵鏽。第二口氣,是燒焦)。整個dxgal(土地,星球)都在 shngak(喘息)。 世界翻轉了。翻了過來。 世界的規範已然崩毀。 這場變化並不乾淨。 它像一支三叉箭,刺入,將身體與心靈強行撕裂。 我們成為癌細胞。受詛咒的膿瘡。 容易被驅使,也時常被利用。 我們增殖,如夏日的昆蟲,卻沒有意義。 活著。真不簡單。 在這片土地上,這片腐爛的廢土上。 金錢成為灰塵。 名譽成為垃圾。 一切都失去了顏色。 只剩身體的聲音。 它在說話,用血液的脈動提問。 怎麼那麼急著要走呢? 這具新的身體想要留下,它適應了這股鐵鏽的氣息。
-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身聲劇場團長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身聲劇場團長莊惠勻 理解混沌,就無所謂邊界
1998年創團的身聲劇場(下亦簡稱身聲),從身體出發,走過竹圍、淡水、再到國際,也跨越了音樂、舞蹈與戲劇的邊界。接下創辦人吳忠良遺志後,團長莊惠勻從演員的身體,一路走向創作者與管理者的角色。她說:「我們當前的世界就是混雜的。」所幸身聲一直都理解世界的複雜,並且甘願用純粹的身心與那複雜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