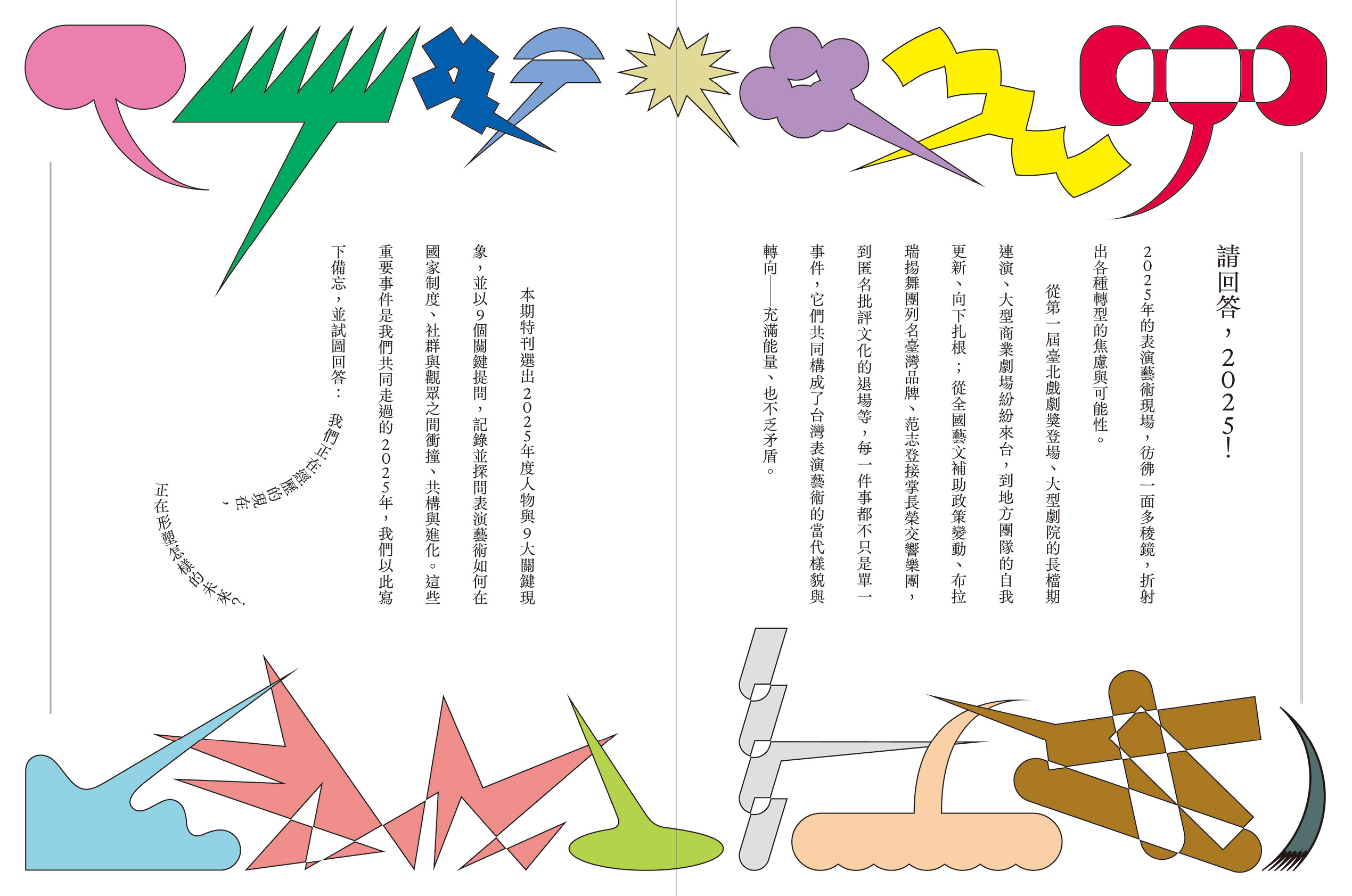英年早逝的法国当代剧作家拉高斯,直到身后才真正开始受到重视。死亡、孤独、旅程、返鄕是萦绕拉高斯作品的几个重要主题,其剧本独到之处,在于如诗句般清澈、晶莹的对白,以及反复再三的语言结构,极易上口,高声朗读有蛊惑的效果,抒情之际,又缓缓分泌细致、不易言表的思绪与复杂情感。
路易:稍后,一年过后
──轮到我将死亡──
我现在接近三十四岁,正是在这年纪我将死亡,
一年过后,
已经几个月了我等著什么也不做、自欺欺人、什么都不想再知道,几个月来我等著一切结束,
一年过后,像是有人偶尔不敢乱动,
一动也不敢动,
在极端的危险之前,难以察觉地,不想弄出声响或做一个太猛烈的手势以至于唤醒敌人立即将你歼灭,
一年过后,
不管如何,
恐惧,
甘冒这个风险而且怀抱绝无可能幸存的希望,
不管如何,
一年过后,
我决定回去看望他们,往回走,回溯我的足迹,踏上这趟旅程,
以便宣布,缓缓地,小心地,小心且精确地──我相信是如此──慢慢地,平静地,以庄重的方式──而且我面对其他人和他们,特别是对他们,难道向来不都是一个庄重的人吗?──以便宣布,
告知,
只是告知,
我逼近的、无可挽救的死亡,
我自己宣布死讯,身为唯一的信使,
而且显得
──或许我一直想要的,想要而且决定的,在任何情况下而且从我胆敢回忆的最久远以来──
显得还能够下决定,让自己还有别人,让他们,正是,你、您、她、还有我还不认识的那些人(太迟了而且活该),给自己还有别人最后一次的幻觉,觉得我对自己负责,一直到尽头,始终是自己的主人。
这长段独白是法国当代剧作家尙—路克.拉高斯(jean-Luc Lagarce)《正是世界末日》Juste la fin du monde(1990)的序曲,作者事实上是透过主角之口自我告白。拉高斯三年后死于爱滋病,得年仅三十八。这段独白的语汇简朴,具节奏感的语句一再反复,彷如诗文,口语性强,剧文关键处显得踌躇,作者面临死亡的无奈、胆怯、以及难以表白的苦痛跃然纸上,令人动容。
拉高斯生前是个活跃的人,身兼剧作家、剧团负责人、导演与出版者多重身分。他一生共写了二十余出剧本,创设「蓬车剧团」(Compagnie de la Roulotte),并在巴黎的出版社相继缩减其戏剧丛书的规模之际,协助筹设「不合时宜之隐者」(Les Solitaires Intempestifs)出版社,专门帮助新作家出版新剧作。出版社的名字出自于他的一部舞台表演作品标题。这家远离巴黎位于贝藏松(Besancon)的小出版社,现已成为当代法语戏剧创作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
然而这样一位富有能量的戏剧工作者,却直到身后才真正开始受到重视,拉高斯的命运与当代最受青睐的法国剧作家戈尔德思(B.-M. Koltès)极为类似。拉高斯的另外两部遗作──《我待在家里,我等雨来》J'étais dans ma maison et j'attendais que la pluie vienne(1994)和《遥远的国度》Le Pays lointain(1995)──直到近年才真正被搬上舞台,引起广大的回响。这得归功于长年支持他的「开放剧场」(Théâtre Ouvert),还有一些欣赏他的导演,如:Noel Jouanneau、Stanislas Nordey、Olivier Py、Francois Rancillac等人的努力。因为拉高斯的剧本独出机抒,不以剧情编排或人物塑造取胜,而几乎全赖抒发心怀的诗意言语架构剧本,剧情冲突性低,角色个性不明显,结构宛如清唱剧(oratorio),要搬上舞台演出并非易事。
在死亡的阴影下
爱滋病,一如其他无药可救的绝症,无情地将人的余生变成缓慢、痛苦的临终过程(注1)。自知日子开始倒数计时后,拉高斯一面忙著出入于医院和剧团间,一面埋头写作,导戏不辍,其中以上文提及的三出戏,以及两篇记述自己濒临死亡的散文〈当学徒〉L'Apprentissage和〈海牙之行〉Le Voyage à La Haye最受到瞩目。这两篇散文文字洗练,情感内歛、真诚,已数度搬上舞台演出,感人无数。而《正是世界末日》、《我待在家里,我等雨来》和《遥远的国度》三出戏,则为同一死亡主题的三首变奏曲。
拉高斯仿佛有预知未来的本事。早在爱滋病四处肆虐形成上个世纪最大的瘟疫以前,他就受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狄福(D. Defoe)的启发,写了一个奇怪的剧本《疯疫那年模糊的回忆》Vagues souvenirs de l'année de la peste(1982),描绘几个伦敦人如何逃离首都躲避瘟疫,以及最后决定返回的历程,如今读来,直如一出寓/预言剧。死亡、孤独、旅程、返鄕、和解/调适(l'arrangement)的议题是萦绕拉高斯作品的几个重要主题。其中浪子返鄕的母题,早在一九八四年即出现于《返回堡垒》Retour à la citadelle一剧。拉高斯毕生关怀的主题前后相当一致(注2)。
与死神的追逐
上述面临死亡的三部剧作自传性高,拉高斯借由浪子返鄕的原型发展剧情。主角路易在自知来日无多的情况下(病因并未交待),返回多年未通任何音讯的老家探望,原是想亲自宣布死讯。
《正是世界末日》分前后两部,中间以插曲间隔,首尾各有序曲和结语。路易返回阔别经年的老家,见到自己的母亲、弟弟、妹妹与首次见面的弟媳。在客套、寒暄过后,昔日的嫌隙逐渐浮上台面。「被迫」留守家园者羡慕浪迹天涯的自由与恣意,而天生的浪子却始终看似远在天边,难以亲近,冲突终于一触即发。路易决定当晚离去,行前并未透露自己的死讯。
剧中最感人处自然是作者面对死亡的心理剖析。起初,为了安抚自己,像是为了安抚一个小孩子入眠,他对自己一再说道:「其余的世界和自己一起消失,/其余的世界可能和自己消失,/消逝、被吞没,不再于我消失之后继续存在。/万物与我一起离去、陪伴我、绝不再回返。/我卷走一切,我不孤单。」(注3)然后是恐惧、失眠、不甘愿、怨恨。
再过几个月,旅行、四处游荡,像其他垂死的人用头猛撞房间的玻璃一样地慌乱与徒劳,「漂泊,已然迷途且/自信消失无踪,/跑在死亡之前,/以为已经将死亡甩在身后,/让死亡绝无可能再追得上我或知道我所在的位置」(注4)。继则假装不在乎,故作风流状。「逼近的死亡和我,/我们互相道别,/我们一起散步,/我们走在入夜后薄雾轻拢、僻静的路上相知相惜。/我们优雅、潇洒,/我们称得上非常神秘」(注5)。
然而有一天,有个人轻敲他的肩膀问他道:「有什么用呢?」「这句『有什么用』/死亡的掮客/──并未寻找我最后却发现我的死亡──」(注6),让路易警觉到逃亡的可笑与无用。他于是重返人生,面带骗人的礼貌微笑,「整理事情,理出秩序,到这里来造访,我让事情处于原状,我试著结束一切、下结论、保持心平气和」(注7)。
走到生命的尽头溯源而上,死亡的阴影无所不在,全剧的基调却不凄然,而是相反地,带点幽默、反讽的趣味,笔触优雅。在结语里,路易表示自己最惋惜的一事,莫过于在某个夏夜迷途于山谷之际,内心虽充满无以名状的喜悦,却未开口极力呐喊,让整个山谷回荡他对生命的呼唤,作者对生命的正面与乐观心态由此表露无遗。
徘徊于生死交界
于谢世前完稿的《遥远的国度》,原是在《正是世界末日》觅无发表空间之际改写的剧本。全剧的结构宛若长河,未分场次,波澜时起,生者与亡者同台,时空模糊。路易的溯源之旅如今充满鬼魅的色彩,不仅有已逝的同志恋人随行,回到家尙遇见早已作古的父亲,剧情的进展犹如一弥留者徘徊于生死交界意识模糊的状态。
本剧扩及主角交友的面相,围绕路易身边的不仅有老友「长年」(Longue Date)和他的妻子海伦,尙有「一名小伙子」(Un Garçon)代表作者过往认识的所有小伙子,以及「战士」(Le Guerrier),代表与路易交错而过的所有独行侠,他们「不愿留下任何痕迹,深怕爱慕太深以至于失足、陷入情网而痛苦不堪」(注8)。这些段落实为拉高斯大胆的情感告白,不过内容含蓄,点到为止。围绕在路易身边等他临终的一群朋友,皆意识到他们的青年时期亦随之告终(注9)。
上述角色犹如被垂死的作者召唤,从记忆的深处现身,现实、过往与幻想交叠,记忆只余片段,未来无可期待。过去的时光,宛如一个遥远的国度,再也唤不回,怀旧气息浓厚,冲突低空掠过,和解心态昭然,委婉地透露作者对生命的无限依恋。
波涛起伏的剧文
拉高斯剧本独到之处,在于其如诗句般清澈、晶莹的对白,以及反复再三的语言结构,极易上口,高声朗读有蛊惑的效果,抒情之际,又缓缓分泌细致、不易言表的思绪与复杂情感。对拉高斯而言,出口成章的对白只不过是灵巧、优雅的句子,主角看似披露了难言之隐,其实不过是和自己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而已(注10)。
的确,一个人思潮汹涌起伏时是不容易出口成章,甚或下断言,而是必得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摸索、修正,才能谈得上掌握自己的想法。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平日说话的方式,特别是碰到困难之时(注11)。
循戏剧分析的传统角度来看,拉高斯可说将戏剧语言置于情节布局、人物塑造和主题探讨之上。因此,用传统的剧本分析角度讨论他的作品,往往让人觉得剧情不够紧凑与明朗,角色面目模糊,或主题不够清晰(注12)。可是,若从戏剧语言下手分析,则让人深感意犹未尽,特别是在语言、思绪与语义之间的纠缠关系上。
就这点而言《我待在家里,我等雨来》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更能有效地将「少年人之死」的主题提升至「传奇」的境界(注13)。全剧是这样开场的:
长姊:我待在家里,我等雨来。
我望著天空就像我平日一样,就像我向来一样,
我望著天空,我还望著缓缓倾斜的田野直至远处,望著拐过森林消失不见的小路,在那儿。
这段开场白中反复出现的语汇与结构强调说话者期盼之殷切,接著话锋一转,以斜体字印行的「在那儿」三个字挑明主题之所在,十分戏剧化。说话者等待的其实不是夏日黄昏解除低压的骤雨,而是:
我等著雨落下,我希望雨落下,
我直等著,如同,以某种方式而言,我向来等著,我一直等著然后我看到他,
我等著等著,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他,那个家伙,弟弟,顺著路势转弯往上朝家里的方向走过来,我等著没有怀有怀抱任何明确的希望,我看见他回来,我等著等著就像我平时一直等著,这么多年以来,没有怀抱任何希望,而正巧就在这个时刻,当夜色初上,正巧就在这个时候他现身了,而我看到他(注14)。
女人望穿秋水等待的其实是多年以前被父亲赶出家门、自此音讯全无的弟弟,等雨心情之殷切,意味著等待手足归来心情之迫切。先说是等雨,等雨的心态接著与平日习惯性的等待交叠,而后突然瞥见久候经年的对象,在确认的过程中,等雨的焦虑、近乎绝望的等待、与至亲重逢的热切期盼等念头不停在心头翻搅,上上下下,直至化为对来者的凝视。
犹如瓦砌的组织,瓦片之间有所交叠,更有新的舖展,拉高斯的诗句亦然,往往于反复之际,逐渐变化,于高潮之时,话锋突转,直指戏剧中心所在。反复三唱的诗文,仿佛一波又一波的海浪,凝聚了无比的张力,最后产生巨大的冲击。他的意旨并非循直线进行,而是透过反复再三的技巧,盘旋而上,以求造成剧力万钧的效果。
另一方面,原文徘徊于现在式、复合过去式(passé composé)、未完成过去式(imparfait)、条件式与虚拟式之间,婉转地披露微妙的心理变化。中译文很遗憾无法在维持原文原有字序之际,同时透露这种微妙的变化。说话者仿佛无法决定确切的意思,而不断修正自己言语的时态,句子似乎围绕著意义不停打转,直到最后「目」标获得证实:看见思念多年的弟弟。
重唱的女声
不过,女人的等待完全徒劳。久违的弟弟一进门后就昏倒在地,旋即被抬到他儿时的房间昏迷不醒,近乎弥留,他从未在舞台上现身。立于台上的是他生命中的一群女人:姥姥、母亲和三位姊妹。这五个女人轮流到床边照顾他,同时回忆过去父子冲突的情境、她们无穷无尽的等待、虚度的青春,肉体的需索、村民的闲话、不切实际的希冀与妥协的未来。
她们一个挨著一个发言,叙述成分大于对话沟通,说话的方式一致,但调性(tonalité)各异,整体而言,有如一群歌队在垂死者身边跳著古典、沉缓、精致的「孔雀舞」(pavane)(注15)。死亡近在咫尺(她们后来迳称弟弟的躯体为尸体),致死之因却隐而未言。她们个别的声音不具力量,是五个女人──女人五个年龄层的化身──汇聚的声音产生巨大的回响。
《我待在家里,我等雨来》是个男人缺席(父亲亡故、独子临终)的世界。从这个观点来看,拉高斯从女性的角度改写浪子回头的神话,只不过这个浪子得了难以告白的绝症(注16),无法替久候生命甘霖的女人带来些许的安慰。
拉高斯的剧作反映八〇年代以来法国剧作家重视剧文书写犹甚于剧情编排或人物刻画的走向,让戏剧回归「话」剧的本质。戈尔德思的剧本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新生代的作家每一位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意即不同反响的文体,看似口语化,实为一种诗意的语言,十分耐读。拉高斯即借由这种诗意的口语提炼个人的经验至普遍的境界,而非一味自恋、自悲。
长年出入于生死交界的非常经历,赋予拉高斯的剧作无可比拟的悲剧力量。
注:
1. E. Ertel, " 'Etre à sa fenêtre et se regarder passer' :Lagarce à Théâtre Ouvert", Théâtre/Publlc, no. 135, mai-juin, 1997, p. 18.
2.除了自传性的题材外,拉高斯经常处理的另一题材为戏剧圈内人物或戏班子,如以契诃夫夫人为夫奔丧为题的《克尼普夫人之东普鲁士旅行》Voyage de Mme Knipper vers la Prusse orientale (1980)、以撒克斯公爵戏班子为题的《撒克斯,小说》De Saxe, roman(1985)、以及以现代剧团排演困境为题的《我们,英雄》Nous, les héros(1993)。
3. Lagarce, Théâtre complet, vol. III, Besançon, Les Solitaires Intempestifs, 2000, p. 243.
4. Ibid., p. 245.
5. Ibid., pp. 245-46.
6. Ibid., p. 246.
7. Ibid., p. 247.
8. Lagarce, Le Pays lointain, Besançon & Rennes, Les Solitaires Intempestifs & Théâtre National de Bretagne, 1999, p.36
9. Ibid., pp. 96-97.
10. Ibid., p. 105.
11.在一访谈录中,拉高斯指出自作描摹的是言语的动静,让人见识到言语如何地迟疑、误会、回溯、再继续、加油添醋、或突然之间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等等。我们平日讲话就是这番德性,尤其是碰到难以启齿之事,往往不断摸索,以期找到最合宜或最精确的话说,见L. Attoun & J.-L. Lagarce, "Vivre le théâtre et sa vie :Jean-Luc Lagarce," Théâtre/Public, no. 129, mai-juin, 1996, op.cit., p. 7.
12.以前两剧为例,我们始终不知路易当年为何不告而别?他与家人的主要冲突何在?路易最后只提及自己缺乏爱,有孤立的倾向,致使旁人难以接近他,而逐渐被迫疏远、放弃他,但其实心底仍是关心他的,而他的心底亦亟需亲情的支持,见Le Pays lointain, op. cit.,pp.106-8。这种侧重厘清思绪的台词难以舖排有力的剧情,但对于捉摸瞬息万变的思潮,则十分传神。
13.这原是《遥远的国度》的主题,见Le Pays lointain, op.cit.,p.12.
14. "J'attendais la pluie, j'espérais qu'elle tombe, j'attendais, comme, d'une certaine manière, j'ai toujours attendu, j'attendais et je le vis, j'attendais et c'est alors que je le vis, celui-là, le jeune frère, prenant la courbe du chemin et montant vers la maison, j'attendais sans rien espérer de précis et je le vis revenir, j'attendais comme j'attends toujours, depuis tant d'années, sans espoir de rien, et c'est à ce moment exact, lorsque vient le soir, c'est à ce moment exact qu'il apparut, et que je le vis". Lagarce, J'étâis dons ma maison et j'attendais que la pluie vienne, Besancon, Les Solitaires Intempestifs, 1997, p. 9.
15. Ibid., P.45. 拉高斯设想这五个女人容貌相仿,年纪相近,穿著打扮一致,尽管戏剧年龄不同,ibid.,p.63.丨
16.拉高斯向来认为爱滋病不宜当成文学作品的主题,因此他从未明白在剧作正面处理这个主题,见"Vivre le théâtre et sa vie," op. cit., p. 9.
文字|杨莉莉 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更正启事:
本刊第一〇七期《差异可观.犹是本来面目》一文,第93页文末因编辑之误有所疏漏,于此更正补文如下,并向作者、受访人与读者致歉。
台北大学都计所教授辛晚教讲评郭志贤的文章时提出「后现代」的观点,建议尊重多元价値,用不同的价値观去适合不同的消费群。兰阳舞蹈团艺术总监游源铿讲评时强调,歌仔戏若要在草台上搬演,不只要改变表、导演方式,连戏曲结构、文白唱词都得全盘重新检查,以适合草台特性,不能用室内剧的标准来硬套:「并不是守住室内剧的手段就可以挽救剧团的发展……要承认草台文本的重要性,这可能才是新歌仔戏或新芗剧的一个开始」。
由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出发思考,在电视上、在黑盒子式可以任意改变观众和演员位置甚至情感关系的小剧场里,歌仔戏的演出,也应该依循特有的美学、观众群来选择内容和形式。至于它们算不算歌仔戏呢?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曾因某些提问,对名词定义展开热烈激辩,当时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教授颜绿芬曾指出,对名称定义是需要时间的,以西方为例,有时甚至需要几百年来累积共识──这个观点或许値得思考。
风貌多元与资料整合
台湾的许多论文具体地整理了传统剧目,甚至记录分析了演出内容和形式,重量级的论文是台中师范学院音乐教育系教授徐丽莎《日治时期的歌仔戏唱腔》,她扎实地将日治时期《包公审梅花》全套八张唱片,采谱、采词,分析出歌仔戏唱腔设计的美学规律,指出这套规律仍于目前通行不坠。台大音研所硕士黄慧琥的《民权歌剧团古路戏的音乐运用──以《山伯英台》为例》、台北艺术大学传艺所硕士刘秀庭的《卖药团歌仔戏的剧目探讨》、台大戏研所硕士谢筱玫的《歌仔戏胡撇仔剧目研究》,分别研究了特定剧目的音乐、卖药团和胡撇仔戏的剧目及演出风格。在这些论文的努力开拓下,歌仔戏的剧种个性和类型特性更加清楚鲜明。九〇年代台湾歌仔戏呈现出多元混血的剧艺风貌(注2),面对现况,歌仔戏的创作者,似乎更应致力于对各类歌仔戏特性和共性的掌握,才能在多方学习、多元混血的同时,不会迷失其中,丧失自己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