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廷
序場劇本發展中心文學經理。國立台灣大學畢業,主修外文,輔修戲劇。關心翻譯、評論、編劇、構作等劇場創作與文字工作。
-
 藝@書
藝@書女神下獅城
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於晚年所寫的《夢幻劇》(A Dream Play),以印度神祇因陀羅(Indra)之女阿格尼斯(Agnes)下凡一遭的遊歷,探討苦難的本質與生命的意義。其中奇幻的角色、破碎的場景雖打破了20世紀初工整嚴謹的劇場慣例,卻也創造純粹如詩、流動如夢的質地,在劇作上另闢一條更奔放無拘的道路。新加坡劇作家亞非言(Alfian Saat)看見抵抗建制的潛能,便以史特林堡的結構概念為基礎,寫出《夢幻劇:亞洲男孩三部曲之一》(Dreamplay: Asian Boys Vol. 1),照見新加坡不可言說的男同志歷史。 審查制度的眼中釘 最早,亞非言其實是位詩人。1998年,他出版詩集《激烈時刻》(One Fierce Hour),其中一首〈新加坡你不是我的國家〉(Singapore You Are Not My Country)表達了一位青年對國家愛深責切的情感。這首詩宛如平地一聲雷,宣告著一位文壇新星的誕生,卻也因其強烈的措辭讓亞非言從此陷入愛國與否的爭議。 之後,亞非言的身分漸漸過渡成編劇,社會關懷不減反增。他熟稔地操持英文與馬文,瞄準多族裔的劇場觀眾,更藉著雙語乘載的不同觀點增添劇作的辯證層次。但,正是劇場這種公共性與政治性,讓新加坡政府找到向他設限的藉口。在《夢幻劇》送審時,政府便以劇中探討同性戀主題為由,祭出R18級的限制,以此箝制曝光與收益。2024年,亞非言更將與審查制度的長期恩怨寫成《新加坡劇場之死》(The Death of Singapore Theatre)。 老派女神下凡亂救人 如同史特林堡的原著,亞非言的《夢幻劇》以女神阿格尼斯下凡開篇,不過這次她以分不清是選美佳麗或變裝皇后的姿態降生人間。一登台,女神發覺比賽已來到問答環節,便頂著浮誇假髮義正詞嚴地說,奪冠之後,她計劃把男同志從以芭芭拉.史翠珊(Barbara Streisand)為首的偽女神崇拜中拉出來,變回陽剛的異男,導回快樂的道路。語畢,掌聲如雷。女神下凡一席話,竟變成帶著保守任務的環球小姐。 一個轉身,女神發現身邊是4位年齡、族裔各異的跨性別變裝皇后。皇后們聽聞女神的來歷
-
 藝@書
藝@書木造的船,傘造的花,人造的夢
當代媒體所描繪的北韓,往往是個獨裁、專制且審查制度鋪天蓋地的神秘國度。若不是脫北者轉述,外界可能難以想像那裡是個高官吃香喝辣、百姓食不果腹的人間煉獄。不過,即使希冀逃出北韓的人數愈來愈多,正如歷史上所有一夕之間緊急宣布的分裂,住在南韓且邁入老年的長者,會不會至今日仍盼著回到兩韓分裂前的北鄉?南韓劇作家尹美賢(윤미현,Yun Mi Hyun)便在北緯38度線的歷史裂縫中找到戲劇的破口,以此為題,寫下劇本《木舟》(목선,The Wooden Boat)。 從詩人到編劇的帥氣轉身 成為劇作家之前,尹美賢其實一直以詩人與小說家的身分自居。對她而言,文學是由詩歌與小說共創的景緻,而劇本並不在視野裡,一直到研究所時期她才有了與這個文體的初相遇。可惜,沒有劇本讓她動心,於是她決定提筆寫出自己喜歡的作品,獨幕劇本《我們可以見個面嗎?》(우리 면회 좀 할까요?)如此誕生。 尹美賢本想淺嚐即止,回頭徜徉在詩歌與小說的世界,沒想到《我們可以見個面嗎?》奪得2012年韓國劇作家協會(한국극작가협회,Korean Playwrights Association)劇本獎。自此,新歡變正緣,她便在南韓劇場以劇作家的身分打滾至今,10幾年間也陸續發表了橫跨話劇、歌劇、音樂劇的作品,包含《菜園殺手》(텃밭킬러)、《德州姑姑》(텍사스고모)以及《木舟》。 死前,能不能回去北方? 《木舟》的故事源於90幾歲的老蔡。老蔡在兩韓分裂前將妻小留在北韓,隻身一人跨過停戰線,不料一別就是一生。縱使物是人非,他在死前的遺願還是與家人相聚。但,不論老蔡申請官方的南北離散家族重聚計畫,或找上已有30多年偷渡經驗的仲介,最終屢屢敗露。某天,新聞報導日本大和堆海域停了幾艘北韓漂來的漁船,聞此,老蔡決定劍走偏鋒他要想辦法搭上這些幽靈船。船怎麼來,他就怎麼去。 老蔡的思鄉之情蒙蔽了他的雙眼,看不清鄰居老馬正在暗處動著歪腦筋。老馬是80幾歲的詐騙慣犯,出獄後雖開了一家房屋公司,但一鎖定目標就想敲一筆。老馬嗅到老蔡身上的商機後便開始找隊友,第一個對象是無名的「運動服青年」,善於讀書考試,卻因太內向而無法上班,只能以出租證照度日;第2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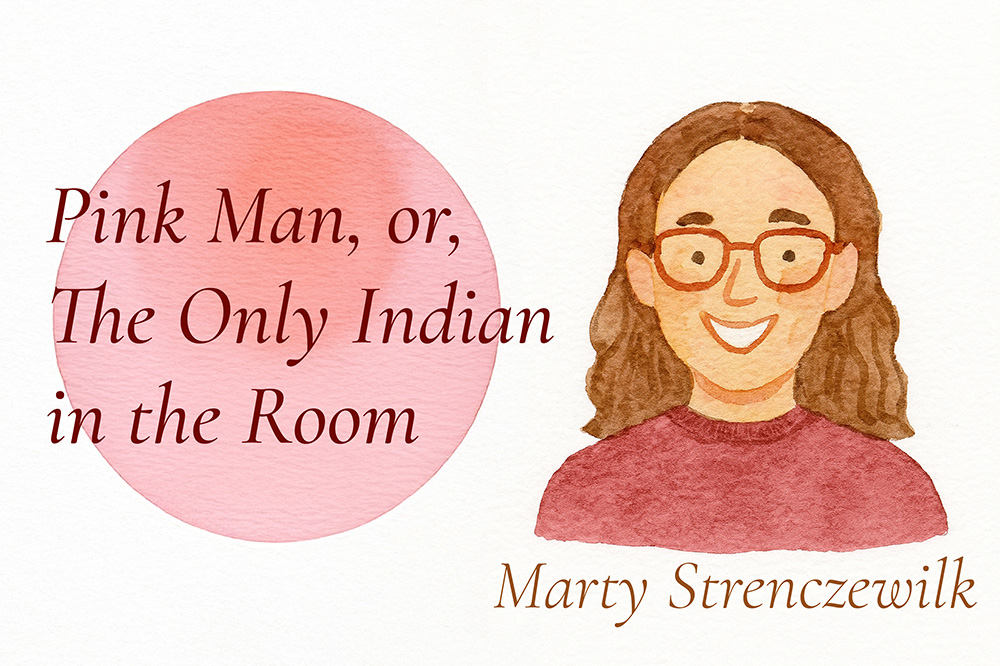 藝@書
藝@書粉色的認同
在美國這個種族多樣的國度中,身分政治一直都是劇作家亟欲探索的主題。近年來,除了非裔劇作家之外,也有愈來愈多原住民劇作家以種族的角度切入書寫劇本,奧吉布瓦族(Ojibwe)劇作家馬蒂・史特倫茲威爾克(Marty Strenczewilk)便是其中一例。他憑著《粉色的人或在場唯一的印第安人》(Pink Man, or, The Only Indian in the Room,以下簡稱《粉色的人》)從2023年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多元之聲劇本競賽(Diverse Voices Playwriting Initiative)脫穎而出。藉著這個類自傳、類單口的喜劇作品,觀眾走進他的內心世界,看見原住民這個身分所蘊含的美麗與哀愁。 「內化的種族歧視」 史特倫茲威爾克成長在白人小孩才有權利平安健康長大的時代。鎮上,兩名非裔與亞裔小孩因外表不同而被霸凌。他看著自己的白皮膚與褐頭髮而感到幸運至少他可以藏起自己的原住民血統,偽裝成白人,全身而退地度過大學以前的時間。 但,他憑著少數族群的身分拿到大學獎學金後,「可以偽裝」便成了問題。當他頂著白人臉孔走進滿是少數族群的新生教室,非裔、拉丁裔、印度裔的惡意齊發「白人又來偷我們的獎學金。」另一邊,即使其他原住民朋友第一次給了他歸屬感,但相比之下,他受過的苦難似乎太少,少到他不夠格自稱一位原住民。 日後,一次在診間,諮商師剖析道,他對自己有種「內化的種族歧視」。這句話劃破了幻象。他的童年幸運不是真的幸運,安然無事長大成人的代價,是對母系原住民血脈的糾結與不願理解。諮商師的無心之談,逼著他重新審視自己的出身,卻也燃起寫作的火種,焠煉出如今的《粉色的人》。 類自傳、類單口的喜劇作品 《粉色的人》以類自傳、類單口的體例寫成,角色有印第安人(Indian)、納納博佐(Nanabozho),以及穿梭在各場景間,時而評論、時而扮演的歌隊。 印第安人是劇作家在劇本中的化身,向觀眾說一則又一則個人史與家族史故事,但有趣的是,劇作家只給予角色「印第安人」之稱。沒有名字,是因印第安人/劇作家曾逃出命名儀式;用貶義詞則突顯了他們內
-
 戲劇 變形成人的代價
戲劇 變形成人的代價《羊之歌》 以寓言叩問人的盲目慾望
羊群中,一隻羊兩腳站了起來。與低頭吃草的同類相比,牠顯得更有定力與決心。畢竟,牠想從「牠」變成「他」。 牠有變形成人的慾望。 比利時柏格曼劇團(FC Bergman)的《羊之歌》(The Sheep Song)便在這般怪誕的設定中展開了。一隻羊踏上變成人的旅途,路上所見雖有人有獸、有男有女、有善有惡,但牠還是毅然走完整趟旅途,變成新造的人。 回顧西方文學史與戲劇史,羊的旅途一點都不新,但柏格曼劇團善於以經典挖掘靈感、發展作品,「不新」恰是他們的專長。《羊之歌》中,羊的所求就是文學中常見的「變形」。當牠走在《聖經》的意象上時,身後一幕幕掠過的場景,也如中世紀劇場的戲車。 旅程的開端:變形的慾望 《羊之歌》最初,羊就有變形成人的慾望,推著敘事前進的也是這股驅動力。 西方文學中早有「變形」的概念,《木偶奇遇記》就是一例。如《羊之歌》的羊得看透世事,皮諾丘也得越過重重試煉。兩名角色都得通過考驗,才會有超個人力量(如仙女或人類社會)認可成人的資格。但,兩者不同的是,皮諾丘變形成人不是出於己願,而是仙女給他的額外獎賞。最初,木偶不知道他有變真人的可能。 再探源一點,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是西方文學中更古老的例子。奧維德從希臘羅馬神話中採集與「變形」相關的篇章,編寫成詩,而他筆下角色變形的驅動力五花八門。少數如宙斯,追愛的慾望可轉為變形的驅動力,化作天鵝,但更多的是神祇等超自然力量操弄的結果。 《羊之歌》中的羊何來變形的慾望?或,人或獸為何想變成另一族類?英文中,慾望(desire)、想望(want)與匱乏(lack)是近義詞。變形的慾望,是我族匱乏漫延成的他者想望我不夠好,我多想變成他。但,羊在人身上看到什麼長處?柏格曼劇團只呈現了,當兩族的界線變得模糊,人與獸變得沒有太大區別。在貶己抬人上,人與羊似乎一樣不遑多讓。
-
 藝@書
藝@書打造一本屬於每個人的馬戲書
對於身在台灣的我們而言,第一次接觸「馬戲」的契機或許藏在電視機或遊樂園內,而我們對馬戲的記憶便停留在那些丟瓶子的雜耍者與跳火圈的獅子上。不過,這種單薄的想像很快就會被《火箭發射:24位當代馬戲大師的創作方程式》(後簡稱《火箭發射》)打破了。
-
戲劇 王嘉明vs.理查三世 Round 4!
聲響塗鴉 製造「真相」
王嘉明前幾次執導《理查三世》,「聲音」是他始終著迷的元素。在玩過「身聲分離」、現場樂隊與演員人聲撞擊之後,這回的《混音理查三世》,王嘉明說要讓聽覺元素有更多「街頭、塗鴉」的質地,不只讓多位演員以不同聲調扮演同一角色,還讓演員同時斜槓當樂手,毫不避諱地向觀眾展示這些角色與聲響被「製造」出來的過程,因為這些人造感、加工感,正是王嘉明研究《理查三世》的體會,也是他創作《混音理查三世》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