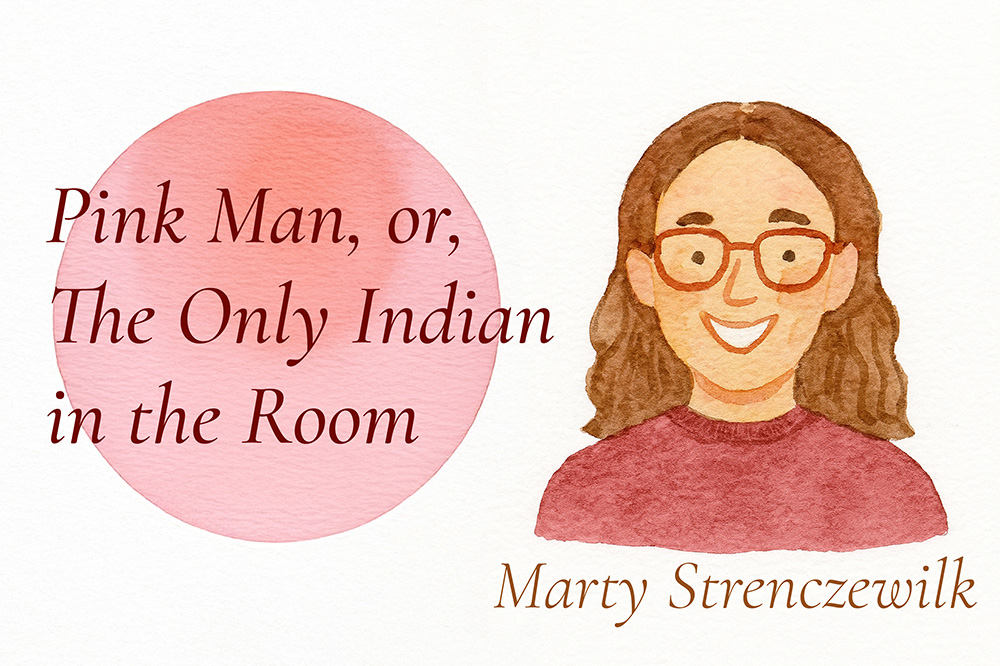在美國這個種族多樣的國度中,身分政治一直都是劇作家亟欲探索的主題。近年來,除了非裔劇作家之外,也有愈來愈多原住民劇作家以種族的角度切入書寫劇本,奧吉布瓦族(Ojibwe)劇作家馬蒂・史特倫茲威爾克(Marty Strenczewilk)便是其中一例。他憑著《粉色的人或在場唯一的印第安人》(Pink Man, or, The Only Indian in the Room,以下簡稱《粉色的人》)從2023年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多元之聲劇本競賽(Diverse Voices Playwriting Initiative)脫穎而出。藉著這個類自傳、類單口的喜劇作品,觀眾走進他的內心世界,看見原住民這個身分所蘊含的美麗與哀愁。
「內化的種族歧視」
史特倫茲威爾克成長在白人小孩才有權利平安健康長大的時代。鎮上,兩名非裔與亞裔小孩因外表不同而被霸凌。他看著自己的白皮膚與褐頭髮而感到幸運——至少他可以藏起自己的原住民血統,偽裝成白人,全身而退地度過大學以前的時間。
但,他憑著少數族群的身分拿到大學獎學金後,「可以偽裝」便成了問題。當他頂著白人臉孔走進滿是少數族群的新生教室,非裔、拉丁裔、印度裔的惡意齊發——「白人又來偷我們的獎學金。」另一邊,即使其他原住民朋友第一次給了他歸屬感,但相比之下,他受過的苦難似乎太少,少到他不夠格自稱一位原住民。
日後,一次在診間,諮商師剖析道,他對自己有種「內化的種族歧視」。這句話劃破了幻象。他的童年幸運不是真的幸運,安然無事長大成人的代價,是對母系原住民血脈的糾結與不願理解。諮商師的無心之談,逼著他重新審視自己的出身,卻也燃起寫作的火種,焠煉出如今的《粉色的人》。
類自傳、類單口的喜劇作品
《粉色的人》以類自傳、類單口的體例寫成,角色有印第安人(Indian)、納納博佐(Nanabozho),以及穿梭在各場景間,時而評論、時而扮演的歌隊。
印第安人是劇作家在劇本中的化身,向觀眾說一則又一則個人史與家族史故事,但有趣的是,劇作家只給予角色「印第安人」之稱。沒有名字,是因印第安人/劇作家曾逃出命名儀式;用貶義詞則突顯了他們內化的種族歧視。
納納博佐則是在奧吉布瓦族口述傳統中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角色。他可以是渡鴉、兔子、郊狼或人類;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可以是精神領袖也可以是搗蛋人物。如此無法定義,劇作家於是將納納博佐設定為咖啡廳老闆,在因緣際會下將印第安人從「白種人」、「紅種人」的僵化定義中解放出來,帶著他走上粉色的和解之路。
不是紅色也不是白色
劇本的時空設定在一個大雪的冬夜。星期五,咖啡廳的麥克風屬於有故事的人,但眼下沒有志願者,納納博佐便瞄準了印第安人。擋不住邀請,印第安人站到麥克風前,開始說他的故事。
童年時,印第安人的朋友發覺他的原住民身分後,往往以刻板質疑回應:為什麼他那麼白?為什麼他沒戴羽毛?為什麼他沒騎馬?這些排山倒海、未經修飾的訕笑都讓他厭惡自己的奧吉布瓦族血統,也排斥每年跟著母親回到保留地參加慶典。
他也記得以前坐在白祖父的大腿上看西部片,跟著約翰.韋恩(John Wayne)一起喊「殺死那些野蠻人」。與此同時,他的奧吉布瓦族祖母正在廚房裡為他們煮飯。多年以後,他才發現自己天真又無知。他裡外都太白了,白到甚至願意為電影裡那些開槍殺死族人的牛仔喝采,也不感到冒犯。
但,以原住民的身分進入大學後,印第安人認知到族裔也不是非白即紅那麼簡單,有時他像個冒牌者,有時他又是個原住民。但,更多時候,他卡在一個少數族群爭取少數資源的環境裡,而在「少數」的標籤下,一條食物鏈串起各個族群,所有互動都是爾虞我詐。此時,身分政治的複雜性再度加深了他的自我認同障礙。
看著印第安人說著這些無益於建構身分認同的故事,納納博佐決定點出問題的核心,挪移時空,帶著印第安人重返那個他決定斷根的場景。當年的命名儀式前一晚,印第安人把自己灌醉,覺得生為原住民簡直是場鬧劇。一氣之下,他放火燒了儀式的服飾、頭飾、樂器,並在憤怒與羞恥中離去。
但,既然有第二次機會,印第安人踏上自我和解的旅程。他不再避諱在社群媒體上公開身分,並發現網路上的同溫層比質疑者還多。同伴的力量也給了他勇氣,在納納博佐的引領下,他見到祖母、回到當年中斷的命名儀式,而就在奧吉布瓦族旅行之歌的陪襯下,他取回姓名、找回身分,完成建構自我認同。
交叉性引出跨文化共鳴
身分政治是相對沉重的劇本主題,劇作家能否以輕馭重便可見其功力。除了印第安人的複雜身分可以讓劇作家呈現相反觀點而不偏倚,納納博佐無疑是協助製造戲劇節奏的最大功臣。承襲自奧吉布瓦族的口述傳統,納納博佐有時加快故事,有時減緩節奏,是印第安人的導師兼反派,甚至可以靈活調度歌隊,讓場上隨時準備從多焦的大亂鬥變成個人的脫口秀。他的存在,再輔以咖啡廳開放麥克風(open mic)之夜的設定,便是《粉色的人》可以用喜劇寫身分政治的關鍵。
《粉色的人》的核心概念是「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每個人都擁有多重身分,而這些身分的交織會形塑獨特的生命經驗。當看似衝突的身分共存在同一個人身上時,往往會引發認同上的拉扯。比方說,印第安人的白人外表與原住民血統讓他經歷了強烈的自我認同拉扯。不過,這種經驗其實具有普世性。因此,雖然《粉色的人》是奧吉布瓦族的故事,但任何經驗過身分衝突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鳴。
在眾人仍為「藝術是否該為政治正確服務」而爭論不休時,史特倫茲威爾克就先以他的親身經歷反映了當代身分政治的複雜性。《粉色的人》中,印第安人的外表讓他能夠體會身為多數與少數各是何種感受,並在看似相反的兩種經驗中窺見同樣存在的偏見與歧視。而,或許處理複雜的方式就是承認複雜。承認後,印第安人才能從白或紅的選項中找到出路——他選擇打破單選的機制,粉色才是他的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