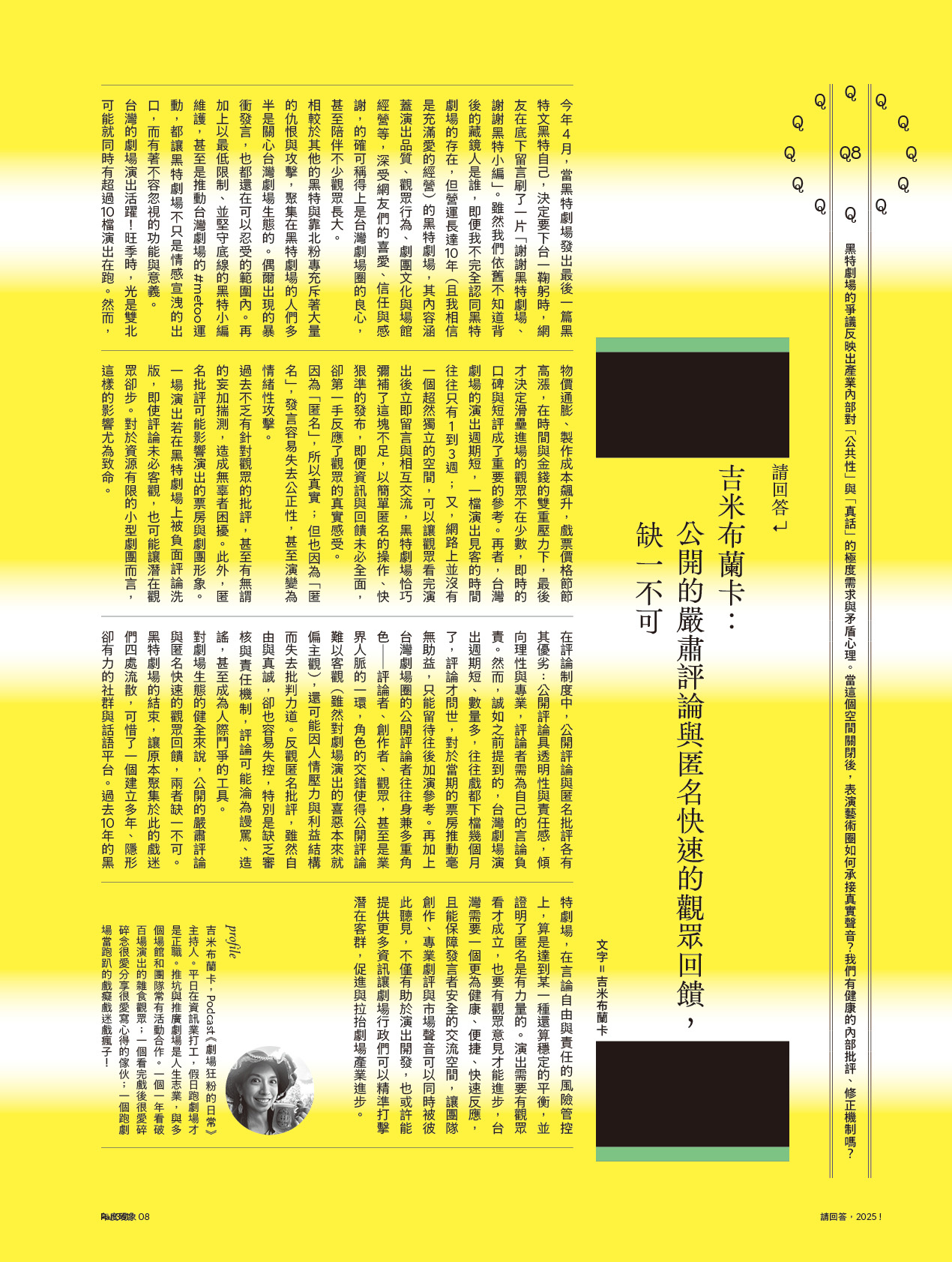陳思宏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無論如何,不要失去想像力」──陳思宏談《少年Pi的奇幻漂流》
讀到《少年Pi的奇幻漂流》裡的狐獴島段落時,作家陳思宏到圖書館借了一本動物圖鑑。 那是網路還不普及、台灣寵物店還未引進狐獴販售的2000年初,他從未見過狐獴這種動物。圖鑑上寫著:狐獴分布於南非地區,以草原為棲地,群居動物,性情溫和。回到小說,住滿狐獴、提供水源與食物的小島,湖水卻在夜晚變成酸液,蓮花裡藏有人類的牙齒,他才意識到,可愛的狐獴島,原來也是一座吃人之島。 多年來,這段情節一直留在陳思宏的閱讀記憶裡。某年他到日本奈良旅行,公園裡有野生鹿群散步、與人互動,他原想與鹿互動,鹿卻一口咬住他的屁股,他大叫,除了是痛,也是驚訝鹿並不如想像中溫和。「我被咬了一口才知道,鹿終究是動物,有野性存在,不像人類期待的那麼溫馴。就和狐獴島上的狐獴一樣。只是動物來到了人類的想像力裡,總是要很可愛,去除全部的野性,但為什麼動物一定要可愛,才能符合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想像?」 由加拿大作家揚.馬泰爾(Yann Martel)所寫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於2001年出版,講述16歲的印度少年皮辛.墨利多.帕帖爾(Piscine Molitor Patel),在與家人搭船前往加拿大的過程中發生船難,倖存的Pi意外與一隻孟加拉虎乘上同一艘救生艇,在海上共渡227天。作者透過一名印度少年的海上漂流,討論野性、信仰與真相,小說出版隔年獲得英國文壇最高榮譽「曼布克獎」,至今銷量超過1,400萬冊。隨後導演李安將小說翻拍為電影,全球票房超過6億美金,還獲得第85屆奧斯卡最佳導演、最佳攝影、最佳配樂和最加視覺效果等4項大獎。
-
 戲劇 從小說到劇場的《鬼地方》
戲劇 從小說到劇場的《鬼地方》結合民俗與當代馬戲 探問:永靖為什麼是一個鬼地方?
旅德台灣作家陳思宏寫了15萬字的小說講述永靖這個「鬼地方」,阮劇團則將陳思宏的15萬字原文解構再拼貼,在劇場舞台上用100分鐘來回答「永靖為什麼是鬼地方」這個命題,結合充滿地方色彩的當代馬戲和現場音樂,引領觀眾一起經歷這場跨越異鄉與原鄉、探詢身分認同的旅程,觀看角色如何揭示層層疊疊的家族記憶和歷史爭議。
-

從文學轉入劇場 阮劇團《鬼地方》乘著「噪音風暴」盤踞台北
在文壇掀起一陣旋風的陳思宏得獎小說《鬼地方》,由阮劇團改編為舞台劇,將於7月18日至8月24日首度登陸台北PLAYground空總劇場。本劇於2024年在彰化藝術節演出,深獲作家陳思宏讚許,更獲得2024 Taiwan Design BEST 100年度概念展演活動,成為阮劇團「2025噪音風暴」系列展演的重要亮點之一,融合文學、馬戲與當代表演語彙,帶領觀眾深入一座充滿靈異傳聞與壓抑鄉愁的台灣小鎮,重探家族、土地與身分的幽微邊界。
-
 特別企畫 Feature 劇場工作者蔡柏璋的「讀」書術
特別企畫 Feature 劇場工作者蔡柏璋的「讀」書術在有聲書的聲音表演裡遇見每個人的獨特
幾年前有機會接觸到有聲書《鬼地方》(小說作者陳思宏)的錄製,自此開啟我對聲音演繹的另一種想像。原以為讀有聲書跟劇場裡「讀劇」沒什麼兩樣,應該不是件太難的差事,殊不知整個錄製過程算是折騰(磨練)了許久。最主要的幾個原因在於: 聲音錄製的媒介與聽眾之間的關係 舞台劇的聲音訓練過程中,常被老師們提醒:不要因為過於仰賴麥克風,就沒有了投射,如果聲音本身是虛的,喇叭再怎麼擴大聽起來還是弱的。當時並沒有特別意識到,麥克風是雙面刃,它會放大優點,同時也會放大缺點。而且每支麥克風呈現出來的音色,以及與聲音演員之間的化學作用都是不同的。因此,朗讀者如何建立與麥克風之間的關係,會是有聲書聲音表演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麥克風能夠放大你聲音裡面許多細緻的表現,即使只是輕輕的氣音,或者是呼吸聲,在只有聽覺的前提之下,都會有頗強烈的指涉性及戲劇效果。另一方面,麥克風也逼迫你去調整原本習慣的投射方式。簡單來說,如果用平常在舞台上習慣的投射方式錄製有聲書,結果可能會慘不忍睹,因為聽眾與聲音之間的關係,往往是極為親密的(尤其很多人都是帶著耳機聽),好似有人在你的耳朵旁說話一般。如何在這樣「親密的範圍」內,用適當的聲量,依舊呈現不同力道的起承轉合,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在舞台上我們常說,演員內心糾結到無以復加,如果觀眾沒有感覺,這個表演就是沒有效果。在沒有視覺的輔助前提下,我們更要把聲音本身視為一個身體的行動、一個舞蹈的流動。我自己戲稱有聲書必須要建立一種「聽感」,雖說這個聽感的審美和標準因人而異,諸多眉角仍仰賴表演者重新去思考和定義;舉凡有些破音字到底該念「正確」的,還是念大家習慣聽的(念ㄞˊ症還是ㄧㄢˊ症呢?),也是我們常常陷入糾結的地方。 聲音掌控度的高度要求 錄製《鬼地方》的過程中,我最常被錄音師提醒的一件事就是「口水音」。這種聲音往往是表演者自身多年累積的舊習慣,也是我在錄製有聲書之前從未察覺到的。口水音在純然聽覺的環境下會被突顯出來,就像是一個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清脆響聲,雖說後製要修掉也不是不行,但出現太頻繁,還是會被要求避免。 其他例如送氣的爆破音及喉擦音(ㄆ、ㄊ、ㄎ、ㄏ)也是我的罩門之一。在舞台上,演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