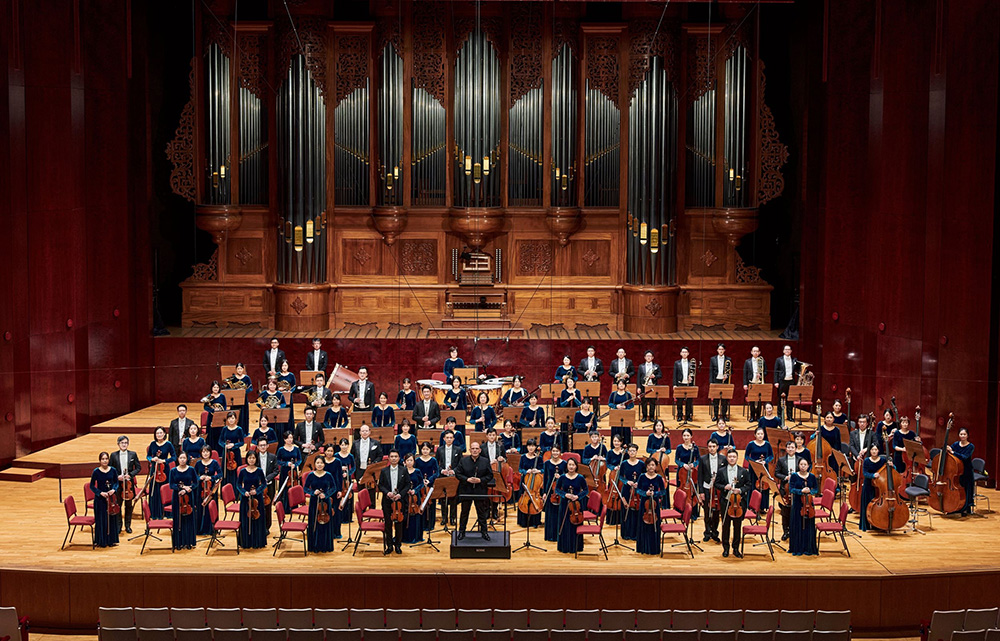台湾究竟有没有经典舞作?「经典」要以什么标准来检视?「优先」、「独占」与「影响层面」?或是较适合台湾独特环境的其他「条件」?
一九九三年十月,在日本冲绳南方的一个小岛上,一位中年妇人在年祭前的舞蹈排练时,指著其中的一段舞蹈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经典。舞蹈的内容是在描绘这个小岛的由来,与其历史、地理位置、人物事绩等等,简而言之,这支舞是小岛的代表作,很淸楚地透露她和别人不同之处。人类学家透纳(Vic-toy Turner)曾经提出一个概念「集体自传」(collective autobiography),可用来看待这样的舞蹈:一群人借由讲述自身的故事,创造其认同,并且在将现今所遭遇的问题与过去的伦理结合之过程中,新的意义于是产生(注1)。因此年年反复的舞蹈,非但强化了自身代表性的地位,并且因参与及表演者的更新,而产生新的意义诠释。
台湾有没有经典?
现在把焦点对准台湾,假使提出同样的问题──台湾有否经典舞作?经典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并不容易。在一个历史观曾经刻意被模糊、意识型态的差异被膨胀、文化歧异性较大的社会之中,由谁来定义经典首先就是一个关键问题(注2)。而从发展的角度而言,充分移植自外来文化的舞蹈,在经过吸收与转化后,台湾的剧场舞蹈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淸晰自我定位也有待考量。
即使如此,某些标准仍适用于检视经典,「优先」与「独占」便是常见的经典性格。比方说,当有人提及《吉赛儿》或是《牧神的午后》,其作品所具备的风格开创地位随即显现,尤其当被放置在历史辩证关系上,它的不可替换性便愈加鲜明,至少对一个想要教导学生了解浪漫时期芭蕾的舞蹈史教师,或是一名硏究尼金斯基者而言。
另一个检视的准则或许可称之为「影响层面」。脍炙人口的《天鹅湖》和令人深思的《春之祭》,不仅以其舞蹈表现著称,其音乐成就亦不容忽视。而其影响力,乃随作品的重复上演及广为流传而累积,甚至透过不同的诠释或版本衍生,不断地进行「再创造」。
云门代表作的地位
引用上述的各项准则来检视台湾是否存在经典作品,虽然无法有立即的答案,但是或许可以解释若干作品之所以历久不衰的原因。台湾第一大团「云门舞集」此刻正全省巡演中,主题就是经典舞作。舞团自己定义为经典者包括《薪传》中的〈渡海〉与《白蛇传》等等。其中关于《白蛇传》有下列说明:
“舞蹈语言融合了国剧动作与葛兰姆技巧,结构却源于传统剧场……家喩户晓的民间故事,充满新意,紧凑精采的编作,《白蛇传》立刻受到社会的欢迎……成为早年云门的重要招牌舞码……二十年间演出三百八十场……一九七九年,云门首度赴美巡演,《纽约时报》首席舞评家安娜.吉辛珂芙赞誉:『林怀民辉煌成功地融合东西方舞蹈语言与剧场观念。』《白蛇传》正是这类融合东西的典型代表作……”(注3)
上述段落中,「优先」「独占」及「影响层面」的元素十分明显。然而,严格地来说,《白蛇传》的经典意义,在文化史的关键角色甚于其风格或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对于自日本统治时期起便接受来自西方的强势影响,台湾的主流舞蹈发展可说是一面倒──倒向西方,无论是芭蕾或是现代,在技巧上的承袭十分澈底,而传统中国舞蹈艺术的不彰和早期本土民俗的受抑,更是加深了所谓东西方在发展上的差距,因此《白蛇传》甚至「云门」的产生,基于中国至上的出发点,稍稍在形式上平衡了这种差距,而成为「中华民国二十年来最重要的文化输出」(注4)。
另一个历史经典的例子,亦出自「云门」,那就是《薪传》。《薪传》的主题原已十分民族取向,而其一九七八年首演日的巧合更是强化了它历史上不可替换的性格。中美断交事件被认为是促使台湾人民摆脱被殖民心态的重要指标,而《薪传》的演出则在主动追求认同的目的上予以强力附会。透过一个淸楚的文化性动机,和近二十年来遍及全省的演出,《薪传》的经典地位因此奠定,但是主要是在一个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非纯从艺术面来考量。
无论是《白蛇传》或是《薪传》,其重要性不仅在影响地位的确立,而是透过后继舞者不断重演或是其他艺术家重新诠释的过程,更新了舞作的内涵而历久不衰。根据统计,曾经演出白蛇一角的云门舞者有十四人,她们陆续构筑了以白蛇为基础的经验传承,同时展现个人创造。不可否认,许多经典舞作都具有这样的吸引力与空间,一方面形成知识或技巧的训练体系,一方面又成为挑战或验证能力的关卡,然而这样的包容力非仅限于特定团体。
其他团体的代表作?
「云门」之外,不乏有其他强调东西融合或是民族取向的作品,但影响层面难以超越前者,原因无他:已经失去优先与独占性格。然而有些团体,其定位淸晰的作品一再上演的事实,则说明了社会对某些含强烈认同意味之舞作需求的情形。由蔡丽华所编「台北民族舞团」的代表作《庆神醮》,在一九八八年以后的频繁演出即为一例。虽然以民族系统的技巧取代国际性的现代技巧系统,在体质上本应将其限定为地方性的团体,但是呼应了一九八八年初政治上的解严,及随之而来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则适度地扶持了以民俗为素材的舞作。《庆神醮》在许多含高度文化宣示意味的场合受到重视即为此理。
因此对比于西方舞蹈生态,台湾本地作品有著十分不同的本质。首先,在这些代表舞作中,舞以载道的意味十分浓厚。以「云门」的例子而言,即使不谈民族文化,也免不了抒发「对社会脉动的关心」(注5)。不循此道,而重结构或创意的思考模式,虽然逐渐有发展的空间,却往往只能获得鉴赏者而非普罗大众的靑睐。其次,对彼此区隔得十分淸楚的各个团体而言,除了少数的例子之外,跨越界限师法他人之作,无论对象为何,几乎是不可能之事。因此「云门」总是演出自家经典:而若干优秀的作品,如刘凤学所编「新古典舞团」的《布兰诗歌》,虽获行家好评,却无法在更广层面发挥经典般的影响力。
行文至此,台湾究竟有没有经典舞作?如果从这个地区独特的文化背景及历史经验来看,笔者认为类似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集体自传」──亦即以一种特定形式传递并更新集体经验的作品的确存在。然而要成为足以影响后世,并具有艺术的开创性与再造性之经典,或许我们仍有许多値得努力之处。
附注:
1.参考Vitor Turner所著之'Are there univer-sals of performance in myth, ritual and drama?',收于由Richard Schechner及Willa Appel所编之By Means of Perfor-mance: Intercultural Studies of Theatre and Ritual,1990年剑桥大学出版。
2.日前《台湾舞蹈杂志》曾就九〇年代的舞蹈风貌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以大专舞蹈科系学生及媒体艺文记者为主。调查结果显示,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及其他项目,两者的结果有显著差异。即便是各校学生也反映其思考上的差异。可以推断若是在观众的调查可行之情况下,答案恐将更形复杂。
3.采自「云门舞集」所发之演出新闻稿。
4.「云门舞集」于香港演出时所得之评语。采自「云门舞集」所发之演出新闻稿。
5.采自江世芳报导之〈云门后天起全省演出林怀民经典舞作〉,见《中国时报》八十五年四月廿三日。
文字|赵绮芳 台大人类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