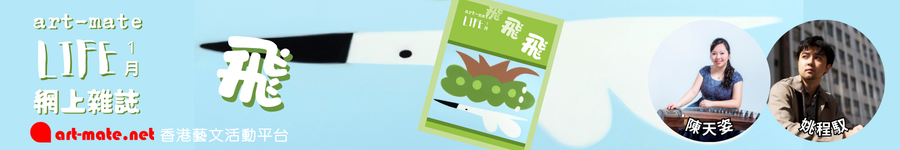唐纳伦(Declan Donnellan)在《演员与标靶》里开宗明义就说:「表演并非人类的『第二天性』,而是『第一天性』…是一种人类成长及生存的机制。」画下「我」这甲骨文的老祖宗很幽默,看透了以这表演的道具为「我」的核心图腾。
《PAR表演艺术》的编辑建议我写些文章时,刚好在带学生看甲骨文,自己当然不是专家,只是为了开心。当看著几千年前一颗颗中文字的模样时,仿佛看著一张张发黄斑驳的幼时照片,似乎有一个个蠢蠢欲动、呼之欲出的场景和故事。重点永远不在真实刺入脊椎缝隙般的定义,是在酒酣耳热,微醺恍惚,古今交媾间,体味残温仍不舍地黏在尚未铺整微潮的棉被皱褶里,那股字的骚味。这第一篇,当然要从「我」开始。因为是「我」写的,写给正在看这篇文章时的不同的「我」。
表演是人的「第一天性」
「我」,当初是一个有三根尖尖锯齿状的兵器,有另一解释是:这兵器看起来不好用,应该是用作惩戒的斧头或是展示用的礼器,像童话故事里国王都有的仪仗之类,所以那三根说不定是飘逸的羽毛,或是摇曳的旗穗。原来,我,只是一根表演「我」所用的道具:一根代表暴力的武器、宣示道德的刑具,或是张扬权力的仪仗。难怪,唐纳伦(注1)在《演员与标靶》(注2)里开宗明义就说:「表演并非人类的『第二天性』,而是『第一天性』…是一种人类成长及生存的机制。」画下「我」这甲骨文的老祖宗很幽默,看透了以这表演的道具为「我」的核心图腾,只是不知他将这字递给老大使用时,老大会不会说:「你是在开『我』玩笑吗?想尝尝『我』的厉害吗?来人啊!」或许这位发明「我」的人,最后就是被「我」砍下头来,嗯……颇有禅宗的意味。
其实要接受「表演」是「我」的第一天性这观点,很难,因为会让很多对话出问题,例如:「我很诚实!」或是「我是真的爱妳的!」这两句会变成只是「我」的台词,我不过演了出诚实的秀和我表演了一档真爱戏码,那么说这两句话的「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诚实」啊?我想,当事人应该会感觉愤怒进而强调:「我是真的很诚实啊!!」如此声嘶力竭的表演,反而成了最不诚实的姿态,成了政客的形象,这就是所谓戏剧的张力吧。
观众无所不在 表演无所不在
说也奇怪,到底是谁在我们脑中灌入厚厚的空固力(注3),让我们深深地觉得「我」体内有个东西=真,表演=假,所以,当我=表演,就会发生真=假的错乱状态,好像站在太虚幻境石牌坊前,望著「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对联。以此类推,当导演要求演员:「你的情绪要更真实一点」就有问题,剧场写实的基础也会有问题。而且,既然是表演,一定有观众,「我」就一定是关系、对话下的我,所以,「我」是演妈妈的儿子,老师的学生,老板的员工,上帝的信徒、情人的情人……「我」成了一个角色集合体,那何时没有观众?没有,观众一直在,即使一个人独处,「我」还是会跟「我」对话,我沉思我、我误会我、我喜欢我、我讨厌我、我和我辩论、我回忆我脑中的我,我爱上我心里的妳,不然,也不会有哈姆雷特的独白。
残酷的是,当我=角色时,「我完全融入角色」这许多演员汲汲营营追求的境界,根本就不成立!我们透过这台词去演自己要热血地好好表演,来否认自己本来就是在表演……嗯,「我」还真是场吊诡又复杂的表演。
注:
1. 英国重要当代剧场导演,1981年与友人Nick Ormerod共创「与你同行」(Cheek by Jowl)剧团。
2. 2001年以俄文撰写关于表演的专书,2010年中文版由陈大任、马汀尼翻译,声音空间出版。
3. 水泥的日文发音,成为台语用语之一,「阿塔马空固力」形容人痴呆,反应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