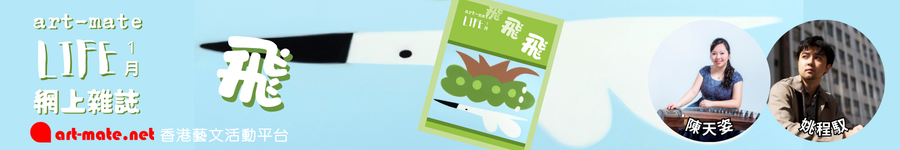国光演出时遇见以前教过的老学生,真是老学生,从清华中文系毕业30多年了,而她竟记得当年我曾带她们到台北的剧场看京剧!
这是作为老师最欣慰的一刻!
我应该是第一个在大学开「当代戏曲」课程的老师。提起戏曲,一般就只是关汉卿、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没人意识到还有「活著的人」在编戏曲。大学有「现代文学」课,包括小说、散文、诗,也有现代戏剧,但从没有现当代戏曲。我开这门课,当然不能只读文本,每次上课都抱著10几卷录影带当教材。其实它们是同一部戏,但因我并非全播,而是精挑片段,技术上就要先拷贝10来份,各自找出不同的起始点,上课时依序按编号播放讲解,所以这些戏我反复看过近百遍,烂熟烂熟,但「现场」仍是无可取代。1993年中国京剧院首次来台,名角大师云集,怎能不带学生亲临现场?那是没有高铁的时代,从新竹到台北是一段「旅程」,记得我好像还帮学生办了保险,戏码呢,当然精挑细选。
挑戏必须稳准狠,这是学生第一次进剧场,万一不喜欢就没第二次了。忍痛放弃《龙凤呈祥》、《群借华》、《凤还巢》、《霸王别姬》、《失空斩》,认准故事新鲜动人、表演可观的《春草闯堂》与《杨门女将》,事后证明我没选错,学生喜欢得不得了。
看完戏,我们持续讨论,学生都很兴奋,而我的情绪较复杂,我比年轻人多一层苍凉感慨。
《杨门女将》拍摄时演员都才20出头,看了近百遍的我,印在脑海中的是他们的青春容颜,而在台北剧场亲眼见到的穆桂英和佘老太君,都已超过60岁,看戏时情绪激荡,这40年辰光是谁偷走的?值得庆幸的是居然仍是原班人马,我一一在脑海中把他们的前后段人生相互比对,只是演到最后,采药老人出场,一看字幕,怎么不是毕英琦?录影带里的毕英琦呢?我焦急慌乱了多日,打听到结果,原来他30多岁就已病逝。得知的当下,我止不住爆哭,对方问:「妳认识他?」我怎会认识他?但他的采药老人陪伴我半生。
这层感慨,我没对年轻的学生说,而我没说的还有另一层,这么好看的戏竟都是在极端不自由、思想受箝制的时代编出来的。
我们都说政治不该干预创作,创作应享有全然的自由,我们说这是天理,但有天理吗?因此我特别尊敬在被监控的状态下端出好戏的创作者。本篇先从《杨门女将》说起。
《杨门女将》原本是扬州戏,范钧宏改编为京剧,杨家为远在边关的宗保庆寿,却传来宗保中埋伏身亡噩耗。一开场就大逆转大对比,寿堂变灵堂,接著寡妇出征,百岁老太君挂帅。后半到边关,扬州戏以战略武打为主,但随著得胜,逐渐失去了悲剧气氛。京剧却掌握宗保死亡的情绪主轴,随著马夫、白龙马相继出场,和宗保相关的人事物逐一浮现,到了采药老人引路寻到栈道冲到最高点,形成最后的大高潮。
但,首演时并没有采药老人。
我看到首演节目单,演员表并无此角,剧情简介是说「老马识途,发现宗保遗诗,寻到栈道」。
资料上说,首演结束,大家都很兴奋,等著领导上台握手奖励。没想到领导边握手边说:「应该走群众路线,才能打败敌人。」
我想,编剧范钧宏和整个剧组当晚一定彻夜未眠——群众路线?
我常想,如果换做我是编剧,当下会怎样?质疑?辩解?指责领导干预?
范钧宏当然不敢,恐怕连抱怨都不敢,连夜苦思,竟然想出采药老人。老人曾为宗保引路,可惜宗保遭暗算身亡,而今见到穆桂英,心情激动,颤颤巍巍再度引路,这才能直捣贼穴。但若只是剧本的修改还不是最精采,更高明的是导演指定言派老生毕英琦来演。言派唱腔拗折宛转,最适合衰弱老人,全剧一路激昂慷慨、悲壮豪迈,最后忽然出现幽峭之音,以柔弱之姿掉尾一振,藉反差形成最高潮,领导的政策要求,竟逼出了艺术新境界。这戏原本有两位老生,宋王是谭派,谭派原就适合王帽,机智善辩的寇准是马派,最后再来一个衰颓的言派,三老生三种个性,编导演抓紧京剧流派特质,文本结合表演,创出经典。现在的观众来看这戏,演到快终场前,莫不引颈期盼全剧「最后一位角儿」登场。台下观众鼓掌叫好甚至跟著哼唱时,这位领导早就被历史遗忘,没人感受被干预监控的阴影,没人想到「群众路线,人民的功劳」,这是艺术的成功。
刀架在脖颈上创作的年代,文艺界如同一片烈火灼伤的焦土,而杰出艺术家却能在焦土上栽种出鲜花,创作,令人敬畏。
但也未必每部创作都能在主题、剧本、表演之间得到完美平衡,下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