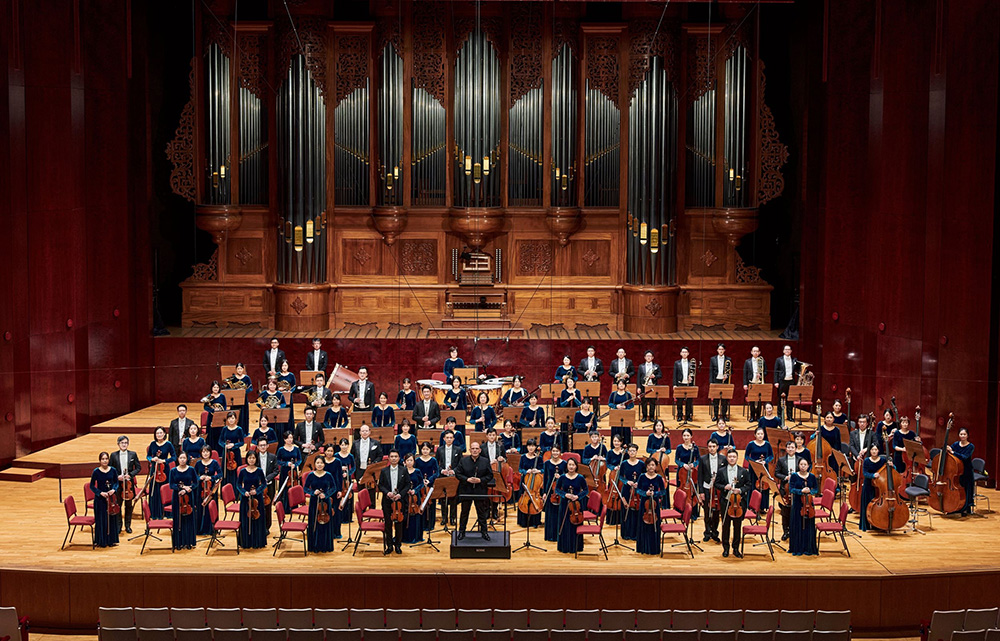我常常告诉学生,当我们在演出时,存在的「我」常常是两个或三个,有一位诗人曾说:
「我的呼吸、我的热情,在夜深、沈静的夜晚里都休息了,我独自在花园,我是花园的园
丁,也是那花园里的花。」
第一届美国范.克莱本钢琴大赛金牌奖得主费亚多,在美俄冷战时期,他的获奖在共产主义国家被视为他们在西方世界的胜利,讽刺的是,苏联政府却害怕他投奔到西方世界而扼杀他出国演出的机会,使他几乎在西方世界消音。苏联解体之后,他仍未被遗忘,受邀至美国演出,让他开始活跃于西方乐坛,现在更是北德大学的驻校艺术家。费亚多此次应NSO之邀来台,借此机会有幸访问这位延续俄国学派的传奇人物。
在您得到范.克莱本首奖之后,您被苏联政府禁止出境,当时您的心情如何?
在参加比赛之前,我已经有许多演出的机会,但是比赛之后才是我演出生涯的开始,如英国皇家爱乐的邀请及许多捧上门的合约;但是由于俄国政府对我的限制,因此无法出国,这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压力的解除,觉得轻松,因为演出需要更多的曲目,才能出国巡回,而那时我是非常懒惰的,但是我却没想到这个禁令会这么久,之后我也无法期待会有什么改变。这种情况让我感到气愤与不满,因为我不能呼吸新鲜、自由的空气,尤其是在音乐世界里面,我认为音乐家不应该学习四十套曲目,却在同样一个地点演出,应该是在四十个不同地点演出同样的曲目,而且有机会与不同的伙伴、不同的乐团合作,这些经验我在俄国已经拥有了,但对我而言这仍是不够的。
艺术与生活的结合
在您与诺莫夫学习的过程中,他影响您最深的是什么?
虽然诺莫夫是涅浩斯的学生,但诺莫夫仍是诺莫夫;而我,虽然是诺莫夫的学生,我仍是我,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质与风格。诺莫夫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在音乐的想像力方面,当我开始与他学习时,他发现我音乐的想像力,在心灵上有与他相同的触点,还有对建立个人风格的想法。在莫斯科音乐院里,所谓俄国学派还分几个派系,除了涅浩斯这个学派之外,我还接触了其他学派,我藉著阅读、听录音与音乐会,吸收其他学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有我自己学派的风格出现。
我现在除了从谱上读到情绪上的冲动、兴奋、喜悦之外,我还可以借由手上的技术来诠释与表现,我不仅可以对自己解释,也可以教导学生。所以从乐谱上所获得的情绪表现,并将情绪转达成手上所能够表现出的音乐,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所谓艺术上的结合。
在涅浩斯学派中最重视的是什么?
在涅浩斯学派上所存有的一个原则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它就是生活、人生,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时刻是无法被模仿的,关于这种艺术与生活的结合,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比方说,俄国戏剧大师史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 ),曾发生一个故事:在某一次排练时,有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必须骑著单车拿著花束从舞台上骑过,而他所饰演的角色是恋爱中的男孩,这时,大师不断地喊叫:「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是一位恋爱中的人。」从这里,即可反映出也许戏剧本身也有独特身体语言的表达。
音乐的联想
是不是俄国的戏剧与音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俄国,音乐与戏剧的确息息相关,但是戏剧与音乐就不一定了,因为音乐存在任何一种戏剧当中,但是戏剧就不一定总是要有音乐存在。关于音乐与戏剧的联想,就好比是我在演出时,必要时我就好像要按钮,让我自己照著谱上所写的、作曲家想要的音乐弹奏出来,当时的我与平常的我是不同的,而每一次在不同地方演出,有不同的听众、音乐厅及环境,任何都是不同的,而我必须要有演员的能力才能表达不同的音乐内容。
这样的联想也许有可能是出乎意料的,它有可能是存在於戏剧、文学、绘画、生活中的一个抽象概念,但这是必须的,因为艺术所需要的内容就是来自于此;这是同时存在的两种生活,一个是我们活著的真实世界,另一个是联想的世界。这就像我们用一只眼看东西,这东西不会是立体,没有容积,如果是用两只眼一起看,所见的范围都是立体的。在艺术上,所需要的这种容量、体积、规模,这也就是作曲家的乐谱,而当我们在读谱时,需要的就是这种想像力。
钢琴家在演出时他所扮演的戏剧角色是演员还是导演?
我常常告诉学生,当我们在演出时,存在的「我」常常是两个或三个,有一位诗人曾说:「我的呼吸、我的热情,在夜深、沈静的夜晚里都休息了,我独自在花园,我是花园的园丁,也是那花园里的花。」
心灵的力气
昨晚听了您的演出,您可以发出与乐团抗衡的音量,这是怎么办到的?
昨晚的演出我非常地不满意,也非常地生气,因为在音乐厅里,我听不到音乐厅的回响,指挥也不听我的演奏,我也听不到乐团独奏的段落;而我是一位演奏家,我是一位艺术家,所以我必须掩饰我的不满,事实上我是非常不满意,我也不认为我的音响效果有这么大。我可以说在音乐会上我演奏出的音量是因为我生气的缘故。此次来台,我非常地高兴,也在这里过得很愉快,我两位台湾学生安排的大师班与主办单位无微不至的招待,这一切都很美好,与乐团合作是唯一的缺憾,如果这个缺憾可以弥补,这将是一场不一样的音乐会。
关于体力与力气,演奏的力气是什么,这是相对的名词,当年李希特还在世时,每次到我家来,他总是一手高举我的狗,一手拿起哑铃,满脸通红,只为了表现他巨大的力气。他的去逝,因此令人感到意外,他带著他的太太到医院检查,回到家后,坐在扶椅上,说著他好累好累,就这样与世长辞。死后,医生解剖他的身体,大家都非常讶异,发现他的心脏非常地小,几乎都没有肌肉,而大家都对他生前频繁的演出与练琴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很难相信如此小的心脏可以应付如此繁重的工作,所以力气是生长在心灵里的力气。
上次俄国小提琴家皮凯森来台时提到音乐是他一生的信仰,它也是您的信仰吗?
音乐也算是一种信仰,但任何一种信仰都必须从仪式去寻找,但真正的信仰是超脱这些规范的,是在仪式或规范之上,是更广泛的定义。从俄文religion来说,re是再一次,ligion是创造万物、在宇宙之上、不可测力量的结合;所以对信仰的解释我可以接受阿拉、佛教、基督教等等任何宗教,因为我对信仰已超出仪式的界限。我必须强调音乐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有限制的事实主体,当我说我要清楚表达某件事时,这背后仍存在著我对此事某种程度的不知、不了解,而这在信仰里,也超乎仪式之外、在宇宙之上的这种感觉,这在艺术、音乐里,也存在著无法限制、没有范围、没有边际,无法去探索、摸索的。音乐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信仰,是没有仪式、教条的信仰,是一种崇高、在宇宙范围之内我所能感受到的这一种信仰。
音乐与商业的竞争
您为何会选择美国作为您教学与定居的所在地?
我是在美国比赛、获奖,也是第一位俄国音乐家因获奖资格而从白宫走进自由世界的音乐家,我待在俄国,经过共产主义十三年半的压制,我看见许多负面、不好的事情,当时我总是想离开俄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任何地方总比待在俄国好,后来我发现那是另外一种不好,我所谓的不好是因为太自由了。我在北德大学是「驻校艺术家」(Artist residence )的身分,我可以不受学校的约束,教学时间很自由,当初我会选择这个学校是因为它离范.克莱本(Van Cliburn )的办公室很近。我发现自由世界的学生对民主的认知是反向的,比方说巴赫不可能与乐团团员有同等的地位,而且很奇怪的是,艺术它并不懂民主这种东西。常有美国学生来上课时坐姿不雅、口嚼口香糖,我问他:「你的身体语言代表什么?」他回答我:「怎么样,巴赫以前是靠写音乐赚钱,我现在靠弹钢琴赚钱,这是同样的意义啊!」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要求学生从门的另一面将门关起来!我觉得这与家教及美国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我有两个美国学生和我习琴,当时他们才十二、三歳,有一次俄国朋友来找我,他们听了他们的演奏,他们都感到惊讶,因为在莫斯科音乐院很难找到这样的学生,他们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他们的弹奏技巧都已经成熟且具备专业的程度。从教学当中,我发现每个人都隐藏著某方面的才华与才能,老师的责任是将这些才华引爆出来,所以任何一种教育都是依赖教授个人,在世界各地都可以遇到各种才华的人,而这些有才华、有内涵的人往往都成为最受争议的一群,而我们对艺术的追求却已转变成利己主义,使得这群人成为各校派系的牺牲品,这种情况不只存在美国,在俄国也是如此。譬如海草,它并不需要特别的养分,大海自然给海草一个保护膜,老师的责任就像保护膜一样,他不需要亲自栽种它,海草有自生能力,可以继续发展与成长,有些时候我在音乐会上听到别人说:「他为何弹得不像CD里的呢?」所以社会舆论也是重要的一环,大家觉得只要是CD的音乐才是绝对的、正确的。我现在很少听到年轻演奏家是真正用自己的心灵、用自己的爱去表达自己的音乐,而是靠他外在的条件证明自己的能力或天分。
当年在莫斯科时,音乐家都是为音乐努力,所以有很高的成就,而现在许多音乐家纷纷到国外去,当然这个现象是世界性的,这就像是音乐与商业的战争,现在的音乐家只顾著赚钱,却忽略音乐的内涵与质量的问题;学音乐的人口增加,但是当中真的有多少人是有天分,是很难下定论的;过去在俄国,一方面是有很好的教育体制,另外当时的俄国人较有韧性、有柔软度,在心灵方面可以接受许多不同的事物,可以为理想奋斗。我的责任是只要能引发学生的潜能,我的人生就有意义,在艺术的路上,也可以扮演好老师的角色。
口译:古晓梅 莫斯科国立音乐院钢琴演奏博士
采访整理:赖惠娟 本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