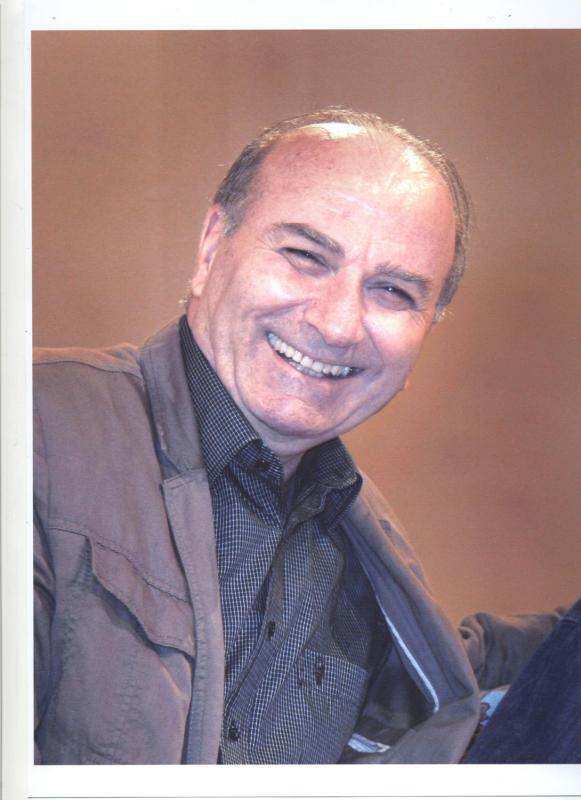希腊悲剧在形式与内容上,与写实剧场的观念格格不入,成为现代剧场在激发创造力上的最佳挑战。由于没有人真正看过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状况,透过剧本、场地与花瓶画像的想像重建,往往是瞎子摸象,却激发出现代剧场多元丰富的景观。
希腊悲剧充满对正义、真理、人性与城邦等重大议题的讨论,以至到今日,依旧是西方思想的灵感来源。当代美国女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在《善的脆弱性》一书中说:「悲剧向观众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积极地活在一个道德挣扎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美德有可能战胜各种反复无常的不道德力量,而且,即使不是这样,美德依然可以因其自身缘故而闪闪发亮。」
现代剧作家也很喜欢参考希腊悲剧,他们在其中发现可以与现代社会对话的基础。二次大战期间,沙特的第一出剧作《苍蝇》Les mouches(1943),是改编自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奥瑞斯提亚》,并加入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观念,突显他对参与抵抗运动的决心。另一位法国剧作家阿努伊(Jean Anouilh),于一九四四年重写了索福克理斯的《安蒂冈妮》,他添加士兵抽烟打牌等现代背景,在法国被占领期间,传达了个人对抗强权的讯息。更现代的德国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也改编与拼贴不少希腊悲剧,包括《暴君伊底帕斯》 Ödipus Tyrann(1966)、《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1968)与《米蒂亚素材》Medeamaterial(1982)等。
美国剧作家奥尼尔(Eugene O'Neill),则将《奥瑞斯提亚》写成是发生在十九世纪美国内战的家庭悲剧《哀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1931)。掀起英国新残酷剧场旋风的莎拉.肯恩(Sarah Kane),也曾以古罗马作家塞内加(Seneca)改编尤里皮底斯《希波里特斯》Hippolytus的剧本为蓝本,再改写成一篇现代药物暴力版的《菲拉德的爱》Phaedra’s Love(1996)。
以古剧喻今况 处处微言大义
其实,希腊悲剧的迷人之处,在于演出时与当年雅典的政治社会事件相呼应,用以古喻今的方式,唤起市民对当下环境的洞察。希腊悲剧常采用类似春秋笔法的写法,让古典学者与哲学家们,对研究这些作品感到乐此不疲。他们发现,悲剧的故事并不停留在表面,而是处处潜藏著微言大义。例如《奥瑞斯提亚》在西元前四五八年的演出与获奖,就与西元前四六二至四六一年,雅典实施民主制改革有关(这不是跟很多电影奖很像吗?评审们总偏好那些能与当下现实政治对话的剧本,不然《亚果出任务》怎会频频打败《少年Pi》呢?)。
前面提到阿努依的《安蒂冈妮》,当年在巴黎被占领的背景下,意外演出六百四十五场,主要也是德军将这出戏当作古代神话来看,没有意识到对法国人来说,安蒂冈妮正是反抗的象征(别忘了法国抵抗英雄的典范就是女性——圣女贞德)。
就演出来看,希腊悲剧对面具、歌队与音乐的结合使用,这种特殊形式,往往也是现代剧场试图突破写实主义框架时,经常拿来实验的对象。像执导《狮子王》闻名的美国女导演茱莉.泰摩(Julie Taymor),在一九九三年于日本斋藤纪念音乐节执导斯特拉温斯基的歌剧《伊底帕斯王》Odeipux Rex,就结合了偶戏与面具的创新元素。
美国导演兼学者谢喜纳(Richard Schechner),于一九六九年推出的《酒神69》Dionysus in 69,以集体裸体与互动即兴的诠释手法,为美国实验剧场打开了一道新大门。另外,二○○六年在台北艺术节演出的《酒神》,由美国实验剧场老将辣妈妈实验剧团(La Mama Experimental Theatre Club)制作,运用了类似舞蹈音乐剧场的方式呈现。至于更当代的后戏剧剧场风格,国人有机会看过的,是二○一年华沙新剧团在国家剧院演出的《阿波隆尼亚》(A)POLLONIA,欧洲当红的波兰导演瓦里科夫斯基(Krzysztof Warlikowski)以片段撷取的技巧,将《奥瑞斯提亚》、尤里比底斯的《阿尔克提斯》与纳粹大屠杀的议题并置。
仪式性演出 与其他文化传统剧场接轨
回到历史来看,希腊悲剧早已担负著激发新剧种的角色。例如文艺复兴初期,佛罗伦斯的梅迪奇家族,为了鼓励复兴希腊悲剧,号召艺术家透过史料的想像重建,创造出结合戏剧与音乐的表演,成了西方歌剧的始祖。
希腊悲剧所具备的仪式性,让它很容易与世界上其他传统剧场衔接,因为这些剧场在身体、音乐、舞蹈与面具等元素上使用上,都有类似的共通性。日本的铃木忠志是最好的例子,他曾在国家剧院演出的《酒神》(2007),透过源自能剧的身体训练,加上传统音乐与服装,充分诠释了希腊悲剧应有的肃穆感。这种希腊悲剧成为跨文化剧场桥梁的范例,还有当代传奇剧团的《楼兰女》(1993),这出改编《米蒂亚》的传统戏曲,以京戏的身段唱腔,激发了希腊悲剧应有节奏韵律;一九九五年,谢喜纳还与当代传奇剧团合作,在大安森林公园执导京戏加环境剧场的《奥瑞斯提亚》改编版。
至于歌队的使用,除了形式上有别于写实主义,背后的政治意涵往往也成为导演策略之一。○八年以色列哈比马国家剧院在国家剧院演出的《安蒂冈妮》,歌队就用了三位二战退伍老兵的角色,很难不让观众联想到以巴冲突的暗喻。
希腊悲剧在形式与内容上,与写实剧场的观念格格不入,成为现代剧场在激发创造力上的最佳挑战。由于没有人真正看过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状况,透过剧本、场地与花瓶画像的想像重建,往往是瞎子摸象,却激发出现代剧场多元丰富的景观。以此次将在国家剧院推出《普罗米修斯》的希腊导演特尔左布勒斯为例,他在执导《波斯人》(1990)时,运用了古希腊的厚底靴,让这些挺身站立的王族角色一旦跌倒,便令现场观众惊心动魄,成了最震撼人心的表演诠释。
在地实践 此起彼落源源不断
不论如何,希腊悲剧在实验剧场与跨文化剧场上,的确有其特殊地位。且不论国外,看看我们自身的创作环境,小剧场教父王墨林,早在一九八六年即做过《Tsou.伊底帕斯》,让原住民文化与希腊悲剧相互激荡。近两三年来,台湾小剧场界也卷起一股不容忽视的希腊悲剧风,这包括二○一○年杨景翔改编《安蒂冈妮》的《底比斯人》,二○一一年黄丞渝在「新人新视野」系列呈现改编自《米蒂亚》的《小坏物》,还有去年同党剧团演出的《底比斯人》。
至于今年,我所知道在台北的小剧场悲剧演出,在五月有台北海鸥剧团《她杀了他的孩子》(改编自《米蒂亚》),九月是王墨林执导改编的《安蒂冈妮》,以及身体气象馆与法国秘密集社剧团 (La communaute inavouable)合作的《又一个,米蒂亚》Another Médée,十一月台北海鸥剧团还要演出《最后英雄——伊底帕斯》。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如果《孙子兵法》可以是哈佛商学院的必读教材,那么希腊悲剧应该也应该是我们去拥抱的创新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