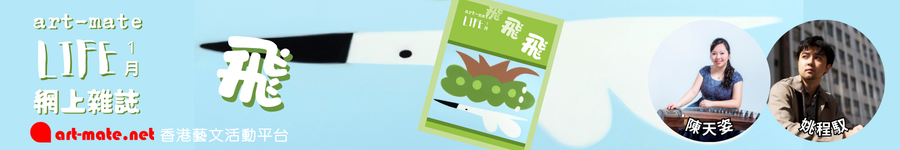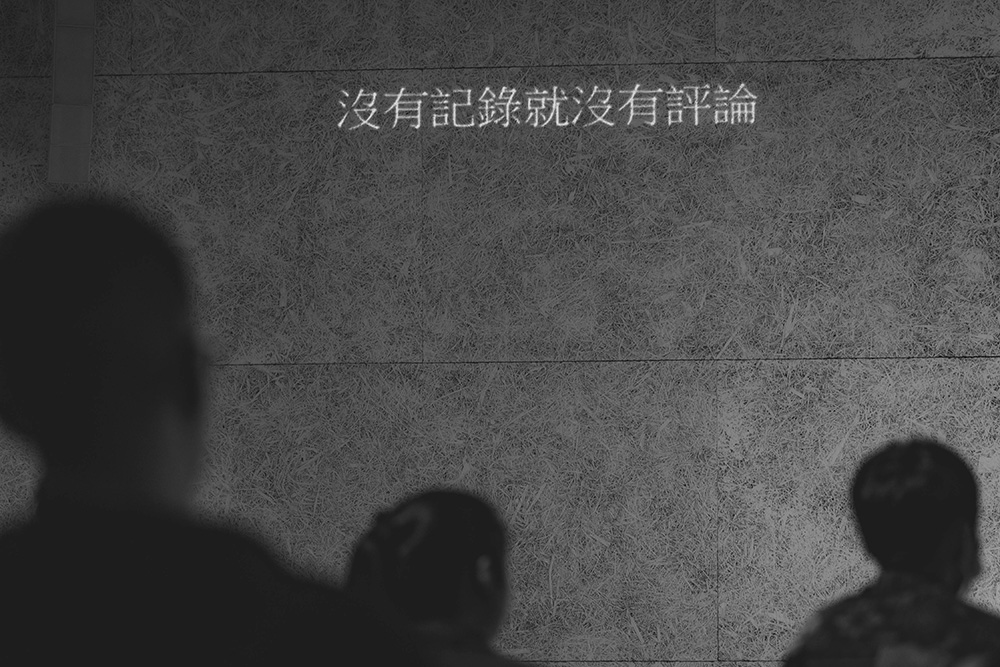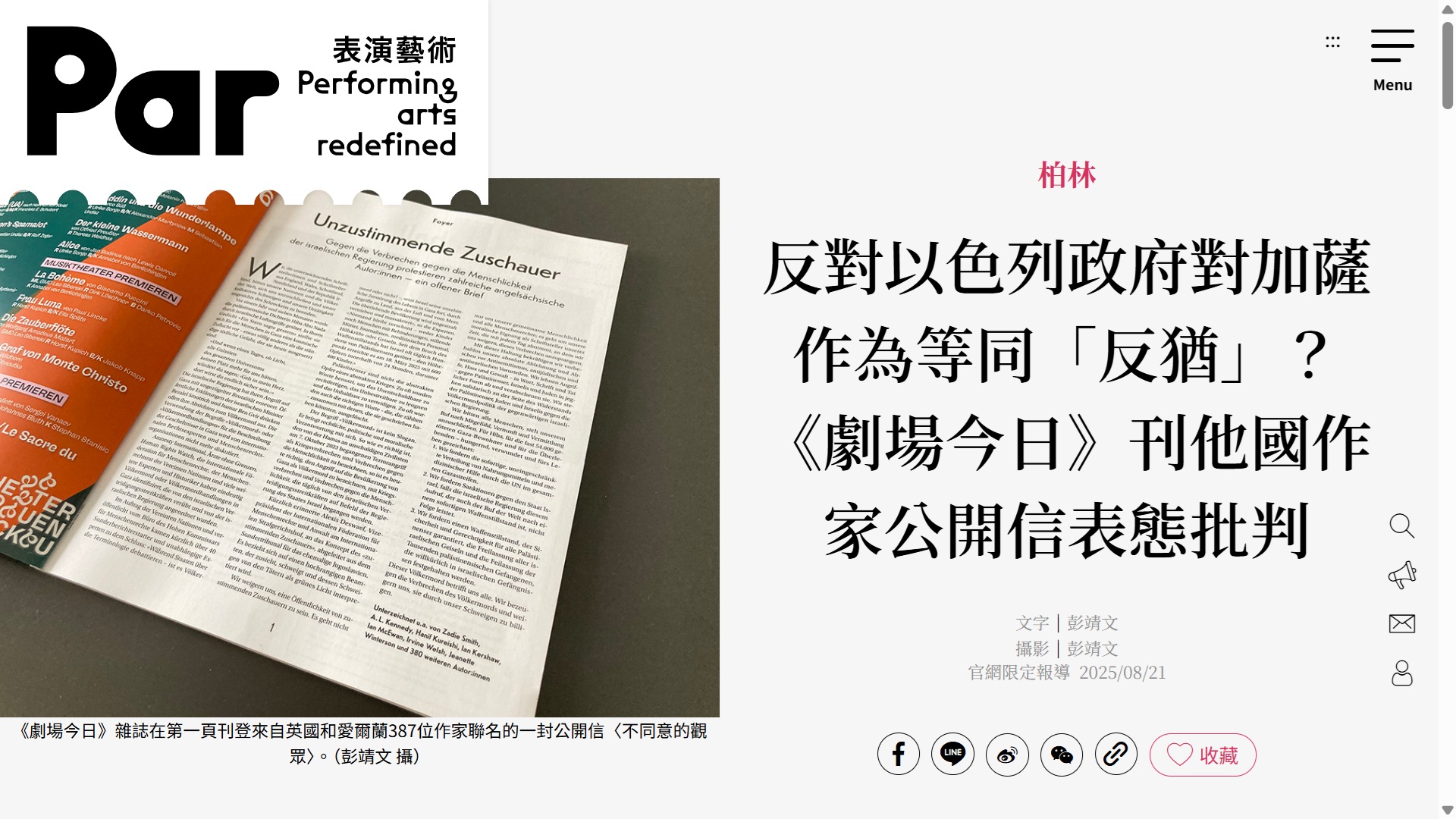超歌舞伎Powered by IOWN《今昔飨宴千本樱 万博版》
2025/5/25 台北 中华电信综合活动中心
2025年5月25日于中华电信综合活动中心上演的超歌舞伎 Powered by IOWN《今昔飨宴千本樱 万博版》,不仅是一场表演艺术的创新实验,更是一项融合传统与未来、跨文化与跨技术的多重尝试。
从沉浸式萤幕设计到AR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的参与,从九天民俗技艺团的实体加入,到NTT与中华电信合作的全光网路技术(IOWN),本演出不仅重新定义「现场演出」的条件,也为当代跨国剧场文化的未来打开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