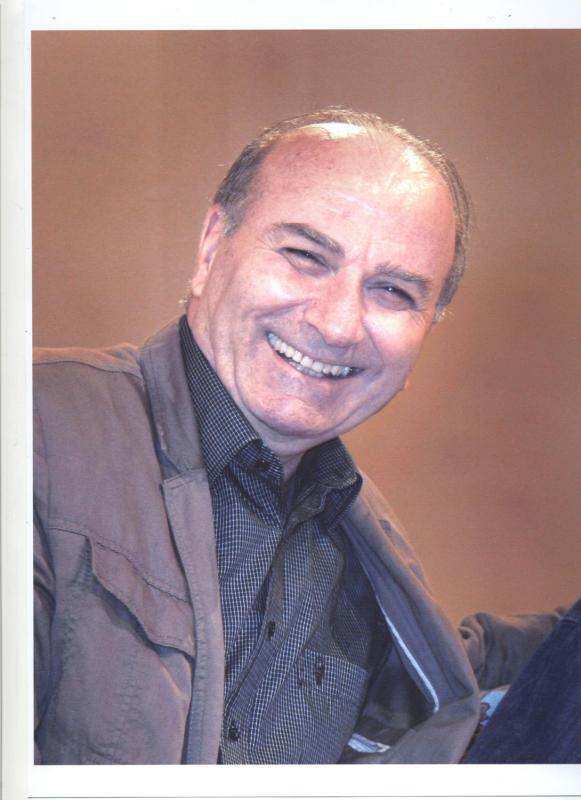即将随著作品《普罗米修斯》首度访台,希腊知名导演特尔左布勒斯也特别接受本刊的e-mail访问,一谈他的导演理念与剧场表演思考。他表示,在古希腊三位悲剧名家中,他「稍稍偏爱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剧作家)」,因为在埃氏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神、人与城邦之间的一体性」。他也透露,台北演出中他也会上台轧一角,演出歌队长,不但要说古希腊诗文,还要唱一首高加索的民谣。
人物小档案
- 生于希腊北部匹埃利亚省(Pieria)的马克里基亚罗斯村(Makrygialos),1965至67年就读雅典K. Michailidis戏剧学校。1972至76年于柏林剧团学习。
- 1981至83年任国立北希腊剧院戏剧学校(the State Theatre of Northern Greece Drama School)校长,1995至89年任国际古代戏剧大会(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Ancient Drama)艺术总监,1990年成为由22个地中海国家组成的国际地中海剧场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Mediterranean Theatre )的协同创始人之一,1993年起担任戏剧奥林匹克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Theatre Olympics)主席至今。
- 1985年创立阿提斯剧院,重要执导作品:《酒神女信徒》(1986)、《波斯人》(1990)、《普罗米修斯》(1991)、《四重奏》(1993)、《安蒂冈妮》(1999)《愤怒的海力克斯》(1999)、《贝克特三联剧》(2003)、《伊底帕斯王》(2006)、《茱莉小姐》(2008)与《毛瑟枪》(2009)等。
- 全世界有30所以上的大学戏剧相关科系,教授特尔左布勒斯在阿提斯剧院发展的演出希腊悲剧的工作方法。
Q:请问您觉得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里斯(Sophocles)与尤里皮底斯(Euripides)这三位古希腊悲剧作家之间差异为何?您最偏爱那一位,为什么?
A:埃斯库罗斯最接近宗教的原型。他的悲剧被视为是原初悲剧,因为非常接近神话。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里,神圣的存在是压倒性的,他的悲剧有强的形上学与宗教意味。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里,我们感受到神、人与城邦之间的一体性。
在索福克里斯的剧本里,一样有神的存在,但占优势的是城邦。这个平衡开始被松动,因为人类试图摆脱诸神与城邦的束缚。换句话,我们可以说在索福克里斯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社会的悲剧,因为原型已没有像在埃斯库罗斯中如此有力。
至于尤里皮底斯,他的剧本中人类完全成为主导;人类在城邦与社会中地位提升变得很高,他们开始质疑诸神。尤里皮底斯是一个充满争议与冲突的诗人。我执导过埃斯库罗斯、索福克里斯与尤里皮底的悲剧作品,我觉得他们都很重要,我对这三位作家的作品都有兴趣。但如果要说,我可能稍稍偏爱埃斯库罗斯一点。
Q:那您是如何思考希腊悲剧与演员身体的关系?
A:一般来说,当代的身体,不只是在剧场,基于当代的生活状况,都倾向失去它的力量与能量。剧场演员的身体会失去它的能量,在于某些新的自然主义剧本当中,演员的身体只需要做、走、坐或喝饮料等动作。但在悲剧当中,演员必须完全展露他的身体。演员需要有很大的能量、耐力与强有有力的声音(不能用麦克风),这样才有办法表现悲剧的诗文,因为这些句子都有一定的重量,暗示了极高的意义。在悲剧中,剧场必须发展属于自己的表现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古典悲剧对演员训练是如此重要。
Q:在一九七二到七六年间,您待在布莱希特创立的柏林剧团,这段学习经验对您执导《普罗米修斯》一剧,有什么影响吗?
A:当我在柏林剧团时,我遇到海纳.穆勒,而他也成为我的导师。他对古希腊悲剧的观点,深深影响了我用希腊神话来理解悲剧的看法。也就是说,悲剧的古代神话的解放。换句话说,我总失在寻找隐藏在悲剧后面的深远意义,以及剧本本身所欲表达的普遍意义。
在柏林剧团,我学到布莱希特在简洁、几何与抽象上的技巧。我学到在舞台上的任何事物都应有其目标。不要为了造型而创造某个造型,我学到如何组织我的创作素材。透过布莱希特的工作模式,我理解到方法的重要性,而不是难以捉摸的情感。你知道,希腊人与大多数的地中海人一样,都太依赖情感。
Q:我记得包浩斯对您也有影响,不是吗?
A:我受到来自德国与俄国的构成主义的强烈影响,还有包浩斯剧场的史莱莫(Oskar Schlemmer)也对我意义重大。包浩斯美学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在于对抽象的偏爱,其简洁性,以及对空间的使用方式。
Q:我在网路上看了您在二○一○年在华沙多样剧团(TR Warszawa)带工作坊的记录片,我发现您很重视呼吸与节奏,能跟我们解释您对演员训练的看法吗?
A: 每次在演出前,我们都会花一个小时,进行我们在阿提斯剧院做的基本练习。所以演员通常会在演出前两或两个半小时就到剧院。这个练习完全是重视呼吸的过程:吸气,吐气。藉著更换不同姿势的呼吸,演员的身体开始放松,整天的焦虑也被解除。在吸气时中,气必须要沉到骨盆的位置,演员在此过程中,是不断在放松与集中间替换。呼吸创造出幸福与沉稳的感受,这对集中精神、耐力与控制力非常有帮助,但这只是阿提斯剧院工作体系的一小部分,其实整个练习有很多阶段。其中一个阶段,是对身体与声音的分解与组合练习。你在网路上看到的,其实只是演员的基本准备工作,还没有进入正式练习阶段。
Q:您执导的《普罗米修斯》在希腊埃莱夫希(Elefsina)的古代橄榄油磨坊遗址首演时,是一个户外演出,那么到台北的国家剧院时,您会做什么改变吗?
A:在我们演出《普罗米修斯》时,我与贫穷艺术运动(Arte Povera)创始人之一的雅尼斯.库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一同合作,我们在古磨坊的墙上,挂上一千块石头,而演员是在泥土上演出。
到了台北后,演出的基本概念是一样的,只有一点点改变。最重要的,是我会亲自披挂上阵,说著古希腊诗文,并唱一首高加索的民谣。高加索是普罗米修斯被缚的地方,而我的家族也是来自高加索。也就是说,我会诠释歌队长的角色。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我们会在一个圆圈中演出,这意指著古希腊剧场悲剧演出的半圆形合唱席,这个半圆形空间是由石头与泥土构成的。如此以来,虽然我们现场没有泥土与石头,但同时我们保留了相同的感觉。
Q:为什么您让男性演员来饰演海神女儿的歌队?为什么您不使用面具?
A:我想您应该知道,在古希腊剧场,女性的角色是由男演员来扮演的,女人当时根本被不允许演戏。大约卅年前,我在执导《酒神的女信徒》的时候,我找了一个女演员来饰演先知泰瑞西亚斯(Teiresias)的角色,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我在本剧中想表达的,不是失望,而是愤怒与控诉。这是我希望演员能传达出来的,不论是他们是男人、女人、小孩或老人。重点是带出我要的能量。而我认为,在这个演出中男性最能带出高峰的能量。我从不直接使用面具。透过我们在身体与语言的表现,脸部、眼睛、嘴巴等的表情都被强化了,我们呈现了一种以生理表现的古希腊面具。
Q:您怎么思考「普罗米修斯」这个角色,还有他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A:普罗米修斯是在诸神的冲突中被打败的,他本来是泰坦神族。但他被宙斯处罚,被绑在高加索的高山上。在那里,他吐露他的痛苦,他的悲伤,以及肯定自己站在与胜利者的对立面。普罗米修斯是个充满冲突又具创造力的角色,他是最早的一个,也是最惊人的一个例子。
普罗米修斯毫不妥协,他的坚持与警觉,对当代人来说是一则重要讯息,因为当代人早已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受害者,他们只是参加活动,却没有真正参与在其中。
Q: 您的《普罗米修斯》,让我联想到尼采对希腊悲剧的分析。您的执导方式,可说是将酒神戴奥尼索斯精神与日神阿波罗精神,完美结合在一起,因为这场演出结合了迷狂的身体与理性的几何图形。您是如何评价自己对希腊悲剧的执导?
A:没错,戴奥尼索斯的元素在演出中有非常强的表现,即使演员是静止不动时,也是如此。但是,戴奥尼索斯的元素是受到控制的,透过能量与结构之间的平衡,我们找到了酒神与日神之间的平衡。
Q:那请问您自己与希腊悲剧或酒神戴奥尼索斯之间的关系为何?
A:对我来说,悲剧是关于伟大状况与想法的剧场,这是一种探索永恒人性需求与疑惑的剧场,有著崇高动力的剧场。戴奥尼索斯是剧场之神,是当我们演出时所面对的神祇。悲剧演出是以行动探讨什么是诸神与背叛。我们会想要碰触悲剧这样伟大的议题,是为了想摆脱平凡与写实主义。而且,阿提斯(Attis)这个名字,是古代土耳其弗里吉语(Phrygian)中的戴奥尼索斯,是冬天的酒神。
Q:最后一个问题,当初您怎么会想要创办「戏剧奥林匹克」(Theatre Olympics)?二○一○年在首尔办完之后,接下来这一届会在哪里举办?
A:戏剧奥林匹克是一九九三年在希腊的德尔菲(Delphi)创立。第一届戏剧奥林匹克于一九九五年在德尔菲举办,标题是「跨越千禧年」。每一次,每一届戏剧奥林匹克,都有一个特殊的主题,这个主题会跟举办的城市还有时代相关。所以,接下来几届包括了:第二届戏剧奥林匹克于一九九九年在日本的静冈市举行,主题是「创造希望」;第三届是二○○一年在莫斯科举行,主题是「人民的剧场」;第四届是在伊斯坦堡举办,时间是○六年,主题是「跨越国界」;第五届是二○一○年在韩国首尔,主题是「爱与人性」。
戏剧奥林匹克是一个针对剧场与艺术的常态而开放的国际论坛,是艺术交换的空间。这个组织肯定传统质问与实验的价值,也致力推广剧场教育。
至于下一届戏剧奥林匹克,目前筹备工作才刚开始,我们会在近期公布更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