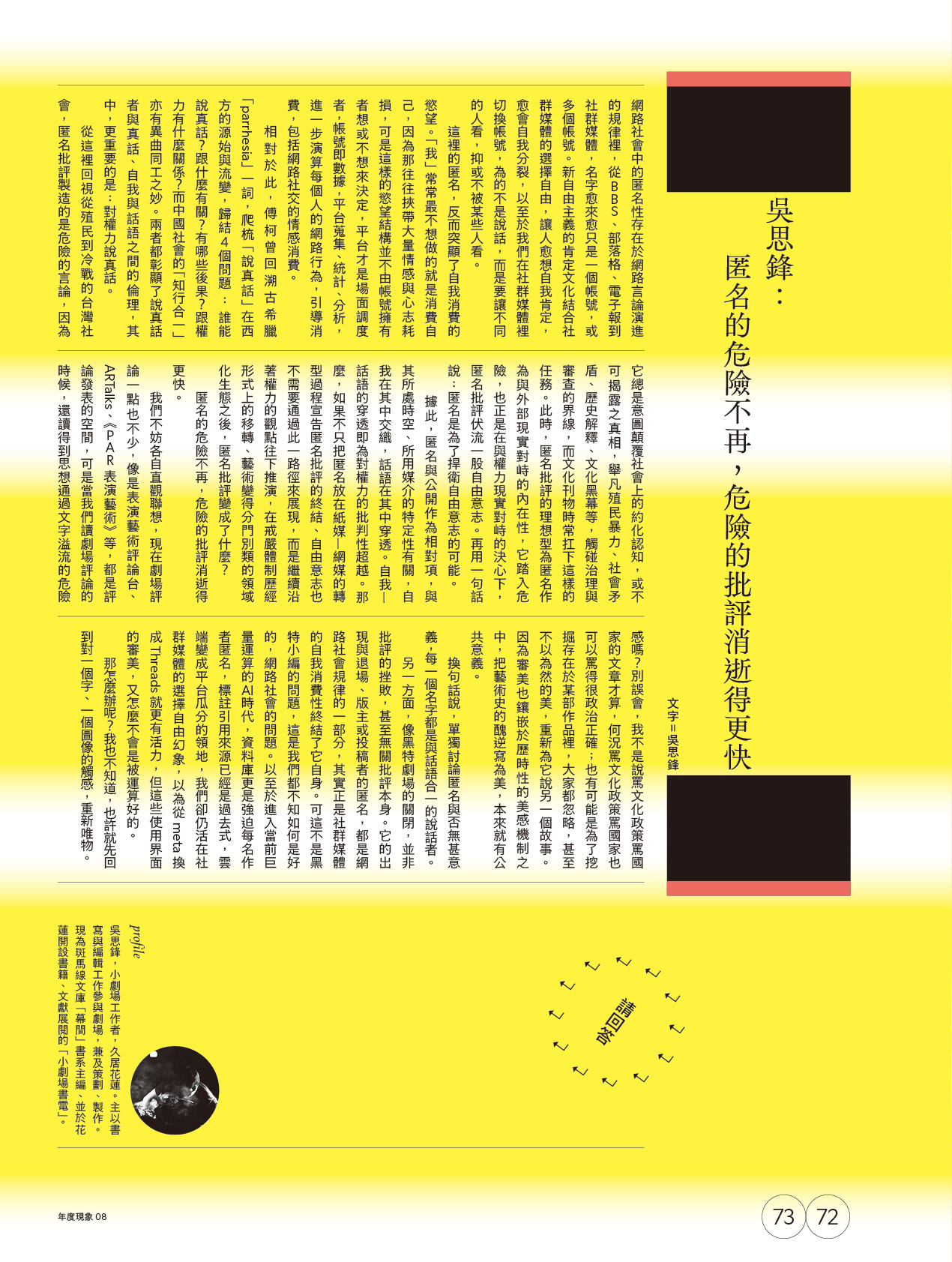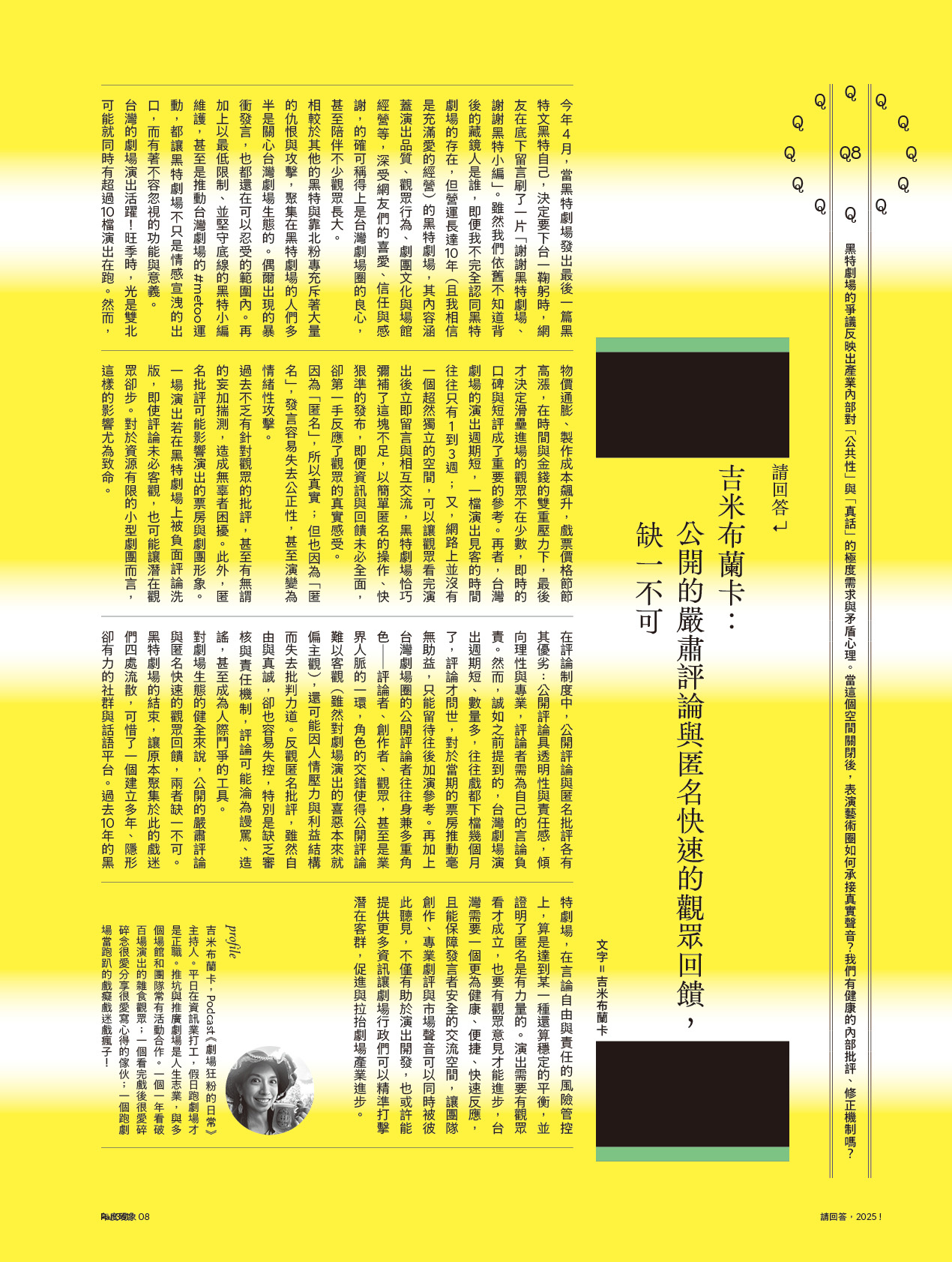裝置藝術
-
戲劇 改變理解的慣性,體驗裝置藝術的完成
《脫殼》 用龍蝦連結未知的感受與經驗
「《脫殼》可以讓你感受到⋯⋯」在導演陳煜典還在猶豫用詞的時候,裝置藝術家范承宗接著說:「會讓你脫殼。」這是《脫殼》兩位主創者描述這個作品能夠帶來的感受。 如此抽象。 抽象可能是作品最後的樣態,但也是起點。《脫殼》來自於陳煜典收到臺北藝術節的邀請,從「非人類中心」為討論起點,然後選擇「龍蝦」為主題,接著回應自己希望做沒有語言、也沒有明顯情節與角色的作品畢竟要用龍蝦寫一齣戲,或要某位演員演隻龍蝦,聽起來都很荒謬,而必須瞄準其他表達相對強烈的元素或方向切入。於是,這與常觀看劇場作品的范承宗曾於IG限時動態,希望能有劇場邀約,以及陳煜典翻閱到范承宗以海洋生物為主題的「龍宮」系列作品,既是巧合也是契合,促成合作不用語言的機緣,碰撞出不想使用語言的媒合,也是如此抽象。 這樣的合作契機,進一步造成兩種主體(劇場與裝置藝術)必須改變彼此的運作方式,更提供觀眾不同的觀看視角。
-
 焦點專題 Focus PQ舞台演出現場之一
焦點專題 Focus PQ舞台演出現場之一《龍捲風警示》 以物件召喚不可能的天氣
《龍捲風警示》(Tornado Watch)被選入今年PQ的舞台演出項目(PQ Studio Stage),為Katharina Joy Book和Eszter Koncz兩位藝術家共同創作的裝置藝術╱表演,關於模擬的天氣未來的、虛構的、不可能的天氣。 演出地點為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內的黑盒子劇場DISK。開演前,前台告知觀眾這是一個可以自由走動的裝置演出,也可席地而坐,請自由選擇。進入演出空間,黑色的地板上用藍色膠帶貼出線條,一圈一圈的不規則形狀,就像新聞上會看到的天氣預測圖。這層設計讓觀眾在一開始就走進一張氣象圖,成為天氣的一部分。空間中有從垂吊的麥克風、裝有水的密封袋、一個小冰箱、電風扇、鐵盤、放有日常物品的桌子等看似毫無關聯的物件。人群在這些物件中行走觀看,逐漸安頓。舞台的側門突然打開,兩個穿著紅衣黑褲的表演者走了進來,身體帶著輕快而專注的節奏,像是每天都在這裡工作。他們用角落桌上的水壺煮開熱水泡茶,水蒸氣在燈光下緩緩上升,一切很安靜。從此刻開始,表演者的一系列動作都帶有這種特殊的質感:帶有意圖的放置或移動物件,做一件看似簡單的事,卻若有似無地影射天氣現象。演出就由這些片段組成。
-
戲劇
身體、敘事與界線
對於「跨界」,往往著眼於「跨」這個動作;但,「跨界三部曲」得思考的反倒是「界線」的劃分,除涉及門類劃分,更核心的是自我定位的安置,而這似乎是「馬戲」在台灣有急於驗明正身的渴望。對我而言,「跨界三部曲」開發了馬戲的身體、啟動了馬戲的敘事;但,「物件劇場」、「裝置藝術」、「舞蹈」三者與「馬戲」的距離到底為何?我們是否像畫下一條虛設的界線,然後標榜「現在進行一個跨越的動作」?
-
名家訪談
浮世繪中任「憂」遊
在中學時夢想成爲建築師,但是當看過費里尼的電影《阿德瑪訶》後,電影導演便是他至今仍未完的夢。大學主修社會學,現在又是身兼劇場導演、敎師、藝術總監的小池博史,在他《春季》作品演出結束後離台前的早上, 談到他自己對創作、敎育的想法。
-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 Feature裝置的跨界表演
裝置藝術跨界表演領域,打破了表演藝術裡對舞台的慣性窠臼,增添了新的觀念與方法。相對地,劇場觀念進入了裝置思考時,也讓裝置藝術作品擁有了戲劇性的演出。不管是「舞台上的裝置藝術」抑或是「裝置的舞台藝術」都拓展了我們對美感經驗的新體會。
-
特別企畫 Feature
裝置藝術的形成
對新形式、新可能的追求,是推動裝置藝術產生的原動力。
-
特別企畫 Feature
自營商與服務業
在當代的表演藝術中,裝置藝術已逐漸延伸至舞台設計的範疇,可是從舞台設計者的角度來看,裝置藝術與舞台設計在本質上有許多的差異。兩者在創作的出發點和工作方式上,以及作品的目的與完整性上截然不同。
-
特別企畫 Feature
互蒙其利!?
裝置藝術家與表演藝術家的合作,對雙方來說大多都是互蒙其利的;但是其中的「合作對象是否契合」以及「工作方式與認知是否協調」,都是完成創作的重要關鍵。
-
特別企畫 Feature
揮灑新視界
對裝置藝術家而言,與新領域的跨界合作,並非只是裝置的形式或功能上的改變而已;更重要的是在觀念上不斷地辯證與翻新後,所累積帶來的新美感經驗。裝置藝術家談到他們在舞台上的合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