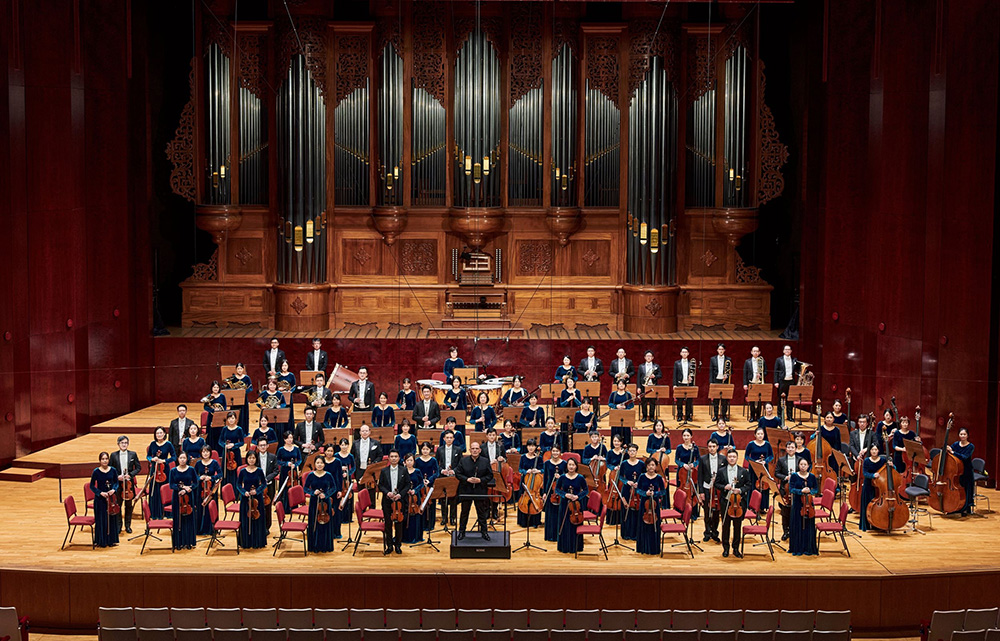无论是呼应社会一片本土化、寻求台湾主体性的声浪,或者是因应歌仔戏自一九八○年代以来逐步进入「文化场域」,经过一、二十年的酝酿与摸索,所产生的大量的创作企图及益发成熟的创作能力,以台湾这块土地的人事物作为歌仔戏新编剧目的创发,都可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现象。
新编历史歌仔戏《黄虎印》
6/12~14 19:30
6/15 14:30
台北国家戏剧院
INFO 02-33939888
河洛歌子戏《风起云涌郑成功》
6/21~22 14:30
6/21 19:30
台北市社教馆城市舞台
INFO 02-25813029
二○○○年以来,「演台湾事」成为歌仔戏创作的显著趋势之一。二○○○年两出本土创作出炉:陈美云歌剧团的《刺桐花开》、河洛歌子戏团的《台湾,我的母亲》相继于国家戏剧院上演,大获瞩目,成为歌仔戏在创作上追寻「在地原乡」的里程碑。无论是呼应社会一片本土化、寻求台湾主体性的声浪,或者是因应歌仔戏自一九八○年代以来逐步进入「文化场域」,经过一、二十年的酝酿与摸索,所产生的大量的创作企图及益发成熟的创作能力,以台湾这块土地的人事物作为歌仔戏新编剧目的创发,都可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现象。
开启历史诠释的另类可能
歌仔戏的传统剧目吸收中国地方戏曲或改编自章回演义,多以中国古代为背景,敷演中原各朝历史。胡撇仔戏虽然时空定位模糊跳跃,但也是一般意义下的「古代中原」为主。以台湾为背景的剧目相较之下可说九牛一毛,仅「郑成功」系列(依附于清朝的古册戏系列之下)、甘国宝过台湾、周成过台湾,及改编时事者如《林投姐》、《运河奇案》等新剧类。曾在田野访谈中问及此事,得知在古册戏连缀起来的「历史叙事」之下,歌仔戏前辈认为「台湾是无历史的」。则,「演台湾事」将台湾被湮灭、忽略的历史和人物搬上戏剧舞台,确实开启了对于历史诠释的「另一种可能性」,也开展了歌仔戏在剧目内容方面的新局面!相较于京剧或其他传统戏曲,歌仔戏在体质上与本土题材较为亲近,再辅以歌仔戏剧种的活泼特性、各个剧团在表演上的自成风格,舞台上对台湾这块土地与生活多采多姿的另类想像,终于填补了认知中仿佛无历史的空缺。
映照台湾当代关怀:族群、国家、后殖民
台湾独特的历史经验,以及当代台湾的关怀,使得本土题材的创作多涉及族群、国族、与被殖民经验的主题。在后殖民思潮的反思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正如二○○○年后「胡撇仔」的多元混杂被定位为反殖民的手段而获得美学上的肯认,本土题材搬上歌仔戏舞台,往往借由叙事、画面、以及对新文化元素的处理等等,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与多元混杂,而在舞台上呈现出一种Bhabha 所说的「杂种化」多元空间。这正是当代台湾对「台湾」的想像与再现。
二○○○年实力派的外台歌仔戏班「陈美云歌剧团」于国家戏剧院推出改编自老歌仔册《甘国宝过台湾》的《刺桐花开》。在新生代编剧杨杏枝的重新诠释下,对这个歌仔戏第一部汉原故事进行了颠覆,不采原本颇具汉人沙文主义的开台情节主干,而将平埔族群提升至戏剧主体的地位,借由汉族男性甘国宝与平埔女性伊娜「牵手」的浪漫爱情线,试图重现族群冲突与融合的现场,引领观众在一连串追寻「平埔妈」的历程中,展开及文化与族群的辩证。
明华园首部近代史取材的《鸭母王》(2002),虽然剧情多为杜撰,最突出的亦是运用明华园一向明快笑闹的节奏处理不同族群间的互动,呈现台湾社会多元族群的缩影。剧中虚构了三位代表台湾不同族群的女性:外省人台湾知府王珍之妹王绣楼,为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生,思想前卫穿著时髦,说话中、英夹杂,主动追求朱一贵;客家年轻寡妇李诗轩,温柔内敛,是朱一贵倾慕的对象;闽南传统女性朱玉妹,聪慧、善解人意,与台湾知府王珍有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剧中用朱一贵对这三位女子的情谊来暗示他对台湾的情感。
题材、主体与思想意识的转换,必然增加新的文化/表演元素进入的契机,也让歌仔戏得以对「表演」这回事进行玩耍。如《刺桐花开》将阿猴社的风俗及传统祭仪搬上舞台、在音乐编腔上除保留歌仔调之外,更吸收平埔族音乐,编创了「西拉雅打猎歌」、「平埔调」、「念农作物之歌」等新曲调,打造了一场成功的音乐实验。《鸭母王》亦配合不同的族群和语言,大唱客家歌谣、京腔流水、西洋音乐等。在表演的风格与肢体上,则介于古路戏与胡撇仔之间。
二○○五年专擅胡撇仔戏的春美歌剧团推出《青春美梦》,以日治时期的台湾与日本两地为时空背景,描述「台湾新剧第一人」张维贤的故事,更加玩弄了「表演」。用歌仔戏来演绎反对「旧剧」的新剧之父张维贤,《青春美梦》将新剧概念的排练、表演及技术过程以「戏中戏」之方式处理,充分展现了歌仔戏的「幽默」与兼容并蓄的长才,确实呼应了张维贤对台湾戏剧「革新破旧」、「求变」的精神。笔者以为歌仔戏「没有包袱」的年轻,实是一个可贵的特质,不同文化元素得以在舞台上并呈,无论在戏里、戏外,均勾划出一个属于台湾的混杂式集体认同。
河洛的台湾之路:建立一个以台湾为国格的历史叙事
河洛歌子戏团作为精致歌仔戏的龙首,在台湾国族意识的展现方面也迈著坚毅的步伐往前,至今已累积台湾四部曲:《台湾,我的母亲》(2000)是河洛创团以来最具台湾本土色彩与立场的代表作,改编自李乔的同名小说,描述清末民初彭阿强一家人来台开垦,为守护土地,与天灾搏斗、对抗交结清朝贪官的叶阿添,并与日军侵略等恶势力相抗争的故事;《彼岸花》(2001)则是以「漳泉械斗」为背景的台湾版罗密欧与茱丽叶;《东宁王国》(2004)描述郑成功之子郑经在台湾本土建立「东宁王国」的始末;《竹堑林占梅》(2005)则刻画清代台湾竹堑诗人林占梅的一生,并阐述清朝政府「以台制台」的手段,让台湾仕绅彼此敌对,以坐收渔翁之利。二○○八年六月并将于城市舞台上演最新的本土创作《风起云涌郑成功》。
河洛的本土创作系列,意图是十分明确与坚定的。与他团不同,河洛用「国家」的眼光看台湾,试图建立一个以台湾为国格的历史叙事,「压迫」与「觉醒」是其戏剧的主轴。透过台湾人意识的凝聚与觉醒、以及揭露、传播「曾经」出现在台湾的王国历史等等,河洛企图以「了解」来颠覆台湾作为「被统治者」的既定想像。了解史实,就会发现历史洪流中存在著许多的可能性与机会去选择不同的路径,现实可能只是「偶然」,而非「必然」。
河洛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情节铺陈中也随处可见「统」、「独」的影射,难免引来「意识形态过重」、「让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的质疑。但诚如《台湾,我的母亲》、《东宁王国》、《竹堑林占梅》的编剧陈永明所言,「意识形态是编剧人对故事的忠诚,如果编剧不忠诚于自己的题材,那就遑论感动观众了。」创作者必须对作品真诚,河洛的走向是目前主事者的选择,只是意识形态也有可能构成艺术上限制与危机,「教育性」是否是戏剧的终点?视野是否足够远大开创一番新局?相信热爱歌仔戏、热爱台湾的观众们,都期待著河洛的下一步。
舞台永远是比喻性的,歌仔戏本土题材的创作,不仅为歌仔戏的剧目与表演风格注入新元素,更反映了当代对「台湾」的想像与再现。透过戏剧「演台湾事」,台湾社会正进行著实然与应然的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