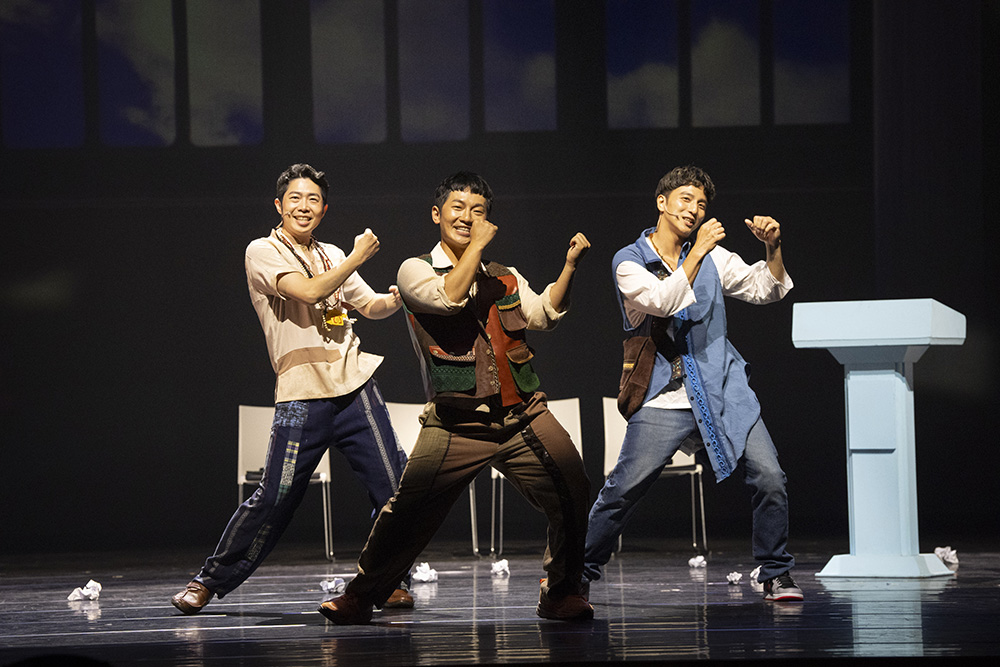至今,我仍然相信创作本身是为了回应那些只能透过创作来回应的「 」,创作者正因为无法用创作以外的方式表达而创作,并且在这之中不断找寻与他人或与自己对话的方式。
大学时期我是在一个没有艺术学院的学校里渡过的,除了一些美学相关的课程之外几乎是靠学生自主去接触以及筹办活动使「艺术」发生。这里的「艺术」对于现在的我会理解为一群对创作拥有各种憧憬、想像,但对自己没那么笃定的年轻创作者们所共同构筑出的临时庇护所——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彼此交流后创造出或许现在来看有那么点「粗糙」且真诚的作品。正因什么都在摸索、也不知道该去到哪,而慢慢捏出对于「艺术」的理解与认识。而那些不可被抹灭的痕迹,有时是期望自己能被看到,但有时出现那种连创作者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就这样做出来了作品,如野草从石缝钻出一般。
在艺术大学念研究所时我所理解到的「艺术」又是另一个面向:更集体、系统性的「艺术」、不同媒材所展开出的「生态系」以及所谓「艺术」与「艺术家」的生产过程。如果说大学时期像是海绵一样到处吸收,那研究所就像蒸馏槽,每次每次的蒸馏如同对自己不断的提问:在有限的时空、物质与精神下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做的?又有什么是只有自己能做的?就如同创作本身是为了回应那些只能透过创作来回应的「 」,或许这时的「 」也呼之欲出了。也是如此鼓励自己应该把握这样的状态与环境,与其他人一起玩、一起尝试各种可能性,也在种种机缘交会之下发展出《逆断口》这件作品。
萧育礼
1997年生,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新媒体艺术学系硕士班(原科技艺术研究所)。从小喜欢拆东西看他们是如何运作的,而开始学习他们的技术并练习维修。在大学进一步学习关于制造的知识后,不满足机械大多被使用在特定领域,于是开始寻找其他可能性。(偶尔也做一些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