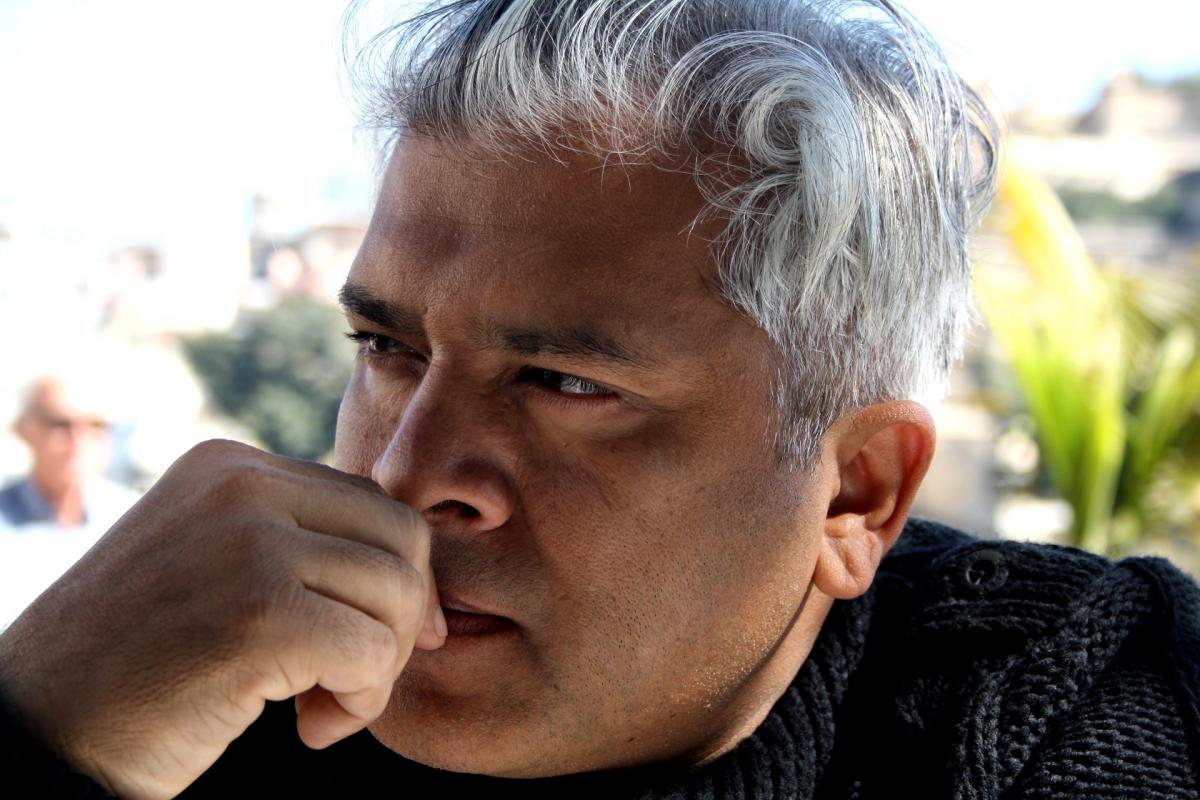許仁豪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專任副教授
-
 戲劇
戲劇誰的房間?何種大象?
極簡的空舞台,上舞台吊掛一整排半透明衣套,或半身或全身,燈光從後方照射過來,營造出一種若隱若顯的視覺;中間安插幾台洗衣店常見的抽風扇,不停地轉啊轉,與上方洗衣機的監控投影,兩相呼應,一方面營造出一種日常生活感,一方面透過影像的反覆播送以及風扇的持續運轉,讓日常生活的尋常節奏在藝術舞台上變成了一種「怪誕詭異」(uncanny)的非日常。再往上,舞台燈架上懸掛著各種真空包,像是辦案的種種證物,有小說、玩偶、各種殺人利器等等讓人聯想到節目單上所說之莫斯科三姊妹弒父犯罪現場蒐集而來之呈堂證供。循環播放的監視器影像壟罩在寫意的舞台上,在可見與不可見,有聲與無聲之間,日常表象的裂隙被打開,不可說的非日常逐漸滲透出來。舞台設計呼應著演出母題:房間裡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那個巨大的存在,但卻又秘而不宣地存在眾人的沉默之間,存在卻不可說,可見亦不可見。 在童話鐘聲的引導下,一身素白洋裝的三姊妹從吊衣架後方魚貫出場,怡君坐在下舞台唯一的一張椅子上念出她們的故事。上方螢幕以中俄語寫著:「女孩子是什麼做成的呢?鮮花和鈴鐺,謎語和果醬。」說故事的怡君用童話故事的語氣訴說著:「在莫斯科西邊的偏遠小鎮上,一座矮矮的紅色房子裡,住著爸爸最愛的三姊妹。他們穿著白色的洋裝,從不穿鞋子,但她們的襪子比雪花還白淨」如是,伊娜、克拉拉、跟絲娃波塔三姊妹以白雪公主一般的形象走到我們眼前,在童話世界的鐘聲裡,她們像是迪士尼樂園反覆登場的人物,行禮如儀,以偶一樣的編舞動作,上下左右,前前後後,以極佳的節奏陣列變化,演出紅房子裡的好女兒,爸爸的小公主,直到忽然風雲變色,父愛變成了囚禁壓迫的來源,在性的恥辱與初夜欣喜的交雜感受下,伊娜成了新的媽媽,三姊妹成了父權世界的禁臠,她們反覆循環扮演好女兒、好妻子的角色,旋轉木馬一般,轉成了無法停止的實驗室白老鼠,日日夜夜,無始無終,無有出期。
-
 戲劇
戲劇在現身與再現之間
從「南洋姐妹會」到「南洋姊妹劇團」,夏曉鵑帶領的外籍新娘草根社會團體,1995年開始的識字班,2003年成立南洋姐妹會,2009年成立劇團,透過劇場訴說姊妹的生命故事,至今走過22個年頭,算是台灣從社會草根組織發展成民眾戲劇團體的重要案例,除了實踐民眾戲劇作為一種文化行動之外,在歷年的展演下來,她們也發展出從真實自我生活提煉而來的獨特美學。 此次的《渡海.度老》由帶領石岡媽媽劇團的李秀珣擔任導演與劇本改編。從演後談分享的工作方法與展演的全貌來看,編創排練過程還是依循民眾劇場方法,以導演帶領大家共創共制為主軸,從各自的生命體悟出發,最後彙整出了一台素樸但卻動人的好演出。 演出雖然以雷蒂娜女士跟女兒李曉婷為主軸,但中間穿插多人多線平行交織的情節,形成一種多音複調,眾生百態的展覽式結構,而非一個單線起承轉合的閉鎖式完整結構。演出尚未開始,姊妹們合唱的歌謠便迴盪在劇場裡,滄桑的聲音追問著:「天茫茫,地茫茫,無邊無際太平洋,月光光,心慌慌,故鄉在遠方」歌謠唱出外配離鄉背井的辛酸,也對現場的觀眾們訴說身無可棲的淒涼。然而歌聲不僅只要訴說情感,還要追問,帶出演出作為一種提升社會意識的訴求。燈亮,演員姿態萬千地從舞台的不同方位登場走位有的滑直排輪移動過場,有的枕著枕頭用身體毛毛蟲一般橫斜過去;有的戴著面具,有的穿著水袖;有的仗著輔具單腳行走,有的推著輪椅出場。最後眾人匯集到了舞台中央,圍繞著輪椅形成一幅靜態的塑像群,演員爬上了輪椅,手持釣竿釣著前方的紙鈔。這個頗具詩意的開場明顯是從民眾劇場的「慾望彩虹」、「靜止雕像」與「意象劇場」發展而來,演員登場並非只是代言角色,而是在演員自我和創造的角色之間,打開了現身的空間,讓觀眾看到各自紛呈的慾望彩虹,以及在這個彩虹光譜背後無形的社會結構力量。新住民及其二代,在這個現行社會結構下,往往被到台灣撈金的刻板印象所烙印,在夾縫裡求生的非戰之罪往往是主流社會凝視之眼下的壓迫結果,從輪椅起身爬上釣錢,這個靜止的意象作為開場的定鑼聲,搶眼是搶眼,卻令在觀眾席間凝視他們的我們感到深深不安。
-
 戲劇
戲劇第四面牆內外的愛情
台南人劇團的《愛情生活》從首演至今,已經巡演多次,其以男色經濟打造出來的立基市場(niche market)長銷劇路線,除了突圍藝文觀眾同溫層,讓大量男同志族群走進劇場之外,也讓喜愛BL的腐女族群走進劇場。近來劇場圈的定目長銷劇風潮,大致上多半處理都會愛情或是婚姻主題,情情愛愛加上當代人孤單寂寞、真情難覓的議題,演員外型吸睛,舞台炫目好看,加上夠說服力的演技,大致上都能吸引一定數量的觀眾,比如橫向移植的音樂劇《LPC》,或是改編自流行IP小說的《婚內失戀》都創造出亮眼的票房,以及一再演出的風潮。 台南人劇團這幾年深耕男同志市場,也算是開創出了某種男同志都會觀劇風潮,而《愛情生活》則是其中的代表作。 乍看之下,《愛情生活》賣的是在男同志族群無往不利的男色經濟。舞台以酒吧夜店風打造,橘黃霓虹燈大大閃爍著「WORK OUT」兩個大字,呼應著男同志群體對於上健身房打造肌肉身材的日常現象,白磁磚搭成的方框底下閃爍著幽幽藍光,是夜店常見的燈光設計,框裡鋪滿著沙,中間是一個白色雙人浴缸;邊框上滿擺滿了象徵都會男同生活的時尚品味,純白色的瓶瓶罐罐可以是Muji的沐浴用品,也可以是Le Labo昂貴的東京限定城市香水款;拖鞋與內褲的品牌一方面標記著男朋友的品味與身分,一方面也是三角關係的戰場;更重要的是散落各處的啞鈴與拳擊手套,那是男子氣概的必備物件,也是整個舞台,男性氣質擂台賽的象徵所指,WORK OUT除了健身運動之外,作為英文片語也有解決、把關係處理好的動詞作用,在整個演出過程,兩個字除了指涉健身,也大聲地吶喊著,男同志愛情關係到底能不能成功,邁向婚姻修成正果的提問。
-
戲劇
後人類時代的人類展演
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在人文學術圈早已不是什麼新鮮的名詞,作為對人類中心思想的批判資源,「後人類主義」的風吹進表演藝術,除了引發學者開始研究動物的表演,比如早期馬戲團中的人與動物共演,也引發了多種非人類受眾的展演行為,比如植物音樂會,比如狗狗劇場。但這些研究或是展演多半停留在實驗或是概念層次,要真的蔚為風潮或是對表演藝術產生根本性影響,說真的,還有待觀察。 表演藝術中的動物登場,多半還是以「擬人化」(anthropomorphic)的方式出現;亦即,以擬人的方式賦予動物主體,讓牠們感知、表情達意、甚至思考與行動。藉此,動物從「牠」們變成「他」們的過程,便不再只是屬於人的「物品」,而成了自己的「主人」。但動物真的因此就獲得賦權,不再從屬於人了嗎?說實話,不論如何展演再現,動物的本體,只要是在人的認知框架下,便無能成為其自身。我們頂多能做的是在倫理學的層次上,打開人類與動物的主客界線,位移人類本位思維,在「擬人」手法打開的戲劇假定性時空裡,重新檢視人性,展演動物,最後關乎的還是批判性地認識人性本身。 如果從這個觀點切入魏于嘉的劇本《大動物園》,我們便能「聽」出劇作家,透過「展演性」(performativity)打開「人性」與「獸性」之間的辯證空間,最後取徑「表演動物」重新思索如何「變成人類」的倫理學命題。
-
 音樂
音樂超越感傷的悼念的藝術
由陳欣宜帶領的新古典室內樂團,發展多年,從古典音樂演奏與編創的實驗精神出發,努力嘗試跨界表演,突破傳統音樂會的編制與演出模式,在舞台布景、場面調度以及展演結構上,屢屢創新,這幾年來也是跨界藝術的話題團隊之一。 這次的《旗津白玫瑰.25紀事》取材自團隊發源地高雄的在地故事,以旗津「二十五淑女之墓」背後的工殤歷史出發,在追憶悼念與超越創傷之間,再度以跨領域藝術的方法,解構了「音樂會」的慣習,也突圍出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藝術語言。
-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 Feature劇場現代主義與文化冷戰
在我們熟悉的台灣戲劇史敘事裡,李曼瑰往往是反共抗俄劇的同義詞,她一個人幾乎等同了黨國威權時代的戲劇文化。因此,她的劇本必然是改革前的老派話劇,服膺於反共抗俄的正邪二分套路,千篇一律,了無新意,除了歷史的考據價值,應該沒有美學的價值。但事實上,正如同鍾明德把小劇場運動的起點拉到她返台後所開始的計畫,李曼瑰在台灣戲劇美學的變遷上應占有轉折性的重要歷史位置,對我來說,這便是劇場現代主義美學的引入。 李曼瑰為了「新世界劇運」,開啟了系列歷史劇寫作,比如《漢宮春秋》(1956)與《大漢復興曲》(1957),一開始固然受到黨國意識形態的指導,但她在西遊之後,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戲劇美學的洗禮,回國後積極推行小劇場運動,企圖在戲劇思想與形式實驗上突破,而因此出現了創作風格的微妙變化,而其中關於「歷史再現」的議題成為了其劇作實驗的核心。
-
 ARTalks
ARTalks持續直球對決的文化行動
編按:由差事劇團製作,段惠民執導,2022年6月首演於台北牯嶺街小劇場。演出透過一個奇幻爬山旅程的詭異寓言,回顧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歷史。
-
 戲曲 展演歷史,表演台灣
戲曲 展演歷史,表演台灣從《船愛》與《步月.火燒》的景觀化展演談起
最近高屏兩地不約而同推出兩齣大成本、大製作的歷史劇公演。首先是2月中旬配合台灣燈會在衛武營戶外登場的《船愛》,接著是3月底在屏東千禧公園,作為六堆300的旗艦活動《步月.火燒》。(註1)兩齣戲的取材與劇本結構十分不同,《船愛》由古至今,散點式擷取歷史片段,沒有完整事件的起承轉合,而是瀏覽式的匯集,歷史成了流轉的古今風景;《步月.火燒》聚焦單一歷史事件,情節來龍去脈完整,人物隨事件變化起伏,舞台上的歷史如同說書,以古喻今,曉以大義。
-
演出評論 Review
搜神與求道
天狗的文化意涵被挪用到當下的台灣,劇情走到最後,透過僧人的媒介,我們了解到天狗有可能只是宗房面對巨大創傷的心像投射,舞台上虛實的演繹,到了結尾也不讓我們知道到底天狗最後有沒有出現,成與敗、生與死都變成了一個謎,這個開放的結局,讓我們看見天狗作為一個搜神願望的視覺形象展現,在劇裡打開了關於超越歷史創傷,尋求個人解脫之道的哲學思考空間。
-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專訪《第十二夜》導演
阿圖.庫瑪 從自身源流 找到喜愛與真實的戲劇
即將帶著《第十二夜》造訪台灣的印度導演阿圖.庫瑪,本身的藝術歷程就是活生生的跨文化範例他接受過傳統印度武術、歌舞的訓練,也曾到歐洲受過義大利即興喜劇、默劇及肢體劇場的訓練,東方與西方的表演藝術在他身上激盪,也讓他在創作跨文化戲劇時有更深刻的思考。他以印度本有的Nautanki戲劇形式改編《第十二夜》,濃厚的節慶氣氛,風靡了世界各地的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