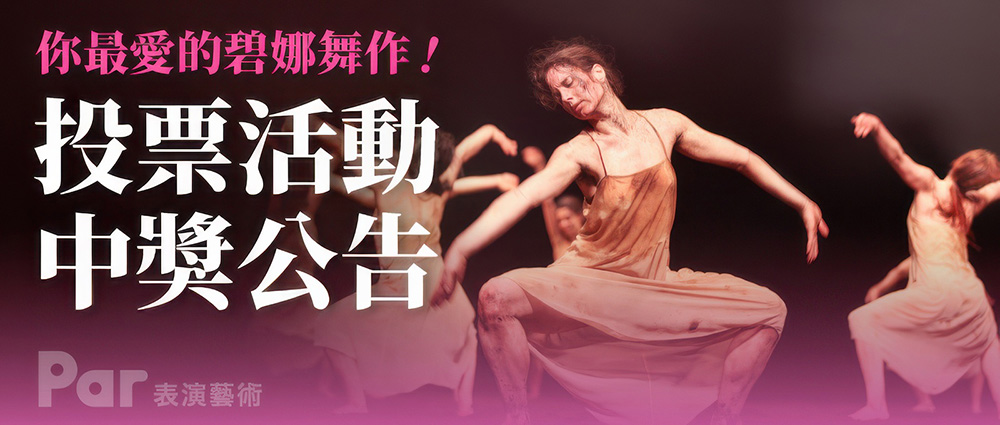「我們覺得時光倒流很美,像是某種既視感。既視感讓你感覺錯亂,讓你感受好像前世去過那個地方,這種生命裡有的東西,是AI不會有的。」吳天章說。
「把時間封存」,幾乎是他發展創作美學核心的芽。從時間出發,他折返回自己的童年,抽取裡頭的基隆印象;進行中的新作《尋找聖保羅砲艇》就是一個以時間為軸、勾描鏡像平行世界的作品:從童年的自己走在山路上的影像為起點,原來是要到基隆港圍觀《聖保羅砲艇》拍攝現場,影像卻引導了時光倒流,讓倒流的敘事沖刷返回原點。
「你們知道,28年後日曆會重覆嗎?」吳天章眼睛發亮地問。「28年前哪一天是星期幾,會跟28年後一模一樣。」(註1)他細數這個重覆:1966年《聖保羅砲艇》上映的日子,他10歲;28年後,1994年,他創作了從油畫踏入複合多媒材與數位影像的標誌性作品《傷害告別式》系列作及《再會吧!春秋閣》。再過28年,2022年他開始了《尋找聖保羅砲艇》(編按)的創作旅程——使用他熟悉的數位影像技術與一鏡到底的動態手法,把時間翻轉再翻轉,回到兩個28年前,他10歲的時候。
霧雨的基隆,真偽相伴的異國情調
不管是被歸類於「台灣當代藝術第一代」或被稱為「台灣藝壇解嚴第一人」,吳天章無疑地代表了那個眾聲喧嘩、百花齊放的時代開端。1970年代就讀文化大學時,正逢鄉土文學論戰高峰,他坦承自己深深受到那股批判寫實精神影響。「就像銘印效應,」(註2)他說:「如果當時沒有遇見那種人文批判精神,我可能不會做藝術到現在。創作是因為我對國家、對時代,有一種使命感。」
回看童年,吳天章說,1952年的《中日和約》決定了中華民國台灣的命運,「1956年我出生,所以我的童年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童年。」把自己的童年與國家的命運纏繞縫合,這讓吳天章所有對童年的記憶敘說總是帶藏了隱喻。
想起基隆,他說那必然是霧雨的灰濛、黎明前天將明未明的灰澀,「那就是我作品色調裡一定會有的東西。」灰雨中的舊式巴洛克建築,走調的現實感;或許就是在這朦朧的霧雨裡,世界變得似幻又真。
1965年越戰爆發,直到1979年中美斷交,這10多年間美軍依據《中美共同互助協定草約》派遣軍隊駐台,基隆港就作為美軍停泊、補給的港口,滿街是舶來品商行、美軍酒吧、軍官招待所,也有知名的鐵支路紅燈區。
「你問我童年與青春,一定會出現水手。在那個苦悶的年代,只有水手可以雲遊四海、可以夾帶一些舶來品進來。聽說他們下船前會把什麼都穿在身上,然後下船後一件一件脫下來,賣給委託行。當時批貨的人都是來自台北的有錢人。基隆人買不起,就仿製。」吳天章半開完玩笑地說,「所以人家說基隆出台客,這是因為基隆有一種倯(sông,俗氣)。」
「我們以前有一條牛仔街,賣的牛仔褲洗了永遠不會褪色。基隆就是這樣,充滿假假的顏色。」那虛假的、如幻似真的贗品情調,不只摹寫了吳天章的記憶,也成了他日後創作的重要元素之一。那些華麗、浮誇的偽贗物品:金蔥布、亮鑽、人造漆皮、塑膠花,是他90年代初期從油畫轉向複合媒材創作時開始使用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