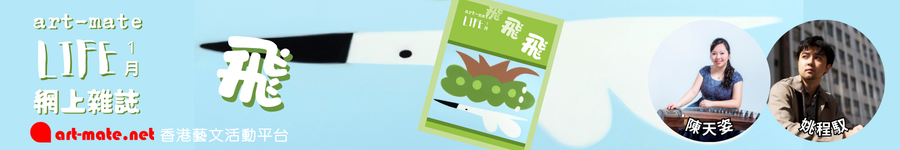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创作可不是一件只能在朝九晚五之间做的事」-罗伯.威尔森
编者按:
这果然是一次令人期待且充满惊喜的越洋专访。
透过主办单位的安排,我们邀请资深剧场工作者耿一伟为本刊专访这位纵横剧场多年的大师级导演。要专访大师,大家难免带著粉丝的心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就在我们一边交出题纲,一边e-mail往返跟大师的助理争取比二十分钟更长的访问时间时,竟已直接收到罗伯.威尔森的亲笔回复——他直接在题纲下一一爽快作答,简洁不啰唆,效率之高,令所有人喜出望外。看来在大师经常在作品里出现的「慢动作」,果然是有某种特殊意义,和他的真实人生完全不一样!
一九九八年时,我于布拉格的Archa剧院看了一个演出叫Bob (Bob是Robert的暱称),内容是一位美国人演罗伯.威尔森的创作片段、美学观念与个人轶事(无独有偶,几年后河床剧团也创作了《罗伯威尔森的生平时代》)。“Without Light, there is no space”这句话,就是当时听来的,印象很深刻。没想到,居然有机会在台北看到Bob亲身演绎自我创作历程,真是有点六度分离的感受。
访问大师的困难,在于出题。因为你不能问得很笨,这样大师会觉得你不够专业。也不能问得太艰涩,会让人家觉得你不礼貌。不能光凭自己喜好发问,要顾及到不同读者的需求。最后还得想办法,套出一些别人没得到过的答案。希望我对Bob的提问,能达到以上的目标。
问:威尔森先生,我想先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身为一位导演,您可否告诉我们,导演是什么?
答:导演就是在状况外观察整体,并给予作品一个焦点的人。一位好导演,还得懂得票房、广告、制作、灯光、舞台、动作、音乐、文学、建筑与绘画等;换句话说,也就是所有的艺术。一位好导演,不论是他或她,都是一个知道不能将工作独力全揽,会将责任与工作分派给一个团队的人。
问:人们认为您的作品属于后现代主义,对此您有什想法?
答:我从没去想这件事。
问:在您导演的作品里,经常充满了慢动作。您想对观众造成什么影响?
答:我的作品希望提供人们一个可以思考的空间。它牵涉到弹性的时间,要不就加速,不然就延缓。时间不是概念,它不属于智识。它是一件你可以经验的事。
问:您曾在别的地方提到「少了光,就没有空间存在」(Without light, there is no space)这句话,您是否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
答:因为有光,黑暗才真的变黑。因为黑暗,才感受得到光线的明亮。这就是空间的基本概念,也是空间的原理。
问:最近有部关于您的纪录片Absolute Wilson在美国上演。我也注意到,您只拍过一些实验影片如Slant或Video 50等。您既然如此多才多艺,当一位电影导演,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而且电影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您。既然如此,您为何不拍电影呢?
答:说实在的,我不喜欢电影,我偏好剧场,因为它是现场的。
问:实际上,您还导了不少歌剧。想请问一下,您认为歌剧与戏剧之间的差异何在?
答:对我来说,歌剧与戏剧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它们彼此间是息息相关的。歌剧处理的,是恰巧成为音乐的声音。而所有的剧场都是舞蹈,因为它牵涉到运动。这就是所谓的opera,它意味著一件作品,也就是opus。
问:您在解释一些想法时,经常提到「结构」(structure)两个字。可否告诉我们,「结构」对您和您作品的意义为何?
答:结构是让个体得以自由的框架,它让参与者获得自由。
问:您经常跟一些摇滚乐手合作,像Lou Reed、David Byrne与Tom Waits等(注1),都与您合作过。这是否反映了您的一些品味?您对通俗文化的态度为何?
答:我的作品是在古典与当代作曲家或作者间取得平衡。我的作品充满了多样性的风格与品味,这种多样性一直是个常数。
问:您如何让自己保持如此有创意?
答:我看不出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差别,两者息息相关。创作可不是一件我可以只能在朝九晚五之间做的事。
问:可否告诉我们,您最推崇那位导演或艺术家?
答:有许多剧场导演我都相当喜爱,而维斯康堤(Visconti)(注2)、巴兰钦(Ballanchine)、康宁汉(Merce Cunningham)、玛塔勒(Christoph Marthaler)(注3)等人,都是我推崇名单的一部分。
问:您出生在德州的Waco,您说过德州的景色充斥在您的作品当中。可否就此点为我们解释一下?
答:那是德州的天空、光线、灰尘、气味与广阔。还有声音里的颜色,以及对声音的感受。它们都成为我创作意象的一部分。
问:从一九七○年代开始,您在欧洲拓展您的事业,甚至连《沙滩上的爱因斯坦》The Einstein on the Beach也是在亚维侬首演,而且您还在一九九七年获颁欧洲剧场奖(European Theatre Prize)。请问您对您的欧洲经验有何看法?
答:我很感谢在过去卅五年间,有机会在欧洲工作。如果没有欧洲的经验,我的作品不会有今天的面貌。当我转头看看美国剧场,它看起来似乎是比较朴素与地方的。我们习惯自我封闭,切断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剧场的交流机会。我们总认为欧洲剧场是某种陌生的东西。对我来说,其实它并不那么陌生。
问:有时您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演出,像《哈姆雷特独白》HAMLET. a monologue或最近的《聋人一瞥的杀手》The Murder from Deafman Glance。演员对您来说到底意味什么?
答:演员是观众的催化剂,他是帮助观众听到与看见作品的人。他也是协助大众了解文本的人,更是对自己所作所为有自我主张的人,但他不会对作品霸王硬上弓。他邀请观众一起分享演出的片刻。
问:您在一九九二年成立的「水磨坊艺文中心」(Watermill Center)(注4),可否告诉我们该中心是如何运作的?
答:这是一个研究艺术与人文的中心,其理想是能为每个人开放。它也是我们审视过往艺术,与创造新作的地方。该中心为社区的人敞开大门,让他们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并有机会与他们合作。
问:您有任何有趣的计划要在未来展开吗,是否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
答:我正在筹备一个录像肖像展。他们会有真人大小,由高画质的平面萤幕来呈现。这些图像将会成为一种大混杂,内容包括一条狗、布莱德.彼特、一只青蛙、法国女演员伊莎贝拉.雨蓓(Isabelle Huppert)与珍娜.摩露(Jeanne Moreau)、西恩.潘、墨西哥女明星莎玛•海耶克(Salma Hayek)、黑豹党员、汽车修理工等。
问:您年轻的时候,曾教过学习障碍的儿童,也领养了一个叫Raymond Andrews(注5)的聋哑小孩。您还跟一位自闭症青年Christopher Knowles有合作关系(注6)。这些残障人士对您有任何意义吗?
答:是的,他们对我现在的创作有著极大(tremendous)的影响。
问: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因为您曾提过,当您面对一个新作时,您会先在完全无声的情况下排练作品。我可以说您是先用聋人的经验来看待剧场(就像您领养的小孩),然后再用正常人的经验(也就是您自己)来面对吗?
答:一位好的导演或演员,是能同时听到与看到内在心象与外在意象的人,也就说,我们同时都是盲人与聋人。例如,只要将眼睛闭起来,一个人就变成盲的了。
问:您在二○○四年于新加坡首演了改编自印尼史诗的I La Galigo。我们可以知道您对东方文化与剧场的看法吗?
答:东方剧场的面貌相当多样。不过就整体而言,亚洲剧场是形式化而非自然主义的。亚洲剧场最重要的部分,是将动作视为舞蹈。一般来说,亚洲剧场拥有一套可以教授与传承的视觉语言,像是姿势、舞台、布景或服装等。这跟西方剧场是大相迳庭的,西方视服装或布景元素为一种装饰。
问:对于您在国家剧院的演讲,台下观众可以期待什么?
答:它将是一件他们可以听到、看见与体验的事。
问:您的演讲会变成一场带有某种罗伯.威尔森风格的演出吗?
答:没错。
问:您对此行有何期待?您想参观什么地方或会见某人吗?
答:我从没到过台湾,我想尽可能地多看,从建筑、古物到通俗文化,都是我有兴趣的。我很期待去台湾。
注:
1.Lou Reed是庞克音乐的教父;David Byrne是八○年代美国新浪潮乐团Talking Heads的主唱,同时也是视觉艺术家;Tom Waits是美国地下音乐大师。
2.维斯康堤不但曾是义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的大师,同时也是知名歌剧导演。
3.目前欧洲当红的瑞士导演,玛塔勒曾任苏黎世剧院(Schauspielhaus Zürich)的艺术总监。
4.水磨坊艺文中位于纽约长岛,之前是发明传真机的Western Union公司的厂房。该中心除了放置威尔森创作品与个人收藏之外,并于每年夏天举办艺文课程。
5.在罗伯.威尔森早期重要作品《聋人一瞥》(1971),就是与Raymond Andrews一同创作。 例如《沙滩上的爱因斯坦》即使用了Christopher Knowles的诗作。
访问、翻译整理|耿一伟 国际剧评协会台湾分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