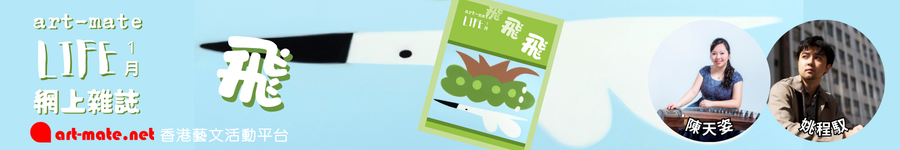比利时当代舞团即将于二月底首度来台,带来舞团创办人暨编舞家布拉德勒的最新作品《断章取“艺”-献给碧娜》。本刊特别于演出前以电话专访刚结束斯洛伐克等地巡演的布拉德勒。自承受碧娜.鲍许影响甚深的他,谈及碧娜时,即使自己已是蜚声国际的创作者,语气仍显羞怯兴奋,典型的粉丝反应;而面对某些可能已被问过百遍的问题,他的嗓音温厚和缓依旧,以最大耐心聆听并专注地予以回应。不论什么问题,他的重心都放在作为人的体认感受,这个舞蹈/剧场表演的核心,在他看来是天,也是地。
Q:先请您谈谈从一名特教工作者、动作障碍治疗师到专业剧场创作者的心路历程?
A:其实都是偶然机运促成的。一开始时我和亲戚、朋友们一起做些小作品,纯粹是好玩而已,有剧场导演看到就邀请我们去表演;大概六、七年后吧,我必须决定自己该回老本行还是继续做剧场,于是就想也许先试一下,看能不能够靠剧场表演过活。
Q:剧场一定有什么特殊魅力,让您这么一试就是廿多年?
A:剧场的魅力在于大家聚在一起做戏,人与人相遇的感觉很温馨,我喜欢。这么多年来我有绕圈子的感觉,早年特教及心理咨商的工作经验仍然是我现在作品的重要基石。
Q:您一直拒绝编舞家这个名号,有何特殊原因呢?
A:一开始大家称我为编舞家,将我跟安娜.姬尔美可、杨.法布尔等人并列在一起,感觉不太好意思,因为我不是舞蹈专业出身,也不会对著舞者示范动作舞句。在我的作品中,所有表演素材都是来自舞者本身,我只负责塑造出一种有利他们创作发想的环境气氛,让舞者充满自信并且可以非常放松,释放、表演他们,想要沟通的东西,这比较像是导演的角色。
后来我知道编舞“choreography”这个字与医学名词舞蹈症“chorea”有关,这是一种神经性疾病,手脚出现不自主舞动、不协调的症状,这就跟我作品中的动作表现很像呀,所以现在要是叫我编舞家,就感觉自在多了。
Q:您通常是如何开始一个作品的创作流程呢?
A:我的创作手法其实没有太大改变,都是在长期集体即兴工作过程中搜集与发展素材。各个作品都有其不同发生情境,譬如做Pitié 这个舞时,我的出发点是巴赫的《马太受难曲》,vsprs 则是蒙台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的音乐,这非常清楚。但是《断章取“艺”》一开始的东西就只有舞者的身体和探索肢体表达能力的欲望,并没有一个明确主题,对音乐、布景也没有特定想法。想要做这个表演是因为我知道碧娜.鲍许过世了,我去参加她的一个纪念仪式,感受深刻;碧娜对我影响深远,不仅是在编舞家这个层面上,更是在作为一个人的角度上,所以想要以这个作品献给她作为送别礼。
Q:碧娜舞作中,您最喜欢的是那一个呢?
A:《穆勒咖啡馆》。只有短短四十分钟,我大概看过二、三十遍,虽然我还是无法指认谁演什么角色;碧娜的身影,那些椅子移动的声响和音乐的搭配,都那么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看过就能理解为何她是这么伟大的编舞家。
有一次我替比利时Klapstruck 艺术节策展,特地选了十个经典舞作做呈现,《穆勒咖啡馆》就是其中之一。我当时还未曾见过碧娜,我知道她从来不曾单独表演过《穆勒咖啡馆》,总是要搭配著《春之祭》,而且只演一晚,还有我猜她应该不会愿意到鲁汶这小地方的一个小空间来表演吧。但是,我还是决定打个电话给她,没想到她愿意先和我谈一谈。天呀,我很紧张,毕竟她是我的偶像嘛,对我而言,她如同女神一般崇高。后来我去了乌帕塔(Wuppertal),他们还请我看演出,我根本就魂不守舍,完全不记得演出内容,只想赶快翘头走人。
后来吃饭见面时,碧娜说从来没有人跟她这样要求过──单单只演出一场的《穆勒咖啡馆》,她觉得很好玩。最后,她不仅答应来演出,还同意跟我做一场对谈讨论,她真的是一个很好、很温暖的人。
Q:在一篇舞蹈杂志的专访中,您曾说过碧娜教导您将重心放在个别舞者身上,除此之外,您的作品跟碧娜的舞蹈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A:我想我们都对人和人性怀有都有许多的爱,作品中也都显现有巨大的哀伤,还有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我的作品比较上而言有些黑暗,但《断章取“艺”》显然快活明亮多了,对吧?唉,生命是如此短暂,以至于无法承载这么多的爱。所以,我想要尽情过活,这并不是说我要找刺激尝鲜,而是在无聊之时也能够享受自己。
Q:我希望这样的无聊时光不会太多⋯⋯
A:其实很少发生,我所谓的无聊,就是缺乏动力去做事。举例来说,我现在身在葡萄牙一个小镇的旅馆中,在十一楼的顶楼餐厅用早餐,旁边环绕的是美丽的乡村景观,没什么特别的大事发生,但我想我不会忘记这一刻的。
Q:您现在就在国外,也一定曾经带著舞作巡演过许多国家,有什么地方特别令您难忘吗?
A: 我最近带著《断章取“ 艺”》去了斯洛伐克、克罗埃西,你知道扎格拉布(Zagreb,克罗埃西亚首都)那里十九年前有过战争,这影响了人们的思维,观众反应相当热烈。当然每一个地方的人反应,思考、感觉、行为模式都非常不一样,譬如说我的作品到了纽约,团员们都抱有很高期待,毕竟它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艺文中心呀!但是我们得到的回应却是两极分化,有人觉得很棒,许多人却是恨死了,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们表演的评论一向都还蛮正面的,纽约人还说这是欧洲出口的垃圾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还是习惯欣赏漂亮乾净的后现代舞,或是形式化的芭蕾表演。
Q:您采用的集体即兴创作模式,一路走来都没有任何改变吗?
A:一九九三年以前我习惯会先搜集一大堆想法、资讯,有系统地规划组织,做好事前准备才开始正式工作。但是在做BonjourMadame 的时候,我跟九名九到三十二岁的男性伙伴工作,其中包括职业舞者和完全没有舞蹈背景的人,我发现他们都对彼此很有兴趣,想要了解彼此对自己和周遭环境的看法,我在一旁看到他们探索彼此那种有趣的互动关系,当下便决定丢掉我事前准备的笔记和想法。就放任事情自然发展,我只是提供让他们舒服、有信心的环境,在旁细心观察,看看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
Q:您说一个舒服、有信心的环境,这是什么意思呢?
A:就是他们可以放心地表达与沟通心中的想法与情绪,并且他们知道我不会滥用他们提供的素材,如果过于私密或是太过极端、脆弱的部分,我会让他们知道并且自己决定到底要不要使用这些素材。重点是不要让他们做不愿意做的事,不管是生理上或是心灵层面上,我不想让他们陷入过于脆弱的情境中,我要保护他们。在做《断章取“艺”》时,有一段难度很高的快速舞句,本来我要求所有舞者一起跳,但是有三个人觉得会受伤,所以我就让他们待在外围,以自己的方式去呼应这段舞句。其实他们也知道,如果往自己身体、心理的极限边界去冒险开拓,虽然会有危险,但可能会挖掘出以前所不知道的事。
Q:这看起来需要长时间的经营与努力,才能够让他们卸下心防,敞开心胸,释放内心深处的记忆与想法。您到底是如何制造出这样的一种创作氛围呢?
A:这牵涉到一些实际操作方法,例如一起喝咖啡聊聊天啦,大家分享心情的感觉是很棒的,或是一起去看展览、看电影也都可以。
Q:您已经创造出独特动作的语汇,包括扭曲歪斜的身形、频繁的抖动震颤、失衡跌地和咬牙切齿、做鬼脸的表情等等,这些又常混合搭配著协调性高、风格化的流畅舞句,您到底希望要表现什么呢?
A:我一向都在试验当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情感之时,如何用身体动作来表现呢?在这些不太优雅,看似反常、丑陋的动作之中,我看到了美与诗意的存在,这让我无法抗拒。
有一次在比利时某处演完《断章取“艺”》后,有一个廿三岁我以前做特教工作时认识的男生来找我,他有肢体障碍疾病,身体会不自主抖动。他说好喜欢这个演出,并且相信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参加这种演出,这给我很大的成就感。他感受到我所讲的美与诗意,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做的。
Q:关于您所看到的美与诗意,可以再多说一些吗?
A:这些患有动作障碍疾病的人每天都在受苦。在我看来,他们比我们正常人更为有人的味道,对生活的可能性、缺失、困难与享乐,他们都更有感觉,更有能力去欣赏生活的种种,而这种能力我们却是忘记了或是忽略它,从而变得有些肤浅。他们比一般人更为敏感纤细,当我跟他们一起工作时,发现他们有自己特殊看待生命的方式。
Q:有评论说您早期作品强调不同个体在文化与社会政治层面的差异性,但是vsprs 却传递出宗教精神性讯息,您觉得自己作品的关怀重心可有发生重大变化吗?
A:我不大会分析我自己的作品,但是我有读那些评论文章,我会说现在的我比较会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情,譬如说以宗教性的命题如生、死与祭典仪式来刺激舞者,希望他们从中能挖掘出更多自己的真实面相。
Q:Wolf 是您休息三年后重新出发的作品,里面运用了狗为要角,把狗带上舞台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A:这个舞作场景本来就设定是荒废的购物中心,我想像中会有一堆野狗奔窜其中,所以就找狗来排练。然后我发现动物独特的身体及习性,或许也反映了人们被文明生活所压抑掩埋的一些东西。
Q:近些年来可有看过令您惊艳的舞台作品?
A:我自己是比利时编舞家如姬尔美可、法布尔、西迪拉比(Sidi Larbi Cherkaoui)的粉丝,他们的舞作常常让我感受良多。但是我特别想要提一个比利时剧场导演EricDe Volder,不过应该没有人听过他,他两周前过世了,六十四岁,一辈子跟同一批人工作超过二十年,早期作品只在他住的小阁楼里演出,后来有到大剧场去。他擅长以小人物平凡日常事物为发想题材,譬如有一次他在跳蚤市场找到个盒子,中间有一个老人家留下的小笔记本,舞台布景很简单,铺上地毯,演员脸上涂著油彩,以古老语言作为表达工具,表演则刻意雕饰风格化,但能够展现出堆叠繁复的潜意识内涵。
Q:最后一个问题,在现今电子数位科技虚拟影像全面掌控的生活世界,剧场舞蹈这样的现场演出,您认为其价值何在?
A:我想现在进剧场的观众都很有勇气,第一要付很多票钱,第二有很大的机率他们会败兴而返。不过重要的是大家来到剧场,集结在一起并谈谈生活经验的感觉是很好的。我以前的作品挑衅意味浓厚,现在就比较是把观众当作分享心情的朋友。以《断章取“艺”》而言,我带著它巡回演出有一阵子了,可以感觉到台下观众和台上表演者之间有很强烈的连结感,这种呼应关系应该就是买票进剧场的人想要追求的东西吧。
当然,职业观众如舞者、舞评和一般人的反应也有所不同,我自己总是试著融入每一场我看的演出之中,一再地去体会、感觉,从来都没有失望过。现在不同形式的社群生活如教会聚会、政党组织,或者以欧洲为例往昔村庄邻里群聚亲近的感觉,这些都逐渐在没落消失中。人们应该滋养这种社群凝聚的意识。看完剧场演出后,人们如果聚在一起喝啤酒时就演出有所讨论的话,就很棒了;如果隔天或下星期还能继续谈到这个演出的话,就真的有所贡献了。当然剧场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不过还是能发挥一些些影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