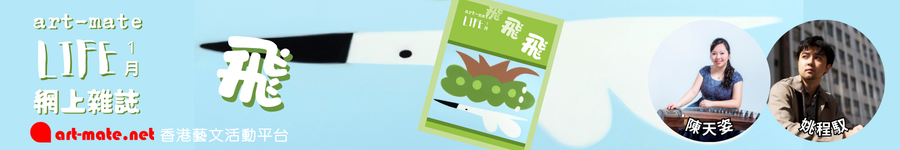不同于德国的舞蹈剧场、法国的浪漫抒情和美国的后现代舞蹈路线,却又包容上述风格,透过创作者个人背景、特质的加乘,揉合出「不只是跳舞」的创作趋向,在舞蹈的基础架构上增添剧场、Live音乐、艺术、时尚等元素,亦解散了人们对于舞蹈的定义,从中开创出新的表演/观赏视角。「愈混愈对」,正是比利时当代舞坛跃居顶端的关键。
比利时在欧洲国家中占地小,成为「国家」的时间也不长,然而,它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却造就出华丽缤纷的当代艺文风景。不若邻国德、法与隔海相望的英国那样拥有泱泱大国的鲜明文化传统/正统,却因地处欧陆对外的枢纽位置,两千年来迭经不同种族文化主导,使比利时对于「异质共生」能以平等、宽阔的视野包容。从比利时因应国内三大族群—— 荷语、法语与少数德语区—— 设立联邦政府分治,即可见证。
极简音乐谨严而逐渐翻转递进的乐曲结构,让姬尔美可演绎出形式简净中不断变奏的肢体语汇。图为罗莎舞团2006 年访台演出的Rain 。(刘振祥 摄 国立中正文化中心 提供)再加上首都布鲁塞尔作为北约和欧盟总部,无须费力寻找、创造在地性和本土性,比利时从先天到后天都注定作为一个聚合点。政治上的尊重异己,投射在比利时的艺术文化上则产生更超越的表现。无论是比利时当地出产的艺术家,或是前来驻扎创作基地的各国创作者,多半沾染上跨界/无界的创作风格,不甘受限于艺术既有的分门别类,人成事、事成人的结果,造就比利时前卫艺术之都的美名,无论表演艺术、当代艺术、时尚等累积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果。
比利时现代舞坛, 也在这样的体质下, 从一九八○ 年代莫里斯.贝嘉(Maurice Béjart)、姬尔美可(Anne Teresa DeKeersmaeker)、凡德吉帕斯(Wim Vandekeybus)、布拉德勒(Alain Platel)等创作者的大破大立、勇于尝试,来到廿一世纪的西迪拉比(Sidi Larbi Cherkaoui)、克丽斯汀.德.斯麦(Christine de Smedt)、Gabriela Carrizo和Franck Chartier等新一代舞蹈创作者的冒险奔放,俨然成为欧陆舞蹈重镇。不同于德国的舞蹈剧场、法国的浪漫抒情和美国的后现代舞蹈路线,却又包容上述风格,透过创作者个人背景、特质的加乘,揉合出「不只是跳舞」的创作趋向,在舞蹈的基础架构上增添剧场、Live音乐、艺术、时尚等元素,亦解散了人们对于舞蹈的定义,从中开创出新的表演/观赏视角。「越混越对」,正是比利时当代舞坛跃居顶端的关键。
从贝嘉的海纳百川,到姬尔美可的专注淬炼
一九五九年,法国编舞家贝嘉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表现代芭蕾舞作《春之祭》,此后迅速崛起,掳获欧陆观众目光,一九六○年更乘著这波声势于布鲁塞尔创立廿世纪芭蕾舞团(Ballet du XXmeSiècle),此后一路至一九八七年因比利时政府补助舞团经费协商失败、贝嘉愤而到瑞士洛桑之前,他几乎等于比利时舞坛面向世界的首席明星。
贝嘉的父亲是通晓东方哲学、能读中文的哲学家,影响所及,贝嘉对东方文化同样具深厚兴趣。更确切地说,他的兴趣广泛,阅读领域涵盖古今中外各艺文学术范畴,也因此,贝嘉的作品即便以现代芭蕾为根基,却能灵活地援引传统/当代、流行/另类等媒材,端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舞蹈作品。
贝嘉舞团曾于二○○一年来台演出的《生命之舞》Ballet for Life(1997),可说是他跨领域创作的典型。这支为纪念已故最佳伙伴乔治.唐(Jorge Donn)和皇后合唱团主唱佛雷迪.麦库雷(Freddie Mercury)而编的作品,以皇后合唱团和莫札特的音乐入舞,服装设计则是时尚大师凡赛斯。舞者从覆以白布的地面上蠕动、缓慢爬起,纯净的重生意象衬著华丽贲张的摇滚乐,浓厚的情感从酝酿到高涨,正是典型的贝嘉风格。
除了流行乐和凡赛斯,贝嘉的合作对象还包括摇滚天团U2、超现实绘画大师达利、日本设计师三宅一生、歌舞伎名家坂东玉三郎、天下第一腿的芭蕾女伶西薇.姬兰(Sylvie Guillem)⋯⋯等,各式各样的跨界合作,形塑了贝嘉视觉华丽、欲望横陈、宛如狂欢盛宴般的总体剧场风格,也成功让现代芭蕾招揽了主流大众的目光。
只是,比利时政府固然对贝嘉慷慨大度,却也因此局限了其他舞蹈创作者的空间。《当代欧洲新舞蹈─表演》(魏淑美,2010)分析,姬尔美可等比利时现代编舞家的发展之所以晚于欧陆各国,原因在于芭蕾长期占据政府关注目光,两大山头比利时皇家芭蕾舞团和贝嘉的廿世纪芭蕾舞团几乎是唯二受到补助的团体。于是,在姬尔美可离开贝嘉的Mudra School到从纽约习舞,后于一九八二年返国成立罗莎舞团(Rosas)期间,比利时的现代舞新生代仍在土壤里寂静无声。
姬尔美可的作品以结构性和秩序感著称,这是因为早期她深受美国后现代舞蹈影响,并多次引极简音乐大师史提夫.莱许(SteveReich)的作品编舞。极简音乐谨严而逐渐翻转递进的乐曲结构,让姬尔美可演绎出形式简净中不断变奏的肢体语汇。更有趣的,在于舞蹈出身的姬尔美可,除了对声音和身体之间的互相映照著迷,也酷爱将舞作改编/重制为影像版本。经典的Fase, fourmovements to the music of Steve Reich (1982)、Rosas danst Rosas(1983),分别于二○○○年和一九九六年拍摄影像版,其中Rosas danst Rosas 在实景拍摄,导演ierry De Mey取镜细腻捕捉了姬尔美可对空间与女性身体之间节奏流动的重新构思,开创以影片诠释舞蹈的崭新面貌。这个影像/舞蹈双人组合迭有新作,二○一○年七月在北美馆展出的「形、音、异:法国里昂国立音乐创作中心声音装置展」中,就有两人再度依史提夫.莱许音乐编制的舞蹈影片《俯拍》。
凡德吉帕斯和布拉德勒:「我不是编舞家」世代
姬尔美可的罗莎舞团领军在前,在一九八○年代伊始突围出现代舞的挥洒空间,到了一九八四年布拉德勒成立比利时当代舞团(les Ballet C de la B),以及八六年凡德吉帕斯的终极舞团(Ultima Vez),更预告比利时舞蹈不再只是专业出身创作者的擅场。
事实上,说凡德吉帕斯的舞作铭刻了台湾对比利时舞坛的印象也不为过。终极舞团先后于一九九九、二○○一、二○○三、二○○九年四度来台,其作品如《非关欲望》In Spite ofWishing and Wanting (1999)、《有关借来的人生》Inasmuchas Life is borrowed (2000)、《骚红》Blush (2002)等,影像与舞者在台上共舞是基本配备,戏剧性流动于舞者不以炫技为目的的肢体动作中,可以看见凡德吉帕斯擅长以不同媒材的对应关系,拉出舞蹈的哲思向度,而这和他心理学出身,同时也是剧作家、电影导演的多元创作身分有关。
凡德吉帕斯曾参与比利时鬼才艺术家杨.法布尔(Jan Fabre)的剧场演出,自立门户后,他受法布尔自由不拘的创作观影响,加上并无编舞背景,选用表演者也多非专业舞者,作品常被评为缺乏舞蹈语汇,但凡德吉帕斯对人体面对外来刺激的反射动作有极为精密的观察,从中发展出富张力的肢体动作,加上他拍摄的影片就像是呼应著真人舞台的异次元平行文本,因此他坦然面对「不像跳舞」的批评,更曾表述:「我不以『编舞家』自居,而是寻找不同的故事」。
同样不喜被视为「编舞家」的布拉德勒,则是借由特殊教育的所学、对身心病患的观察,发展出极为独特的肢体语言。布拉德勒的作品经常出现抽搐、颤抖、狂乱扭曲身体的舞蹈动作,却不突梯也不丑陋;舞台时而抽象离乱,时而将现实空间如超市等搬上台面,现场的音乐演奏亦融为表演一环,舞者开口说话、唱歌剧、被高高吊起都不奇怪。他的作品《巴赫浮世绘》Iets op Bach (1998)在一破烂场景中搬演底层生活百态,音乐则以王子(Prince)佐巴赫,却在纷杂的人生中逐渐涤出受难与渴求升华的企盼,此作一推出,被誉为比利时当代舞团与表演艺术的里程碑。布拉德勒的舞台常常很「乱」,却乱得令人如此熟悉且惊心动魄,其嘈杂反映了当代人内在的紊乱失序。虽然同样引起争议,毋宁说,他作品所呈现的空间,若仅用「是不是舞蹈」来评价就小觑了。
此外,比利时当代舞团也非传统一人领军的封闭式舞团,而是作为一个资源共享的开放平台,除了布拉德勒外,其他编舞家也在此进行创作,使得比利时当代舞团从形式到内容,彻底实践了开放、多元、平等的观念。
不断越界,汲取他人之长的比利时创作力
近年席卷全球舞坛的西迪拉比,正是自《巴赫浮世绘》加入比利时当代舞团创作的明星舞者与编舞家,其出身亦颇能对应舞团融多元于一炉的风格。
摩洛哥裔的西迪拉比,出生于比利时前卫艺术之城安特卫普(Antwe r p) 的一个中下阶层家庭, 从小爱舞、爱东方功夫的他,直到父母离异后才一圆跳舞梦,进入姬尔美可于一九九五年创立的「表演艺术研究与训练工作室」(Performing Arts Research and Training Studios,简称P.A.R.T.S)研习。毕业后的他逐渐崭露头角,被布拉德勒邀至舞团合作,随后陆续与凡德吉帕斯(it )、莎夏.瓦兹舞团(D'avant )、阿喀朗.汗(《零度复数》)等舞坛明星,以及佛朗明哥舞者(Dunas )、少林寺武僧(《佛经》)合作;事实上,欧美各大舞团几乎都有他联合创作的足迹。他的灵活度在于与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合作,每每能迸发出强烈火花,而身为七○年代后世代,对于流行大众文化的广纳吸收,以及扎实的身体技巧,更对他的跨领域编创大有裨益。
至于同样从比利时当代舞团出身的Gabriela Carrizo和FranckChartier各为阿根廷与法国舞者,离开舞团后创立的「偷窥者舞团」(Peeping Tom)也是这几年炙手可热的新团体。虽然作品量少质精,成团至今仅四支作品:《院子》LeJardin 、《客厅》Le Salon 、《地下室》Le Sous Sol 与32 rueVandenbranden ,其剧场与舞蹈肢体并重的演出,以及舞台空间的巧妙运用(从作品名称即可获知空间的关键性),创造出令人时而战栗、时而感伤落泪的表演。以二○一○年的新作32 rue Vandenbranden 为例,两间在雪地上由车辆改装的房子,表演者出没里外,是温暖与冷冽的对峙和交集,而舞蹈在这宛如电影场景的空间中,更扮演著将日常转换为惊悚/孤寂/哀怜等诗意情境。剧场、舞蹈、音乐、场景均衡地构筑成整场表演,看了这样的演出,怎么再强求舞蹈、剧场、影像继续分门别类地被定义呢?
比利时舞蹈的越界演出,从一九六○年代贝嘉的鸣枪起跑,到八○年代鼓吹跨界交流与异质融合的整体艺文环境,提供编舞家、非编舞家上阵开疆辟土,终于让这个蕞尔小国成为欧陆艺文输出的劲旅。比利时的艺术家不倡议、寻求所谓的本土性,而是以更开放大度的心胸,融合自身专长与对生命关注的核心所在,因而能够超越既定范畴进行创作。「兼容并蓄」为比利时开辟了一片天,或许值得同样多元文化、却往往陷于定义、本质泥沼的台湾创作者寻思、反刍── 挪开框架之后,创作的向度将无限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