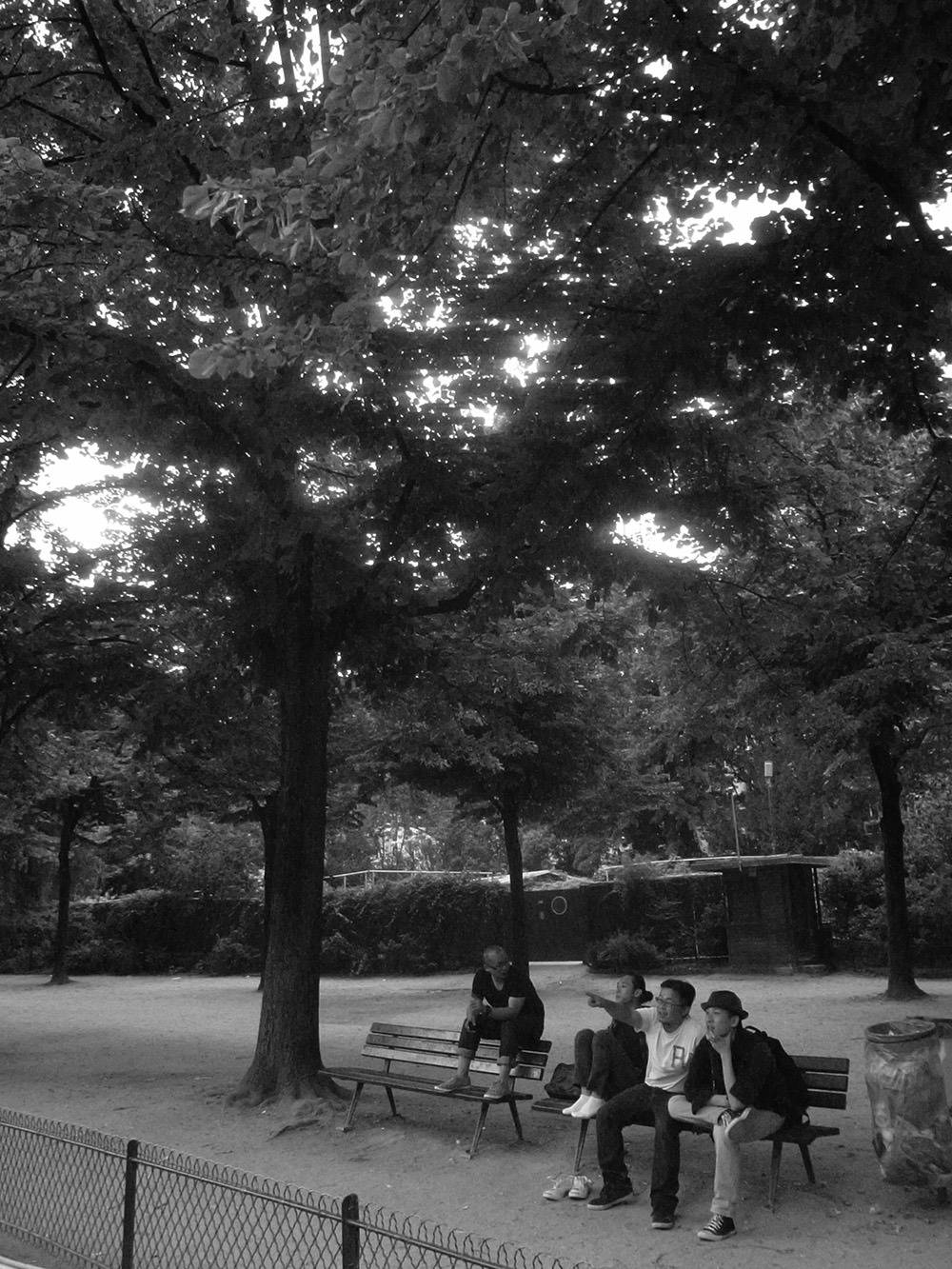曾伯豪之于台湾剧场,应是一种崭新的存在。
以近期两出代表作为例:在阮剧团的《鬼地方》,他是音乐设计及出演者,并不被归类于演员,也不受限于仅仅是音乐演奏者的角色。而在何晓玫舞团的《林投姐,妳叫什么名字?》,他所扮演的说书人,且唱且说,同时担任引路人的角色。
曾伯豪与剧场的关系经常如此,不被任何符号定义,不被任何概念束缚,他用自身的能力自由地成为各种故事的线索,流动于期间。
音乐像是他的本能,却不是他唯一的才能。
2025/8/7 19:30
2025/8/16~17 19:30
2025/8/17 14:30
2025/8/23~24 14:30
2025/8/23 19:30
台北 PLAYground空总剧场
2025/9/6~9/14
台北 西门红楼
无法轻易给予标签的艺术家
曾伯豪很难被定义。或许,他也不是很在乎自己怎么被定义。
高中组乐团唱歌,而后就读台南艺术大学、转进材质创作与设计系,看似与音乐渐行渐远,然而,期间向周定邦先生学习台湾念歌,又像是重新被打开一扇音乐的大门。而后,他进入北艺大艺术跨域研究所以后正式与各种剧团合作,以音乐家的身分成为表演中的一种声音、或以声音成为其中一位演员。
如此经历,成就他多元的艺术养分,放在哪里都能突显特色。
近期,曾伯豪与阮剧团合作的《鬼地方》便是一例,担任作品中的音乐设计及乐手,却不仅只是演奏乐音之人,过程中他以清脆的铃铛暗示禁忌敏感词汇的出场,剧末,在彰显阴阳交界的结尾之处,曾伯豪以招魂的长竹插入他改造的月琴上,哭声、琴声、竹子反复摩擦的嘎嘎声响,竹影、人影交叠如鬼魅。震撼人心。
今年9月,即将在西门红楼登场的《林投姐,妳叫什么名字?》亦然。担任场上的说书上,他以歌声串连这部沉浸式作品的故事线。声音魅力固然重要,然而有些隐藏在歌曲中的线索也安置其中,例如前期歌曲的尾韵「ai」作结、曲终之际则归于「i」韵收起,具体而微地象征这个民间传说的核心——所谓疑问,从「爱」而起,最终祈愿,能抵达平静的尾韵。
他是音乐家,也是艺术的实践者。即便才三十出头,声音却有一种世故的苍茫与穿透能力。
好像他的生命历程是一把直直射出的箭,瞄准哪里早已确定。
但回头来看,根本不是如此,曾伯豪的许多精力,甚至不能说是无心插柳,且多只是误打误撞,却没想到撞出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执著,以及对多种音乐的感受能力。
曾伯豪
台北艺术大学艺术跨域研究所毕。从小学习中国音乐,高中时历经西洋摇滚乐冲击,而后师承周定邦先生学习台湾念歌。2012年与友人创立「迷宫回廊」乐团,2013年参与「小嫩猪」乐团。2014年创立「鬼讲堂」,与表演者吴宗恩、戴开成共创改编噍吧哖事件。2018年于台北和鸣南乐社学习南管。近年常参与剧场与声音相关创作,曾与各国艺术家如Kitt Johnson(丹麦)、坂本弘道、内桥和久、千野秀一、李世扬、李慈湄、黄思农等合作或即兴音乐交流。近来在音乐间流浪以及尝试理解何谓「在当场」,除鬼讲堂计划试图理解抗日事件中的多重叙事问题及背后社会成因外,音乐作品则与社会议题及个人情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