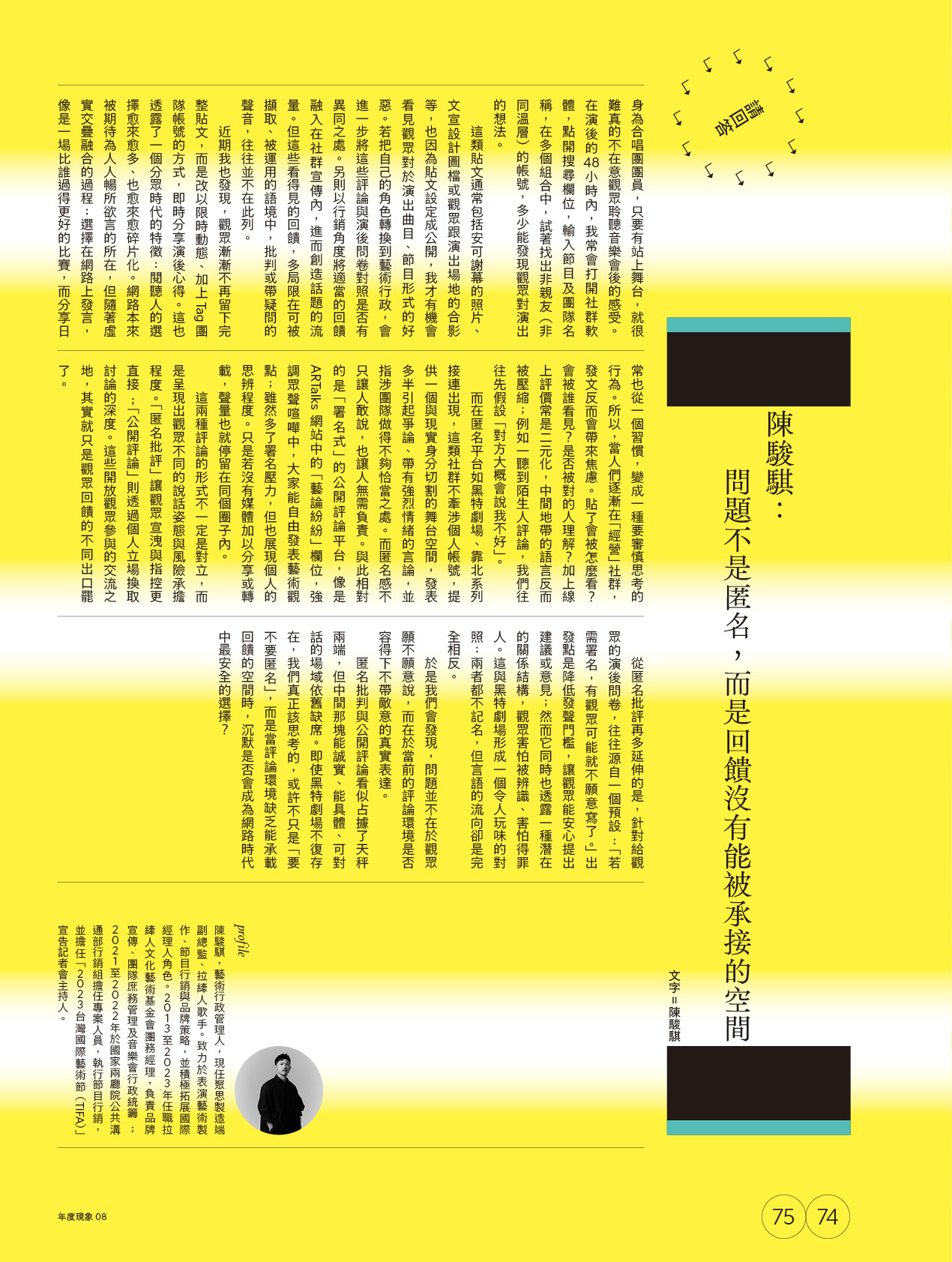盛夏柏林,當大部分公立劇院關上大門時,位於米特區(Mitte)哈克謝爾市場(Hackescher Markt)的一處庭院裡,有一間劇院依然燈火通明、人群熙攘。走上2樓,迎面而來的並非傳統舞台正襟危坐的觀眾席,而是小酒館式的桌椅配置。前台人員帶位後送上菜單,觀眾點上一杯酒或輕食,隨即被包裹在一種親暱、放鬆以及共享的氛圍裡。不同於一般劇院常見的年輕觀眾,放眼望去大都是大人帶著孩子的家庭客群。
這裡是專門上演當代馬戲作品的變色龍劇院(Chamäleon Theater Berlin,簡稱變色龍),在柏林這個表演藝術高度發展的城市裡,馬戲從一種邊陲娛樂轉化為具有創作語言與社會議題承載力的表演形式,變色龍劇院可說是這場轉型的催化場域之一。

從傾聽與嘗試開始重生之路
變色龍劇院創立於 1991 年,正值柏林圍牆倒塌之際。那是一個充滿自由、反叛與想像的年代。「最初的變色龍,其實是一個由藝術家經營的綜藝劇場,」現任藝術總監安克・波利茲(Anke Politz)說,「他們想演什麼就演什麼,對抗所有既定規則,反叛、自由、充滿能量。」
然而隨著城市氛圍改變,觀眾逐漸習慣以「買票」而非「參與」的心態走進劇場,原始團隊最終破產。2004 年,波利茲所屬的新團隊接手劇院,從零開始摸索未來方向。她坦言:「我們不是某天醒來就說『來做當代馬戲吧』,而是在傾聽藝術家、嘗試新形式的過程中,慢慢走向這條路。」
關鍵時刻出現在 2005 年。劇院邀請來自加拿大的七手指特技劇場(The 7 Fingers)帶來作品《閣樓》(Loft)。波利茲清楚記得那場震撼:「這是一個關於『一起生活』的故事,7位創團成員像是住在同一棟公寓。我們第一次看到馬戲也能這樣說故事,完全被打開了。」

擺脫標籤,打造當代馬戲的定位
在德國,「Varieté」長期代表著娛樂性質的綜藝場。變色龍初期仍使用這個詞,但很快發現它過於保守,無法反映劇院的企圖。「人們一聽到 Varieté,就以為是傳統、老派的娛樂。我們逐漸放棄這個詞,開始說自己做的是『Neuer Zirkus』(新馬戲)。」波利茲說,這樣的用語轉換,在當時的德國藝術語境裡幾乎是挑釁。「很多人質疑:一間劇場怎麼可以說自己是馬戲?但我們一步步證明這就是我們的工作。」直到第15年,變色龍才讓媒體、觀眾與資助單位接受「當代馬戲」的定位。
波利茲強調:「我們是一邊實作、一邊學習,一步步調整,才慢慢建立出變色龍今日的樣貌。」引薦世界各地的馬戲作品和柏林觀眾見面的同時,變色龍也吸收來自不同文化的啟發:加拿大的團隊精神(ensemble)、法國的「馬戲戰爭」辯論(即當代馬戲與傳統馬戲之間的斷裂),以及德國本地獨立創作者的能量。一如劇院的名字「變色龍」,她形容:「每邀請一個團隊,就像換了一種顏色。我們持續開放、挑戰自己與觀眾的舒適圈。」

與駐演團隊成為夥伴一起共創
儘管經歷多次轉型,變色龍劇院的核心使命始終清晰。「我們承襲創始者的精神:創作者必須擁有完全的藝術自由。」波利茲強調,「我們希望創造一個空間,讓藝術家能自由創作,也讓觀眾進入一場真正的對話。馬戲不該有第四面牆,觀眾不是被動觀看,而是一起參與、互相傾聽。」
身為藝術總監,波利茲表示,策畫節目這件事,從來都不是單向的「挑選」,更像是關係建立。「我們的考量永遠是:這個作品是否能與觀眾建立真誠的關係?演出是否具有持續5週的生命力?團隊是否願意與我們一起共創?」
變色龍劇院最著名的特色之一,是給予年輕團隊第一次長期演出的機會。波利茲說:「很多創作者在作品還在構思時就找到我們,我們會走進排練場,不是為了審查,而是理解他們的語言與動機。」
例如,去年與來自加拿大的新興馬戲團隊「觀察者」(People Watching)合作《裝死》 (Playdead)的過程中,劇院建議他們調整舞台語言,以符合觀眾視角與長期演出需求。「我們不是干預,而是一起創造變色龍版的作品,」她強調,「成為平等的藝術夥伴,不是出錢的主導,而是共謀者。」

替作品創造觀眾,而不為既有觀眾找作品
20年前,德國幾乎不存在當代馬戲的觀眾,變色龍必須一步步培養看馬戲的氣氛與情境。波利茲坦言,確實有過「我們喜歡但觀眾不買單」的節目,但這是策展的風險之一,「我們不只是為既有觀眾選作品,而是替一個作品創造觀眾。」
她描述觀眾教育的努力:「我們會做導聆分享,讓觀眾能進入他們本來不會主動靠近的作品語境。這就是觀眾發展的核心。」此外,每年1、2月的「Play」系列成為推動觀眾教育的重要平台。「我每場都上台問:誰是第一次來變色龍?結果有七成舉手。」這代表城市裡仍有龐大的潛在觀眾,只要給予機會,他們便會走進劇院。
打造資源循環的生態系
2020 年的疫情迫使劇院停演,這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第一次被迫取消所有演出,那一刻我們問自己:如果世界不再熟悉,劇場還必要嗎?」波利茲回憶。
劇院沒有急於轉往線上,而是選擇「向內」。團隊固定聚會,閱讀、學習多元共融的知識,並重建組織文化。波利茲認為:「我們不只是要回到原本,而是要蛻變。3年的沉澱讓我們成為一個面對未來的機構。」
變色龍在 2022 年正式轉型為非營利組織,這是多年累積下的必然選擇。早期,因缺乏公共資金,劇院只能以私人商業劇場形式營運,全靠售票維持生存。「我們不是為了賺錢才經營劇場,而是別無選擇。」波利茲坦言。
但隨著時間推進,團隊逐漸意識到,他們打造的其實是一個「生態系」:藝術家的平台、觀眾與創作相遇的場域。而疫情更加速了轉型,「我們決定正式登記為非營利,才能建立募款、會員制度,才能讓更多人支持當代馬戲這個仍被忽視的領域。」
劇院也推動「團結票」(solidarity ticket)機制,讓有能力的觀眾支付更高票價,補貼弱勢群體以低價入場。排練場則以「有資源者付費、無資源者幾乎免費」的模式運作。波利茲認為:「真正的文化機構應該讓資源彼此循環,讓強者扶持弱者,這是一種價值選擇。」

馬戲是個開放的容器
波利茲堅信馬戲比其他表演藝術更能觸及大眾。它跨越語言與階級,任何人都能感受身體的張力與風險。「即使你從未看過當代馬戲,你仍能理解舞台上的風險與美感,」她解釋,「它不需要預備知識,卻能承載複雜議題,從移民、創傷到身體政治。」她強調,這正是變色龍長年投入的原因。「馬戲是個開放的容器,能談愛、孤獨與人際關係,也能觸及政治與社會問題。」
談到性別與文化多樣性,波利茲直言:「傳統馬戲充滿刻板印象,『強壯男人抱起輕盈女人』這樣的場景非常典型。」當代馬戲則有機會翻轉這些規範。變色龍會優先邀請處理性別議題或挑戰舞台規則的作品,也積極為不同背景的創作者創造空間,創造被看見的機會。
文化預算刪減下的結構隱憂
柏林的創作能量向來旺盛,然而,近年政府的文化預算削減,讓未來不確定性加劇。波利茲觀察,許多藝術家長期定居於此,作品開發、測試演出頻繁。「表面上很繁榮,但沒有制度性支持,這種生態其實不穩定。」例如,變色龍曾嘗試申請進入市府的4年期補助計畫,雖獲評審推薦,卻因政黨輪替而胎死腹中。波利茲坦言:「創作能量是有的,但結構正在退潮。」
對波利茲而言,最大的願望是某天不必再為「生存」辯護。「我希望我們的能量能專注在探索與創造,而不是疲於奔命地證明自己值得存在,」她說,「當代馬戲應該自然地成為藝術生態的一部分,而不再被視為一場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