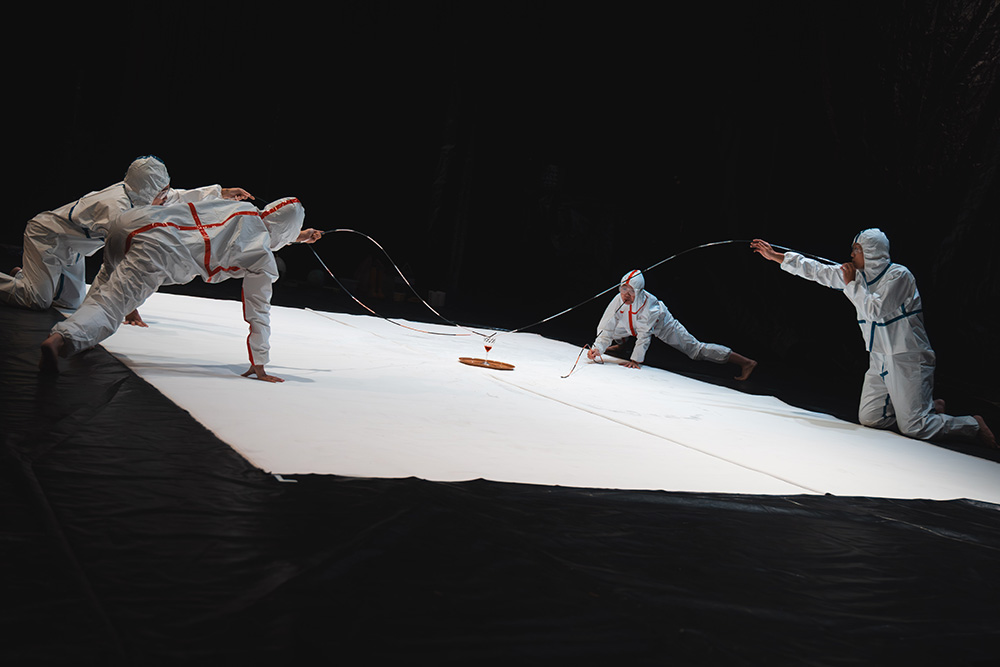班雅明的神秘洞见、杨逵的冷静义愤、宫泽贤治的世故童话,看似矛盾冲突的素质,在他们生命中冲激结合,组构了奇异的透镜,再从那无法模仿、复制的透镜中,折射出永不褪色的光谱来。
班雅明的好友修伦(Gersham Scholem)向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提议,应该编集班雅明生前写过的书信,看看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机会可以出版。阿多诺同意这确实是件该做的事,但他担心:班雅明从来不曾真正是个「名人」,在他过世二十几年后,还有多少他写给人家的信能够保留下来呢?
修伦和阿多诺分头连络班雅明的亲戚、朋友,没多久,出现了让两人惊讶的效果,大量信件从世界各地出土,许多人愿意捐出他们手上的班雅明原件。
阿多诺知道班雅明生前勤于写信,他惊讶的是有那么多他写出去的信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这些信,这些信奇迹似地保留下来的事实,引发阿多诺写了一篇题为〈写信者班雅明〉的文章。
认识班雅明的人,读到班雅明写的信的人,必定感受到某种神奇的、特殊的东西,才会让他们,不分男女老少,不同国籍不同职业,很自然地会把他的信留下来,不随便丢弃,一留留了超过二十年。
班雅明是个奇迹的观察者
阿多诺引用沃尔发特(Irving Wohlfarth)的话说:班雅明从来不曾「直接经验」,他整个人像片屈光透镜一般,任何事物一经过他,就展现出「折射的彩晖」。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位德国哲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的话说:班雅明是个奇特的观察者,他总是在边缘、琐碎的事物上,发现了人生、世界、宇宙最核心的意义。我们不再能够分辨,这些「边缘上的核心意义」,究竟本来就在那里被班雅明挖掘出来,还是根本是班雅明发明、赋予的。
曾经帮班雅明翻译过其少年回忆的塞尔兹(Jean Selz)讲了这样的事:冬天时塞尔兹将壁炉生火,最底下放上火种,再来是几块木炭,上面是细柴,最上面是大木块。火生起来,班雅明突然对他说:「你简直像个小说家。」塞尔兹疑惑地看著班雅明,班雅明解释:「是的,没有比火堆更像小说的了。你必须小心架构,一块叠一块,达到完美的平衡……架了要干嘛?为了毁灭,为了有效地毁灭。小说也是这样。所有的角色一个个彼此相依,形成完美平衡,而其真实的目的,小说的目的,就是毁灭这些角色。」
没有别人这样看待生火,这样看待小说,然而班雅明这样说了,听到的人突然就对生火这回事,尤其是小说这回事,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们不一定说得清楚这感受是什么,然而当我们想著,『小说用角色架起完美结构,最终为了有效摧毁这一切』,以前读过的每本小说,就都有了不同的意义,对我们放送不同的讯息来了。
将经验折射成为某种既神秘又美丽的智慧
就连班雅明做的梦,都让人震骇。一九三二年六月他梦见:德皇威廉二世在高等法院受审,原告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指控德皇毁了她的生活。老太太带著小孙女出庭,为了证明她们的生活再悲惨不过,她们带著仅有的财产,一支扫帚,和一颗颅骨,那颅骨是她们唯一找到可以用来吃饭喝水的器具!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样的梦境,不过这梦和班雅明的著作,同样符合布洛赫的描述:「在令人惊异的、最特殊的,最无法预期的现象中,班雅明带我们到达事物的核心,平常的大字眼或广泛现成脉络无法描露的核心。」
那梦,揭露了皇权政治的核心,不是吗?班雅明在他所有的著作里,一而再再而三如此揭露、至少是如此暗示。
回到阿多诺。阿多诺认为:书信对班雅明如此重要。在个人不断被异化、主体不断被消磨吞噬的机械文明时代,只有在书信里,第一人称「我」,还有真实的「我」的分量。书信里的「我」,保留了最多经验性的「我」,而不是人云亦云概念式的空洞发言位置而已。
可是即使在书信里,讲述著一般经验的班雅明,却总也不会停留在简单的经验里。他根本无法直接转述经验,必定将经验折射成为某种或神秘或美丽,或既神秘又美丽的智慧。折射后的经验,依然留著强烈的经验连系,班雅明从来不是个抽象空想的哲学家,他的「左派性格」扎扎实实展现在他的知识思想的现实经验性上,但他的经验,比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丰富了不知道多少倍。
显然人对于这种折射过的经验放出的光彩,有一种直觉的领悟与珍惜。至少,收过班雅明亲笔书信的人,有直觉的领悟与珍惜。他们明了班雅明的书信中,藏著可贵的东西,不忍丢弃。
用生命写作、用文字表达的作家
并不是因为班雅明有名,不是因为这些人预见班雅明今变得有名。不,生前死后,很长时间班雅明都只是个倒楣的人,老是在不对的地方碰到不对的事的人。他从德国逃到法国,却在法国进了犹太集中营。一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他想越过庇里牛斯山偷渡进入西班牙,却在边界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一听说第二天要被送回法国维琪,班雅明不知是出于愤怒或沮丧,吞食了大量安眠药自杀。
倒楣的遭遇,阻挡不了他那块生命透镜作用出的光芒。在帮班雅明文集写的〈导读〉中,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用了一连串「不是」来形容班雅明:他不是学者、他不是语言学家、他不是神学家、他不是翻译家、他不是批评家、他不是历史学者、他也不是诗人不是哲学家。
但班雅明是个「作者」,是个「作家」,如果「作家」意谓著「用文字创造出一个独特世界的人」。他是用生命写作、用文字表达的作家。他真心做的、真心完成的、是不断吸收经验,却将经验消化吐露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智慧视野。
因为对经验的紧抓不放,使得班雅明和世俗那么近;然而又因为坚持不让经验直截显露,班雅明却又和人群保持相当距离。他是个左派,但我们无法想像他投身、融入任何群众运动中,他是个不运动的左派运动家,不革命的左派革命家。
某个意义层上,杨逵和宫泽贤治,也都是贴近世俗却又远离群众的作家。他们的写作后来没有脱离过一个真正的、机械工业时代之前的主体『我』。写作对他们而言,不是手段,本身就是目的,消化改造世俗经验所产生的一种折射视野。这样的作家,生命与作品完全分不开来,不过他们让生命与作品连结的方式,却不是靠一般的感官经验,而靠超越的必然力量。
班雅明的神秘洞见、杨逵的冷静义愤、宫泽贤治的世故童话,看似矛盾冲突的素质,在他们生命中冲激结合,组构了奇异的透镜,再从那无法模仿、复制的透镜中,折射出永不褪色的光谱来。
文字|杨照 作家《新新闻周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