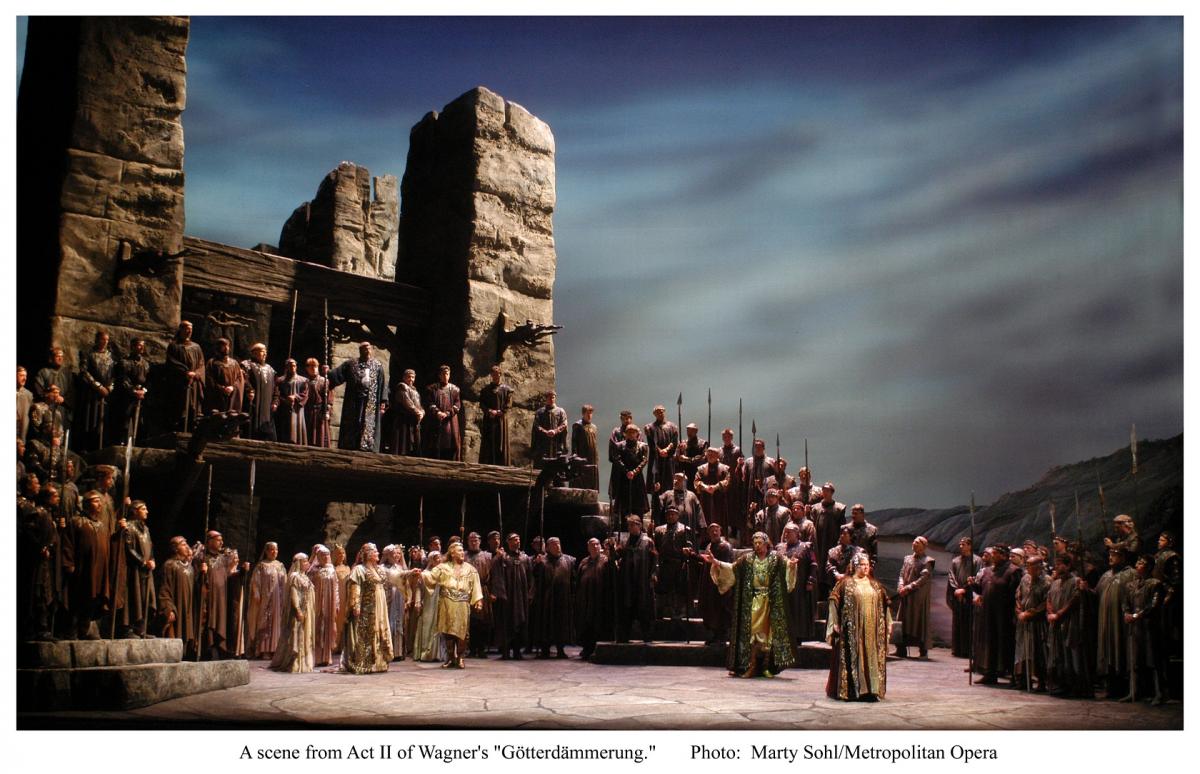来自中世纪的一则神话传说,如何在历经文学家的敷陈说演下,到华格纳手中挥发出强大的魔力,进而让世人沉迷百余年?华格纳到底想透过《尼贝龙指环》说些什么?是权力的虚无,还是真爱的永恒?
神话,总是特别令人心醉神迷,那千变万化的人物、曲折迂回的故事百态,它诉说的再也不仅是一个神话故事那般单纯,是人性缩影的映照。法国人类学家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曾说:「我不是要指出人如何在神话之中思考,而是要指出神话如何在人们心灵运作。」的确,每则神话总会留下些许怅然、情思、渴望或惊喜,那是在人们心中一个始终解不开的谜题,演绎著始终未完结的故事,《尼贝龙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便是如此。
尼贝龙的神话与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
日耳曼的神话文学中,尼贝龙传说一直是饶富色彩的一段传奇故事;它随著世纪的更迭,绵延传承了下来。中世纪之时的英雄史诗《尼贝龙之歌》Nibelungenlied应是最早遗留下的手稿,一四七二年则又出现冠上《身负鳞角的齐格飞之歌》Das Lied von hürnen Seyfrid标题的手抄,当中讲述的多是关于日耳曼神话英雄齐格飞(Siegfried)的蜚语。尼贝龙的魅力历久不衰,一七七二年它更以散文般的记叙式变体呈现,摆脱了史诗的框架,融入了德意志浪漫散文的元素,带领著神话传说迈向新颖的文艺风格。
神话的洗涤确实赋予艺术界无尽的灵感,尤其在十九世纪的德国更掀起一股应和神话的文学旋风。德国小说家与剧作家傅凯(Friedrich Heinrich Karl Fouqué, Baron de la Motte)在一八○三年首度完成了《打铁舖中的鳞角齐格飞》Der gehörnte Siegfried in der Schmied的草稿;若干年后,他将此改写为《北方英雄》Der Held des Nordens的戏剧三部曲,分别为《弑龙者之齐古尔德》Sigurd der Schlagentöter、《齐古尔德的复仇》Sigurds Rache与著重描写齐格飞与布伦希德(Brünnhilde)之女的第三部《阿丝劳格》Aslauga。一八二八年,剧作家劳帕赫(Ernst Raupach)也推出了五幕名为《尼贝龙的宝藏》Der Nibelungenhort的念白剧。此外,德国诗人及剧作家赫伯尔(Friedrich Hebbel)也以《尼贝龙之歌》为形,在一八六二年完成了《尼贝龙三部曲》Die Nibelungen Trilogie,包含《长角的齐格飞》Der Gehornte Siegfried、《齐格飞之死》Siegfrieds Tod及《克里姆希德的复仇》Kriemhilds Rache;其将历史概念与神话传说并置在同一轴线上来勾勒这三部文学作品,转化描绘了异教与基督教的纷扰和冲突。
革命性的《指环》
时代的潮流与华格纳的创作相互驱动著,在接触了戈德林(Carl Wilhelm Göttling)的《尼贝龙与吉勃林》Nibelungen und Gibelinen(1816)及默内(Franz Joseph Mone)的《德国英雄传说的历史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teutschen Heldensage(1836)之后;一八四八年的春夏之际,华格纳也发表了《浮贝龙:传说之世界历史》Die Wibelungen:Weltgeschichte der Sage文集来探讨德国诸民族之形成与关系。随即在同年秋天又撰写了《尼贝龙神话,作为一出戏剧的草拟》Der Nibelungen Mythus, als Entwurf zu einem Drama,这虽仅是乐剧的草本,却已经清楚地揭露了角色轮廓;而华格纳耗时二十六年的《指环》创作狂热,此际更是如火如荼地在他心中炙烈燃烧起来。
一八四九年起,华格纳积极展开歌剧改革的运动,发表《艺术与革命》Die Kunst und die Revolution(1849)、《未来的艺术作品》Das Kunstwerk der Zukunft(1849)及《歌剧与戏剧》Oper und Drama(1851)等书,阐述其欲摆脱贫瘠的传统歌剧思维,建造生气蓬勃的乐剧气象;也期许著社会于革命时期的动荡不安中也能有突破性的变革。因此,《尼贝龙指环》不仅成为华格纳实践乐剧愿景的初试作品,也表现当时破坏性、革新性的反叛情绪,被视为融合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与青年德意志(Junges Deutschland)风格的争议之作,也是醒世之作。
华格纳在《指环》中想表达什么?
从华格纳的《指环》不难看出他对日耳曼神话及文学的深远涉猎,他由多方架构的尼贝龙神话与冰岛英雄文学作品中去插补新的素材,修砌属于他自己的神话;而当中对于热烈的、温厚的、晦涩的、戏谑的情感表现,华格纳施展著更为丰沛的戏剧张力。《指环》四部曲的程序安排虽导出齐格飞惨烈的一生,但更可窥见神话中诸神由神殿完竣到面对毁灭的过程,意图指出权力由生至灭所难以摆脱的循环,以及指环魔力虽可载舟、亦能覆舟的觉醒。
此外,后世研究指出,华格纳在《指环》中塑造了三位要角,即佛旦、齐格飞与佛旦之女布伦希德。关于佛旦,华格纳曾描述他就像人类汲汲营营要达到的目标一样,代表著高峰;齐格飞则是一个拥有未来性的角色,他并不属于我们,而是必须透过现世的毁灭而得到重生。对于布伦希德,华格纳认为她有著与众不同的气质,代表著苦痛,是一位自我牺牲的救赎者,也是一位永恒的女性。
死亡、意志、破除封建的构件
华格纳曾表示试图借由《指环》来传递关于毁灭、学习死亡、意志与变更成规的革新性思维;这是受到一八五四年拜读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之著作《意志与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1818)的影响,启发他对于人生哲学的另向思考。华格纳写道:「我们都必须学习死亡,亦即在充斥纯粹感官的俗世中死去,恐惧面对终止是寡爱之源,那私爱已枯萎……怎么为终止而背离恐惧?我的诗会指出方向。」
对于意志,他则表示以诸神领袖佛旦(Wotan)面对极致的悲剧性下场,看清自我毁灭而彻悟的无畏精神来作为代表。而《指环》对于变更成规的投射,则聚焦在佛旦与佛丽卡(Fricka)这对夫妻身上。华格纳认为人性缺少易变性,佛旦与佛丽卡的结合造成两者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两人虚无的爱情成为对于不朽与永恒的误解;剧中佛旦风流成性的行为对其妻造成伤害,华格纳描写出这对怨偶因为道德的桎梏而相互紧锁,怨怼只是徒增苦闷,恰好也表达出他本身对爱情解放的自由观。
跨越 vs.制约
《指环》在创作当时最受到争议与关切的部分是道德的问题。虽强调道德的节制、高尚的情操,但《指环》中强烈浓稠的情感、忌妒复仇的心智和夺取掌控的渴想,皆在在冲击著世俗的普世价值。
表现最为鲜明的应属佛旦了吧!在剧中他被华格纳设定为悲剧性的角色:《女武神》的第二幕描述佛旦以他的长矛毁坏其子齐格蒙(Siegmund)的剑,使得齐格蒙遭到浑丁(Hunding)的杀害,等于宣判佛旦间接残杀他的亲生骨肉,无不引起一阵挞伐之声;佛旦所拥有的崇高地位与其所作所为形成了矛盾的对峙,这等于种下诸神走向灭亡的第一颗种子。此外,佛旦与崴崧族人(Wälsung)所生的齐格蒙与齐格琳德(Sieglinde)这对孪生兄妹的遭遇虽令人同情,但两人的结合悖离伦理,同样不见容于世;也因为佛旦的不忠,这一波波被诅咒的命运转嫁到他的子女身上,甚至是他的孙子齐格飞也因而受祸。这一串连锁效应导致诸神之首的佛旦也无力抵抗,象征著神并非全能的窘境。
华格纳指称布伦希德在《指环》中扮演一位救赎者的形容相当贴切!布伦希德虽为坚悍的女武神,但自始至终她皆保有感性的心灵,和佛旦的威权与齐格飞的勇武有著强烈的对比,也为全然的阳刚气息注入一瓢暖流。她在剧中一开始的角色是护卫神殿的女武神;担任听从其父掌控的一枚棋子;却为了保护齐格蒙而背叛父亲的指令,下贬为凡人,也因此得以与齐格飞共同体验爱情。《诸神黄昏》最终景,她壮烈地带著指环迈向火堆,与已死的齐格飞共赴黄泉,也使得各方争夺的指环重回莱茵少女之手。在此,燃烧他俩的熊熊火焰好似宣扬真爱的永存,也表示权力拉扯的终结;布伦希德所扮演的几乎超越了救赎者的性质,相对的,是抵抗佛旦跨越道德藩篱所给予的约制。
谁给的迷咒?
历时二十六年的构思,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三日在拜鲁特音乐节(Bayreuth Festival)上演的《尼贝龙指环》带给艺术界与社会新的冲击和启发;当然,启发的不仅只有艺文上的灵感震荡,还包括世人都挣脱不了的心灵迷咒——爱与权力!看来,《指环》就像是个世纪大预言一般,一百三十年来,众人皆在里面浮游;何时能上岸?又不知是多少个一百三十年的岁月吧!而这到底是不是华格纳所设下的陷阱?恐怕是始终解不开的谜题、终未完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