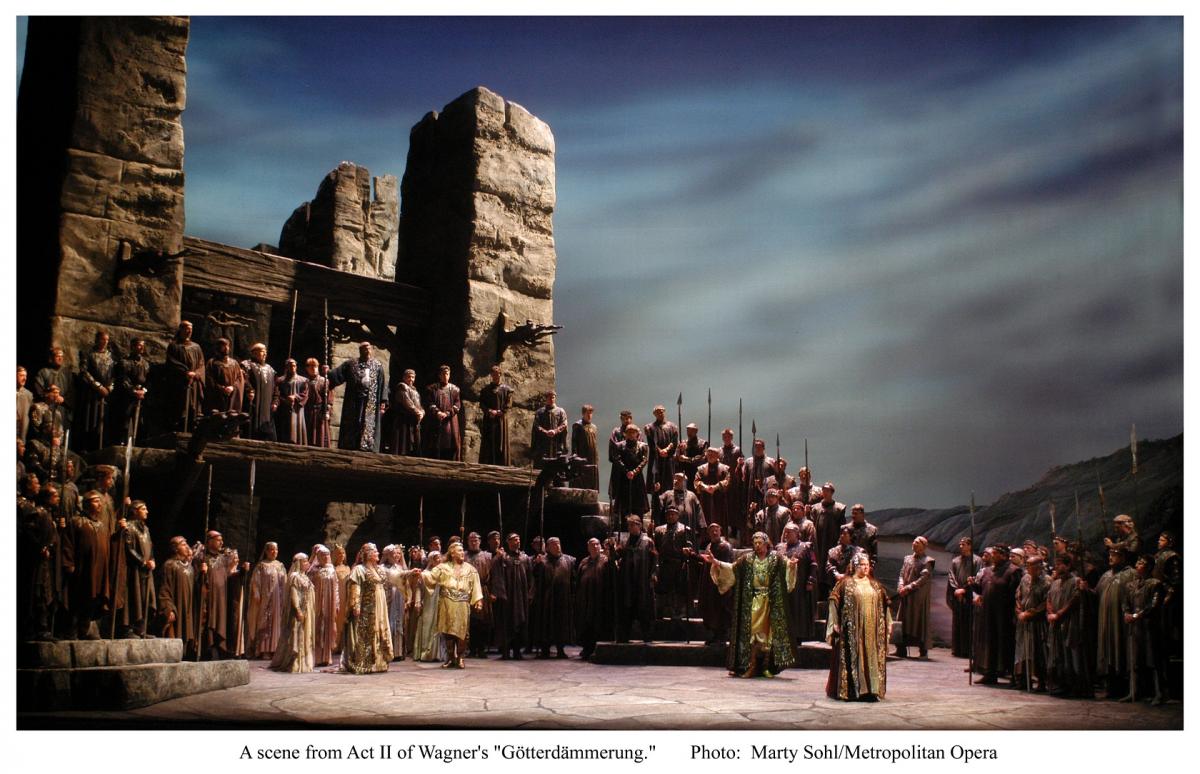华格纳从来都是一位让人难以面对的作曲家,集伟大与卑劣的极致于一身。他的反犹言论,加上二十世纪纳粹对华格纳作品的推崇,以及对华格纳后人的拉拢,使得华格纳成为表达谴责纳粹立场的现成物(ready-made)。但是出人意外的是,照巴伦波英的观察,华格纳的歌剧中压根没有一个角色是犹太人,也就是说,华格纳并没有藉著歌剧来诋毁犹太人。
那么,华格纳与反犹之间的等号是怎么来的?
萨伊德:你不请他吃顿饭吗?
巴伦波英:华格纳吗?如果是为了研究,说不定我会请他吃饭,但不会是为了享受。
萨伊德:那用玻璃墙把你们两个隔开。
── 1995年 10月 7日于纽约
这段话出自两人长达七年的对话所整理成的《并行与矛盾》一书。一个是《东方主义》一书闻名于世的文化研究学者,一个是以钢琴家、指挥家活跃于乐坛的音乐大师。更往里头看,萨伊德(Edward Said)是巴勒斯坦人,而巴伦波英(Daniel Barenboim)是持以色列护照的犹太人。这两个族群的人成天以炸弹、报复式攻击你来我往,彼此的仇恨更加纠缠,公义与不义的分别也越来越泯没。
萨、巴两人期盼以宽容和谅解来消弭仇恨的愿望,恐怕难有达成的一日。耐人寻味的是巴伦波英对华格纳的态度。巴伦波英曾在萨伊德安排下,成为最早在巴勒斯坦演出的犹太音乐家,而巴伦波英也敢冒以色列不能公开演奏华格纳作品的禁忌,不仅推动、鼓吹,还付诸实行,在二○○一年七月七日率国立柏林歌剧院在耶路撒冷演出,曲目排定华格纳《女武神》的第一幕,但是以色列音乐节总监要求更换曲目,最后巴伦波英以华格纳《崔斯坦与伊索德》的片段,作为安可曲。当场有听众离席,事后以色列媒体更是围剿巴伦波英达数月之久。
华格纳与反犹之间的等号是怎么来的?
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一个在一八八三年去世的作曲家,到了廿一世纪仍然是禁忌?为什么又有一位犹太指挥家不怕被同胞戴上背叛的帽子去触犯禁忌,而且他还在拜鲁特音乐节指挥《指环》全集,又担任柏林歌剧院总监(至今还有许多犹太人不愿踏上柏林),大力搬演华格纳的歌剧,但同时,面对一个纯粹假设性的问题:有机会跟大他一百二十九岁的华格纳吃一顿饭,巴伦波英却是避之唯恐不及?
华格纳从来都是一位让人难以面对的作曲家,集伟大与卑劣的极致于一身。他的反犹言论,加上二十世纪纳粹对华格纳作品的推崇,以及对华格纳后人的拉拢,使得华格纳成为表达谴责纳粹立场的现成物(ready-made)。但是出人意外的是,照巴伦波英的观察,华格纳的歌剧中压根没有一个角色是犹太人,或许某个角色(像是《齐格飞》里的迷魅和《纽伦堡名歌手 》里的贝克梅瑟)让人想到犹太人,但是本身并不是犹太人,也就是说,华格纳并没有藉著歌剧来诋毁犹太人。
那么,华格纳与反犹之间的等号是怎么来的?主要就是华格纳写了一篇〈音乐中的犹太成分Das Judentum in der Musik〉,并且在一八五○年的《新音乐杂志》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发表。华格纳在文中直言,「我们毋需证明,现代艺术已经让犹太人给占了,」他接下来的叙述简直和现在讨论全球化「工作外包」、降低成本的著作如出一辙,第一世界的工作机会被开发中国家抢去,而对华格纳的笔下,不管戏剧、音乐、文学,读者读到的都是「沦陷」, 都是工作机会被犹太人抢走。
在华格纳看来,这不仅是工作机会流动与成本降低的问题,而是当艺术落入像犹太人这样两千年来流离失所的民族之手时,在犹太人心中根深柢固的一种漠然、以一种轻浮又小心迎合的心态来与世界周旋,同时又带著嘲讽与压抑扭曲的意识,其结果就是造成艺术的堕落。欧洲音乐天才的血脉到贝多芬为止,之后就断了香火。孟德尔颂的音乐轻盈精巧、技法纯熟,但是华格纳却贬为「甚至失去了形式感」,流于充满奇想、飘忽轻浮的形式,「看似色彩斑斓,激发了想像力,实则完全碰触不到人类内在的情感,更遑论满足情感了。」
一篇文章,与半世纪后的纳粹搭上轨
华格纳以如此猛烈的力道攻击犹太人,或许有际遇上的偶然。华格纳在一八四八年加入「祖国联合会」,这一年马克思发表了「共产主义宣言」,表达了对于社会改革的殷切盼望,以及对于现有体制改革的质疑。而在日耳曼各地,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往往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终极答案,甚至不排除以革命手段推翻各地现有的政府,铲除通往一统日耳曼的障碍。刻意将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与民族主义合流,成为十九世纪中叶之后欧洲各地,乃至亚洲国家不断上演的革命剧码。而华格纳实际参与暴力政治活动的结果,就是他遭到通缉,无处容身之下,得到李斯特的建议前往巴黎。
当时的巴黎正是「大歌剧」当道的年代。巴黎歌剧院在一八三○年代完成,主其事的维农决定放手一赌,精挑具戏剧张力的脚本,重金礼聘名角、力求场面浩大、舞台华丽,只是作曲家难觅。那时罗西尼(Gioacchino Rossini)已经金盆洗手,但几位可能的人选又无法效力,于是大胆启用时年四十的麦亚白尔(Giacomo Meyerbeer),结果以《魔鬼罗伯特》Robert le Diable大为成功。
华格纳所到的巴黎,正是麦亚白尔当红之时。巴黎歌剧院开销惊人,全要以票房来支撑,逢迎大众口味的程度可想而知,也难怪华格纳的作品不受欢迎,麦亚白尔同时推出的《先知》又是满堂彩,两相比较下实在难堪,华格纳只得无功返回瑞士。但是华格纳把这笔帐记在麦亚白尔的头上,碰巧他是个犹太人,而孟德尔颂不用说,也是犹太人。华格纳在〈犹太成分〉一文中,提了好几次孟德尔颂,但主要是从专业上来批评他,麦亚白尔的名字只字不提。但是华格纳在写给李斯特的信中,说这篇文章主要是冲著麦亚白尔来的,或许跟华格纳自己在巴黎的不愉快经验有关。只是华格纳疑似反应过度的结果,却是跟半个多世纪之后的纳粹接了轨,恐怕华格纳当初是没想到的。
当时的杂志编辑也没想到。他只是觉得华格纳的文字让他不安,所以以编按说明:「日耳曼傲人之处之一,就是拥有智识的自由,至少在科学的领域是如此。我们以此自由为准绳,付印此文,希望读者明察。不论同不同意文章观点,但作者的广博是无法否认的。」奉科学与思想自由之名,打开门之后,才发现这条路通往极权、奴役与杀戮。
或许犹太人的问题只是这时华格纳心中一个次要的插曲,一经发泄,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华格纳在这时候所思考的主要是自己在艺术上的主张:一八四九年发表了〈艺术与革命〉、〈未来的艺术作品〉,一八五一年写了《歌剧与戏剧》,在文中说明了「主导动机」的概念,以及它在结构上的重要性。也是在一八五○年前后,华格纳决定创作《指环》──从创作构想在一八四八年成形,到一八五二年完成剧本。
时空牵制,反犹恶名难以洗刷
只是或许华格纳在成就自己的艺术主张、铸炼自己的创世神话时,另一股对现状不满的反作用力在种种时空的偶然必然因素下,指向了犹太人。不幸的是,犹太人在二次大战所受的屠戮,让华格纳即使再世,上了纽伦堡的法庭也难以为自己辩护。犹太人在文学、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美国电影、经济、政治的地位,都使得犹太人在德国的遭遇受到过度的关注 (别的大屠杀不讲,俄国也在二十世纪屠杀犹太人,数量也很庞大,但关注此事的人却少了许多),华格纳的恶名也更难洗刷。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犹太人在二次大战的遭遇,欧美国家未必支持以色列建国。而这么一来,以色列与大多数曾在历史上迫害犹太人的西欧族群都已经和解,反倒是和两千年来搆不著边的阿拉伯人成了不共戴天之仇,并成为影响,譬如说,巴伦波英和萨伊德这两人生命方向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这种深切的悲剧感,或许只能从希腊戏剧和华格纳的《指环》中,寻得一点解释与慰藉。
文字|吴家恒 爱丁堡大学音乐硕士、音乐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