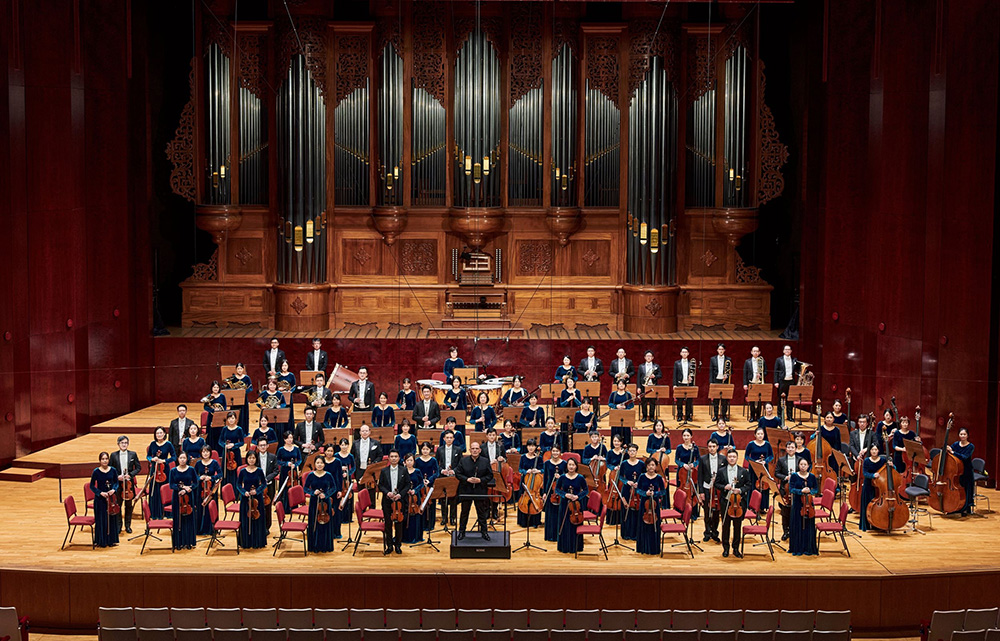一九四三年演出的《阉鸡》与《高砂馆》,在结构与戏剧精神上,展现了现代戏剧的特色,而这些特色,我们也可以在西方十九世纪末进入现代戏剧阶段的剧作如《樱桃园》中发现——例如以日常琐碎的对话去开显人物自身潜意识的深层动机与隐藏情感,以及把「现代化」的问题置入成为情节的关键……。
林抟秋改编自张文环的《阉鸡》与独立创作的《高砂馆》,于一九四三年首演时是同步推出,只是场次错开。不但是时间上的巧合,在结构与戏剧精神上,《阉鸡》与《高砂馆》,也呈现了相同的现代戏剧特色,这种特色,不止是表面的日常生活对话与写实的场景,背后还有现代戏剧所具有的现代精神。当西方于十九世纪末进入现代戏剧的历史开端时,我们可以在当年的许多剧作中,发现类似的精神。
角色对话呈显现代戏剧精神
什么是现代戏剧的精神?以《荒谬剧场》一书扬名世界剧坛的学者马丁.艾思林(Martin Esslin),认为:「传统的戏剧惯例(这种惯例自剧作产生以来一直存在),不仅是给每个人贴上『恶棍』或者『英雄』的标签,而且常常通过独白旁白对心腹知己坦白等方式,告诉观众人物最主要的私密动机。观众习惯于这种戏剧惯例几世纪之久。直到写实主义——后期易卜生戏剧是典型代表——关闭了人物的内心窗户(指独白、旁白等)之后,观众才不得不自己动脑去弄清楚人物行为背后隐藏的动机可能是什么……现代戏剧对话的规则,与古典对话的规则是直接相反的。现代戏剧的艺术性,就在于通过最琐碎的日常谈话的裂隙,去开显人物自身潜意识的深层动机与隐藏情感。」
例如,我们在《阉鸡》与的《高砂馆》的最后,也看到类似的日常对话间隙,让我们对角色的动机与内在心理状态,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在《阉鸡》的结尾,阿勇只是听到农夫唱〈六月田水〉,就忽然生出奋斗的勇气。我们不知道这首歌对他的意义为何?阿勇到底经历什么心理转折?这些问题,都成为观众的功课。同样地,在《高砂馆》里,这种现代精神,变得更加明显。那名广东回来的女客是谁?为何在被男客抛弃后,还要住在高砂馆?我们完全不了解。但我们看到她在舞台上出现,听到她的对话,我们完全知道她是谁。只是角色的存在,不再依附于情节了。
在《高砂馆》的结尾,也出现了类似《阉鸡》的莫名逆转,令我们迷惑不已。从华北回来的木村,向等待未婚夫国敏归来未果的阿秀,提出:「长久以来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不如就让我们…(下定决心,坚决地)一起照顾二老吧。」我们只见到阿秀走到窗边,望著窗外海面,没有提出任何否定,最后是舞台指示写著「两人无视阿富的喊声,凝视著华北的上空」。这种充满希望的开放式结尾,非常富有诗意,令人感动,却无法阻挡我们的疑虑。几年来毫不动摇的阿秀,刚刚还在说忘不掉过去的阿秀,怎么就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是什么东西改变了她?这都不免让台下观众狐疑。当然,在这个转变发生之前,阿秀与《阉鸡》里的阿勇一样,也是沉默了一阵子之后(然后她说一句:「船要过防波堤了」),才做出有别于之前的表现。
角色有了独立生命,对话不再只是推动情节的工具,这不就是西方现代戏剧所走过的道路吗?推到极端,就如同贝克特荒谬剧(甚至是品特)中的景况,角色间各说各话,不要说剧情,连内在主体性也不能透过对话得知。不论是阿勇或是阿秀,他们都是作为具有现代戏剧精神的人物,首度出现在台湾戏剧史的舞台上。
面对现代化的历史课题
从更大的历史范畴来看,《阉鸡》与《高砂馆》也面对了现代性(Modernity)的问题。在契诃夫的《樱桃园》中,铁路的延伸所代表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改变了农庄生活与阶级关系,旧有价值与回忆不再有任何意义,樱桃园终究要被砍掉。铁路不是可有可无的话题,打从《海鸥》开始,就善于将舞台布景转为戏剧象征的契诃夫来说,将通往车站路上的电线杆摆在舞台上(第二幕),正是要与看不见的樱桃园相对。契诃夫作为伟大的艺术家,不只是因为他优美的散文对话,也在于他敏感到即将在未来发生的大变动——这个扑天盖地的红色现代化,会彻底地砍掉俄罗斯文化的怀旧樱桃园。
在《阉鸡》当中,现代化(也是盖车站)不只是单纯的故事背景,更是造成情节逆转的关键(现代化作为阉割的象征,在张文环的小说原著中更为明显)。在《高砂馆》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已经不再被土地所束缚,连木村的父亲吴源,也赞同儿子打算再度前往满州国发展的构想。这就代表著现代性终将切断了人与自然的脐带。如此说来,原本在《阉鸡》里,人与土地还若即若离,到了《高砂馆》,自由而孤独的现代人,已经浮现。
令我们惊讶的是,作为现代化隐喻的电力,在现实的《阉鸡》演出中,以一种充满精神分析式的意外出现。演出因为停电而中断,靠的是民众自己带的手电筒,才让这出新剧的代表作,得以演完。这也恰好象征了台湾现代戏剧的命运:外在的政治干扰,让台湾的剧场艺术老是遭到阉割,无法成为敏感未来趋势的社会预警器,只能靠民众的热情,在忽暗忽明的纷乱时代,留下一线生机。至于新剧之后的台湾戏剧,如何接下人际对话的棒子,在形式与内容上反映社会变迁,这条现代戏剧的发展道路,还没有真的好好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