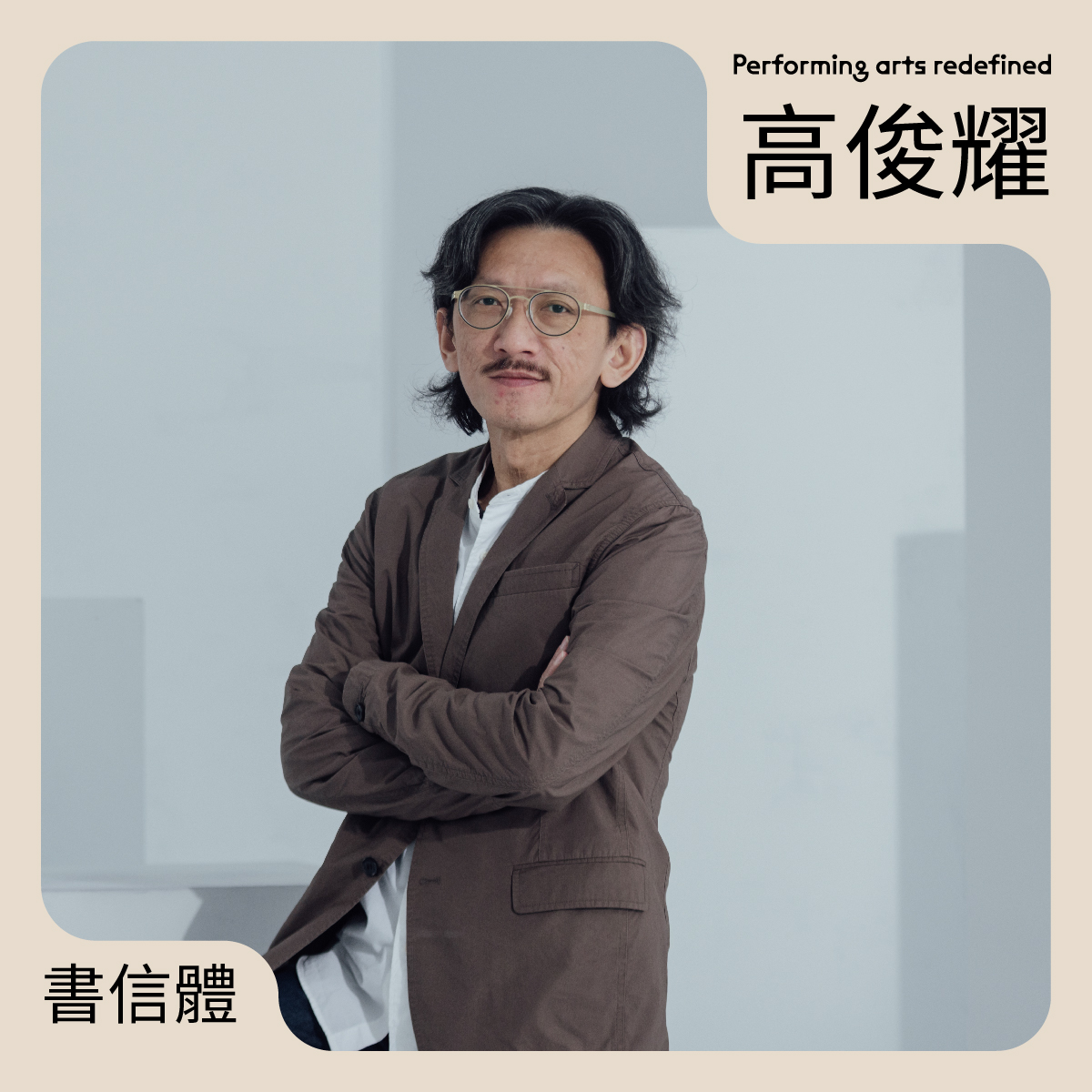YC,
年前回老家双溪大年,老妈和大姐因年后要搬去吉隆坡居住,大扫除之际,该丢的丢、要留的留、能送的送,辛劳地奔波著、困难地抉择著。2004年8月我出国留学时,就留了一大批书籍、物件和资料在姐姐家,想说过年过节回来时就清理,结果一搁就10来年,每次都跟自己说,再等一年吧,如果真的没有再使用,就会放掉,如此自我说服了这些年。现在终于无法回避长年堆积的旧物,要把眼下10来箱整理成两箱带走。于是第一步要把舍不得的书籍送走,恰好刚认识了一位在当地经营二手书的朋友,心想也太巧,偏偏在这时刻,就意味著书找到了主人,我得聆听书的决定。再来就是一些工作资料,抉择的方式简单而蛮横,捧在手上,有画面的就保留,想不起的就丢弃,然后默默提醒自己,不喜不悲不嗔不怨,乍看以为在修行。最后就是一大堆剪报,最久远的至少20余年,油墨味沾黏在尘埃中,有些纸质几近脆化,新闻或已不新,事件未必就此过去。该怎么办呢?我打了几个喷嚏,偷偷捡拾了一些放进箱子,其余的,一并回收。扪心了然,回收的,不只是旧物。
几个小时后,心里郁闷得很,就往家附近走走。不远处传来咚咚镗镗的锣鼓声响,寻声而至,来在关帝爷庙口前,果然有潮州戏在上演。还记得我跟你提过吗?小时候,电视还不普及,潮州戏就是民间最要紧的娱乐。每逢节庆,黄昏5点就有许多人搬著凳子来占位,凳子一摆下,你就可以离开忙别的事,等7点开演再回来。大家颇有默契,都懂看戏伦理,你的凳子放著,没有人会去挪动。那时候我就是负责帮婆婆和妈妈搬凳子的小家伙。7点开演前人潮就聚集了,许多流动摊贩也忙著招呼人客,炒粿条、云吞面、叻沙、红豆冰、煎蕊、冰淇淋等,小小的我心底一乐,天底下有什么比边看边吃、边吃边看,更逍遥的事?!
潮州戏,又称潮剧,是用潮州方言载歌载舞的地方戏曲,流行于广东、福建一带。早期华人移民到马来西亚时,通常会根据原籍地或自身方言来群聚或结社,甚至决定了所从事的行业。过去有「华社三宝」之称,指的是中文教育、华文报章和华人社团。后者,就是按照地缘籍贯成立的会馆,通常会运用庙宇、祠堂等公共空间来举办活动,联系乡情也同时凝聚族群认同。我爸妈小小年纪就从广东潮阳过来,一别就是五六十载。潮州戏敲锣打鼓,口音荟萃了一个群体的精神样貌,相信也慰藉了台下不少看倌们的心情。
话说回来,我来到庙口前,只见戏台前方停了好几辆车,有几只野狗在觅食,就我一个观众望著台上演员唱念做打。几个跑龙套的演得很马虎,眼睛半睁不开,比手画脚,完全不甩乐师的拍子。小生和旦角疏离地对戏,酷似闷热的气候,懒洋洋地演出著。或许是我看得十分专注,突然,小生一眼瞥见了我,眼神一扬,「咦,有人看戏?」兴许是职业道德所致,他动作顷刻俐落爽净,和他对戏的旦角见状,也不敢唬弄,精神一提,嗓子拔地嘹亮,乐师们乐了,跟著起劲,音乐生猛起来,只剩下几个跑龙套的,左顾右盼,在想发生了什么事。
有几个小孩搬了凳子过来,野狗识趣地让了道,好几个老人家携伴走来,坐下,人群开始聚集。车主匆忙赶来,一边跟大家说抱歉,一边小心翼翼地把车开走,让出了更大的空间。我索性爬到台口右侧平台处,隔著乐师们的板子,就近观看。啊!小时候自己不也这样,好几个小朋友因为个子矮小,坐在台下被人头遮挡,看不到戏,就毫无顾忌地爬到台口两侧,仿佛是为自己而设的贵宾席,直到管事的庙祝瞅见,拿了把鸡毛撢子来赶人。印象中,我也被弹了几下。有几个流动摊贩推了摊子过来,叫嚷著,场面一时喧哗起来,吃的喝的看的乐的,这下轮到我有些惊呆,仿佛儿时戏班荣景霎时重现。
一个跑龙套的顺著走圆场靠了过来,「喂,这里不能坐人,下去。」我不甘愿地跳了下来,惊扰了一旁歇凉的野狗,一瞧,人群早已散去,空寂的平地就自己一人。我回头看,台上兀自演得热络,大伙儿纷纷飙戏。我无法就此转身,便继续站著看戏,戏需要观众,观众也渴望著戏。小生炽热的目光扫视过来,嘴角微扬,「啊,你还在!」……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