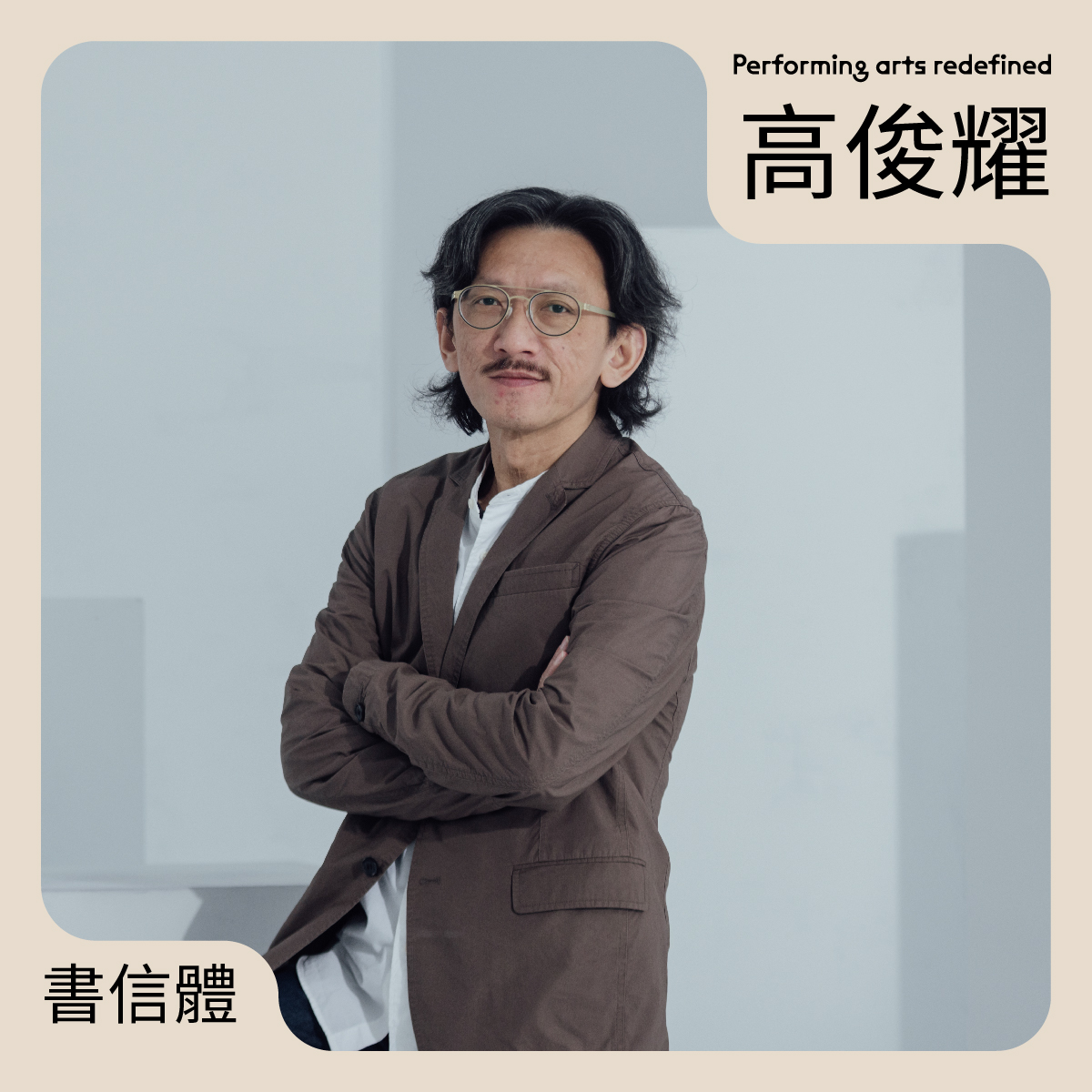YC,
「重要的是变成了玻璃,再敲敲变成了铜,再敲变成了水——这样的语言质地的变化。」诗人顾城是这么形容他写诗的过程,在字与字之间无尽的排列组合,他会先把声音放在这个地方,试试看,然后再换另一个地方,仿佛字松开了身体的关节,咯咯作响,「O点 的鬼 走路非常小心 它害怕摔跟头 变成 了人」;「不死 不活 不疯 不傻 刚刚下过的雨 被他装到碗里一看 就知道是眨过的眼睛」;以前读他的诗是不求甚解的喜欢,从音声发出,回头辨识字的形状,再咀嚼意义的灵动。顾城喜欢把事情说得神秘迂回,朦朦胧胧,意有所指,却又萌生歧异。这对年少的自己就是说不出的魅惑。再后来,重读唐诗,才明白他用白话文转化了古诗词的韵律,所以他的诗可以朗读。美学鉴赏家顾随先生说:「诗原是入乐的,后世诗离音乐而独立,故音乐性便减少了,词亦然。现代的白话诗完全离开了音乐,故少音乐美。」诗的美与音节字句有关,夕阳冉冉、杨柳依依,音节带来印象的感受和情感,顾城很聪明,换了个作法说法,骨子里仍是古典的薰陶。再更后来,重读顾城的诗,总觉得美是美,却不肯落地,少了世间烟火。
创作之前,我们首先是读者。写作之前是阅读和聆听。过去这些如此如此,后来形塑成写作习性,非读个几遍,字句听得舒服,才能落实。若是写剧本,就更过瘾,一人分饰多角,自己在爬格子里头演绎爱恨情仇,不亦乐乎。
2015年,我参与大墨(编按:王墨林)导演《长夜漫漫路迢迢》的台北重演版本,担任副导演。这出戏在2013年澳门艺术节首演,顺应当地演员演出,语言全改为粤语。2014年牯岭街小剧场「为你朗读II」邀我来当此剧的读剧导演,那时候发现,大墨导演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英文原著改写成中文,再由澳门演员以粤语个别转译,语调风格上出现了不统一,各有各的诠释和理解,导致彼此对话时,语境无法汇聚成整体的想像。
于是在澳门排练的第一阶段,就和全体演员围坐,按字逐句去寻找华语和粤语之间的音韵声腔使用,如何调和文读和白话的比例,然后在两者叠合中创造别具一格的节奏氛围,比如某一字词放在文中语境有什么意思,和文本内在情境的呼应,以及念起来在听觉是什么感受等。大墨导演希望剧本语言能接近口语但不那么白话,要找到某种语言的气质,要有诗的意味。
印象中这个推敲选字的阶段至少用了3个时段来工作,过程很好玩,我们在反复念读中确认文字的理解,原本的卡司与新加入的演员从各自经验分享对语言的看法。比如在角色称谓上,首演版出现了「爸爸妈妈、阿爸阿妈、老豆老母、老嘢」等各自在生活的使用习惯。为了语言调性的流动,我们拿掉了「老豆老母、老嘢」等等几个日常习惯的叫法,然后在不同语境下选择不同称呼,把「阿爸阿妈」放在他们日常对话当中,「爸爸妈妈」则有某种文字书写的距离感,在亲暱叫唤中带有陌生的裂隙,仿佛身处并行的两道现实,一个是现场,一个在意识中。儿子与父亲争执过后,走到麦克风面前说:「爸爸,呢段时间我都过得好快乐。」一个称谓的调动,就把心里的位置往下压了一压。
参与语言修订有当时在习修广东曲艺地水南音的何志峰和梁建婷。有此一说,南音的精妙不在曲词,而在声音结构。「词语如海,欲渡意境的彼岸仍要靠『声音』这个『舟』。」粤剧曲艺研究者沈秉和如是说。我们在用词的调整,仿佛顾城在字句的敲打过程。「感谢主,啲雾终于都散咗啦。但我今朝反而周身唔『聚财』,𠮶啲咁嘅雾笛呢,成晚喺个海度不停咁『叫』,搞到我冇觉好瞓。」粤语「周身唔聚财」是形容精神不振,我们从音韵出发,提炼出言语的物质性,决定将「聚财」换成「自在」,「叫」换成「响」。于是句子就改成:「感谢主,啲雾终于都散咗啦。但我今朝反而周身唔『自在』,𠮶啲咁嘅雾笛呢,成晚喺个海度不停咁『响』,搞到我冇觉好瞓。」至于说书人的台词:「雾来了,黑夜就接踵而来,他们用艰难的步履,走向生命最后一段旅程。」虽然不尽符合粤语文法,我们以朗读方式带出文字异质性的韵味,让听觉有字外之意的感受。
回想这段经历,仿佛也叠合著更早之前在《忿怒》和《死亡纪事》里,华粤声腔的思考,体会更深,从言语的物质性提炼,到身体性的调度,在字句跌宕、抗衡中,让音韵穿透文本辞意,感受声音其实就是身体,不免更深刻理解,古典底蕴的打磨,念兹在兹。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