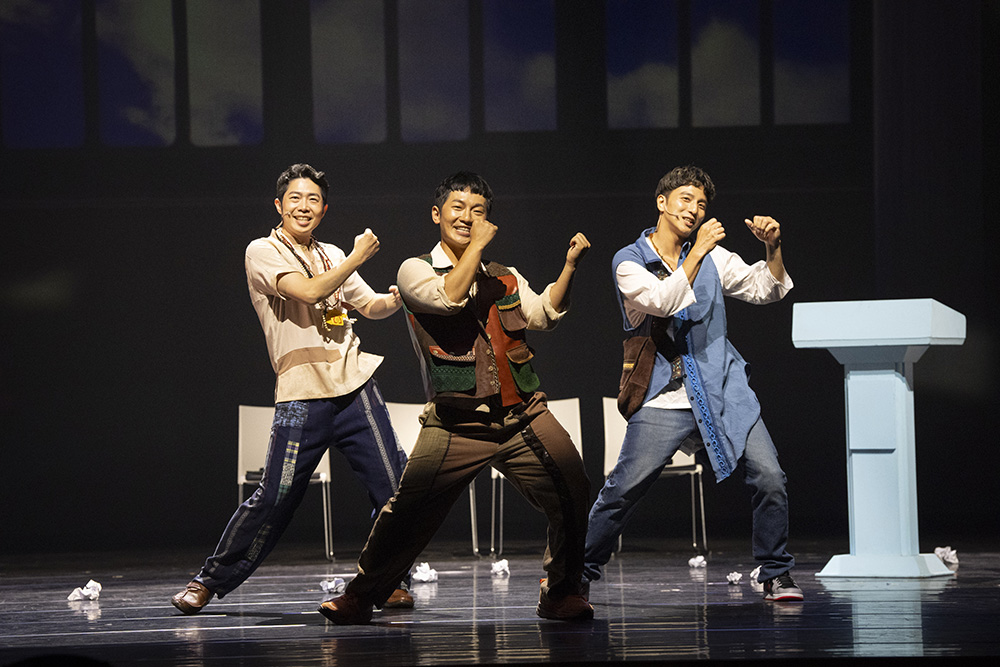無論中西方,回溯表演藝術發展歷史,多能與宗教祭儀、民間信仰或是官方娛樂有關,而後來演變至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其所產生的商業需求,小從個人的消遣,大至生、老、病、死,幾乎都與它有連結。而「缺少了觀眾就不能成為完整的演出」的特性,也讓表演藝術緊貼著社會脈動,關注民意潮流與趨向,甚至能為社會帶來顛覆性的改變。故自古早時代表演藝術也擔起教育之責,從教忠教孝到政策宣導,也透過民間戲曲、歌謠等方式,傳唱大街小巷,在潛移默化中帶來整體性的改變。但經歲月流轉,時至當代,現今台灣的表演藝術,對於這方水土的人們而言,又是個什麼樣的存在?「需要」又是如何產生?
台灣表演藝術體質
台灣的劇場環境,並不是以票房與私人贊助達成自立更生的生態,大多數的表演藝術團體,仍需要依靠公部門的獎補助資源維生。現行官方的表演藝術經營概念,同步取材歐洲與美國體系部分特色,融合而成:效法歐系設立國家劇院、贊助藝文團體,但於此同時卻未有培養與劇院共生的國家劇團或舞團;場館藝術行政配置也不走邀請創作者擔任藝術總監的模式,能夠在一定期間內焦點投資特定藝術家與團隊,以其美學領軍,進駐場館共同推出作品。台灣場館首長的人選考量上多以行政經營層面為出發,仿效美國劇院自營方式,期待市場與喜愛藝術的民間資金投入。而若藝術家有機會獲邀擔任公部門轄下場館重要職位,在上任前甚至需要向公單位保證,自己的團隊不會因此獲利或自肥,許多條款也依防弊原則而生。我們能觀察到,目前台灣表演藝術領域在思考藝術場館的公眾性時,盡量保持多樣性與公平,優先於美學與藝術價值的深化。
在台灣商業劇場仍尚未成為主流的現在,當一個創作者或表演團體希望能被大眾看見,不免需要尋找公部門與私人企業的獎補助資源協助,現行台灣大環境裡針對表演藝術的獎補助,以公部門與其底下場館的計畫案為大宗,每年皆是各大表團的兵家必爭之地。雖然也有立志不依靠補助扶持的表演團體,但在大部分場館或多或少受到公單位資源挹注的狀況下,只要進入大型劇院、文化中心或地方館所,使用到公部門資源的情況仍是難以避免。
創作者選擇以藝術作為與世界溝通的橋梁,大多是有外於主流旋律的意念希望透過創作傳達,而在必須將獎補助與場館偏好列為創作考量的大環境下,藝術家享有的創作自由夠充分嗎?而反向提問,擔任資源提供與分配者的公部門,又期待著表演藝術團體與從業者,在現代的社會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生存,或是要轉行,這是許多表演藝術創作者面對環境的大哉問。
公部門資源分配下的生態
目前官方獎補助主要來源為文化部,從表演藝術聯盟2024年8月份整理公布的「民國102年至112年文化部表演藝術相關計畫預算統計圖」(附圖)中,可以明顯觀察到表演藝術總預算在這10年來大幅提升,但在第一線表演藝術行政人員大多對此無感,這樣的情況與預算分配方式密切相關。
表演藝術聯盟將文化部與其轄下機構的補助計畫分做3大類討論:第1類為協助已有規模與穩定輸出作品的表演團體基本營運、場館的業務維持,以及保存傳統藝術所需要的「固本保底」類補助;第2類是帶有引導公共性施政計畫目標、可提供跨藝文類別申請的「生態調整」類,像是近年熱門的推動多元語言計畫,或針對特定主題規劃的創作補助案,都在此範疇;第3類則為關注市場開發、科技應用與文創等計畫的「策略投資」類。以此分類區隔,10年中的預算分配裡,對於表演藝術團體最有幫助的「固本保底」類漲幅並不大,加上疫情後通膨狀況,使得許多團體不得不往其他計畫案開源;而預算增幅最多的「生態調整」類,也正影響著藝術家們取材與創作的思考。
許多創作者與表演團體為了獲得創作資源,努力在自我創作脈絡之外,為了補助案而碰觸新的題材,正向來說雖然有機會迸發新的火花,但對於其本身想討論的議題往往無法深化。而對於計畫案的指定題目作答,目前達成的成果也不盡令人滿意。例如有些團體耗費大量心力投入科技跨域領域,啟動後才發現所需的人力與費用遠高乎預期,不得不為了執行計畫而耽擱了團體該有的創作量能,這樣的生態是否有助於表演藝術的發展?或是讓表演成為了另一種技術產業?

場館間的策展競賽
台灣劇場環境在2018年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正式啟動後,正式邁入了「大劇院時代」,加上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等地方場館陸續到位,館際之間為了建立品牌形象,有意識地展現場館各自特色,期待做出與其他館所的區隔,並在近年導入視覺藝術領域行之有年的的策展概念,設立議題與風格多元化的各式藝術節,以特定主題策展邀演表演團體,或邀請創作者們據此推出新作。
藝術節之外,各場館於表演藝術人才培育、廣發英雄帖徵集主題性╱指定形式創作的題材開發策略下,也逐步形塑自己的資源走向與喜好,而由於戲劇與其他藝術類型不同,在乎當下性與社會共鳴感,因此藝術節與徵件的規劃,很難不貼近當下時代價值觀,或與場館的贊助單位靠近,這也間接影響著這一輩創作者們的關注視角與創作節奏安排。
製作取向 vs. 創作取向
回到創作者與表演團體端討論,在現今自媒體與社群發達的年代,戲劇相關科系已然不再是冷門選擇,學院與坊間相關課程琳瑯滿目,人才輩出且愈分愈細。那麼,在表導演能力與設計水準俱優的今天,劇場工作者投身創作的初衷,已然成為另一項重要的課題。
從1970年代許多表演藝術團隊的紛紛成立,到80年代台灣小劇場運動蓬勃開展,當時的團隊多以創作與美學先行,後才邁入製作。今日當表演創作生態已然足夠往產業化邁進,許多團隊將健全的工作環境與生態視為第一優先,由製作角度思考與規劃劇團或個人的未來創作走向。當一個專業領域走向產業化,這樣的生態變動必然發生,但我們想回問的是,在獎補助總金額升高的今日,創作者如何能夠在賞金獵人的產業遊戲裡,仍保有自我創作意念?在以案養案的過程裡,會不會太過投入而迷失方向?
不可否認,指定命題的創作帶來了許多新的創意與火花,也能有機會誕生優秀的作品。但對於公部門來說,集中資源在生態調整上,對藝術創作的深化是否有幫助?在中介組織的協助下,公家機關補助的「臂距原則」是否有效執行、給予創作者足夠的空間與自由?「表演藝術團隊」、「演藝團隊」、「商業劇場」等看似雷同,但卻又是表演產業生態鏈上不可或缺,本質上卻又截然不同的創作屬性與團隊特性,無論是從業人員本身抑或是主管機關,似乎也到了需要釐清相互關係的時候了。但無論未來公部門的各項計畫或補助會如何回應台灣表演創作生態,其實最終的關鍵,仍是在創作者身上。畢竟,資源是有條件的,創作卻永遠都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