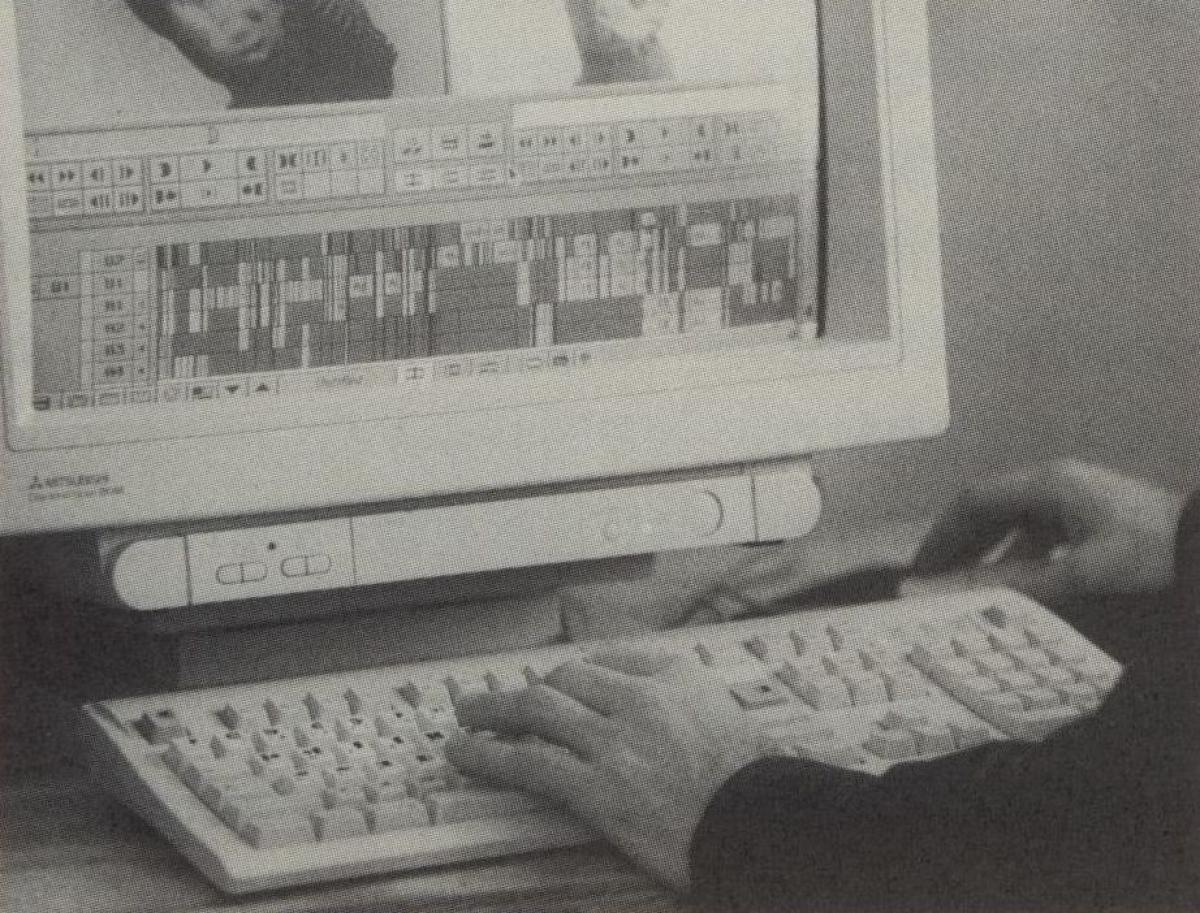录像在舞蹈的应用是一种进步吗?
舞蹈在录像里失去了什么?
一九八二年,在纽约市一个有关舞蹈与录像的硏讨会上,杰夫.邓肯(Jeff Duncan)力促众人抵制录影纪录的恶性侵入。他劝吿我们,千万别允许自己的作品为这种难以掌控的媒介所评断。依他之见,录影纪录不足以呈现舞蹈这种艺术形式。当时,我觉得他的想法太极端了,实在没必要这样。没错,我承认要把舞蹈作品放进录像规格里,确有不少限制存在。既然录像技术能使舞作被更多的遴选单位,如艺术委员(arts councils)、国家艺术资源会(NEA-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经纪公司与经纪人等来鉴赏与评估,我觉得这是无可避免的科技突破,应将其视为某种进步。
抵制录像的恶性入侵
泰半的与会者也多像我一样,觉得杰夫.邓肯的警吿过于偏激,且有守旧之嫌。再说,我们毕竟是所谓「现代」舞蹈的一份子,甚至有时还因为被贴上「前卫」或「后现代」等标签而沾沾自喜,我们又怎能拒绝「进步」呢?
然而,最近的一次经验却使我开始对这种媒介的适当性产生怀疑。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当时我为天普大学校友会的表演评委会担任主席,由于参选的作品来自各地,我们决定凭录影带作决选。
评委会真的看了所有的带子,虽然常常因不耐烦而用快转瞄过。评选结果是,唯一一支专业拍摄的影带获得全体同意而保送入围(即使里面只秀了舞作的零星片段)。至于其他的带子,则没有人显出丝毫的热情。有位评审看过某个影带的现场演出,替它说了几句好话,它就中选了。有两支带子来不及寄到,但编舞家曾向我描述舞作,好让我向评委会说明,结果这两团也上了榜。最后为了凑数,评委会勉强塞了些相当无聊,只因有现场伴奏而略显不同的作品。我觉得,这种无奈的结局与影带的观看不无关系。评审们对能看到影带全貌的作品倒足胃口,却倾心于集体想像的产物。到头来,影带制作的专业程度竟超越舞蹈本身成为评选的标准。
舞蹈的某些隐喩来自它稍纵即逝的短暂存在。比起其他的艺术形式,舞蹈很难产生任何有形产物。为使舞作能如音乐般恒久留存而建构舞谱,这尝试在舞蹈史上一直持续地进行著。广受现代舞坛支持的纪录系统──拉邦舞谱,近来确有被录影科技凌驾的趋势。影片(film)因所费不赀,影响不大,倒是开销较小的录影作业,的确比舞谱纪录及人员重建快得多。
舞蹈学生及专业人员可以从录影纪录,更快、更容易地学习旧作。况且大部分的舞蹈作品都会为了经费申请、资料纪录、舞作保存、宣传推广、评论分析,与演出回应等种种理由作例行录影。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要将动作中活生生的人体转化为录像,其中肯定有许多缺损与不足。
编舞家丧失主导权
不妨就从「尺寸」(size)说起吧!曾有人就此议论,既然观众能接受电视剧里的人物尺寸,为什么换成舞蹈就不行呢?这问题可用电影作例子来回答,当电影放在电视萤幕时,原本气势盛大的群众场面变得很无聊。
舞蹈录像用在单一或少数舞者时效果较佳,反当有越多的个体想挤进这个长方形的空间,人变得更小,观众便觉无趣。这与现场演出的情形恰恰相反,台上的人数愈多观众愈觉震憾。
再者,电视萤幕的矩形尺寸与人体比例不符,即使整个画面仅纳一人,也得裁掉头或脚,而焦点亦仅能在足部的舞动节奏与面部表情间两者取一。至此,细部特写所看到的不再是舞蹈,倒成了录影师的个人表现手法。
舞蹈与动作息息相关,是动作之于身体与其他身体的动作,也是空间中的动作与动作穿流的空间。录像完全不足以捕捉此种现象。在现场演出中,表演者身边未被占据的空间蕴含著可能性,但在录像中,离开萤幕就是不存在。
舞蹈的部分即时性来自于「动能反应」(kinesthetic response),或可说是观众对表演者正从事之身体活动所生出的同感心。假使摄影师选择紧随某一人,以表现其动作,则不管此人往何处舞去,他还是在原处──萤幕的正中央。或者,摄影师可以选择呈现某人从一端舞至另一端的画面,但这将大大削减了此人的重要性,而其中所含足以唤起动能或情感反应的力量将消失殆尽。
另一个空间的层面是「框限布局」(framing),总地来说,这是指编舞家运用界定镜框之后、地板之上的舞台空间,或是布景与舞者位置的安排。框限布局可说是编舞家的构图艺术之一。这些框线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的,只不过是编舞家在创作时的考量罢了,但当舞作转移至录像,它们却被全盘抹煞了。在录像中,录影师担起了框限布局的工作。动作设计或许与原作无异,但却因与框限布局关系的变化使舞蹈产生剧烈改变,且编舞家完全丧失操控这项重要元素的主导权。
舞蹈在录影里的变形
编舞家的工作空间是舞台,所以总有些「规范」(conventions)可循。其中一项假设是,剧院正中央是最理想的座位,因此舞台的正中央具有非常大的力量。这项规范使得即使因受剧场建筑之限没坐在正中央座位、未能享有相同视野的观众,也能认可舞台中心的特殊意义。
当我观看舞蹈录像时,我会不自觉地去辨认方位,哪里该是中心,哪里该是翼幕等等,除非作品明显地打破规范,专为录像的萤幕而编作。譬如,最近保罗.泰勒(Paul Taylor)所作《舌语》Speaking in Tongues的《舞在美国》Dance in America版,当这支舞从舞台版本转化为录像时,其原与传统规范的关系荡然无存。
「景深」(depth)也因录像而大受影响,实际上近乎消失。在镜头焦距不断的改变之下,眼睛接收缩小尺寸的形体时,无法测出相对距离。比方在现场演出,当动作急速地由后向观众前进,使形体赫然耸现时,能营造出极为戏剧化的效果,但在录像中却看不出这层变化,动作的影响力顿失。
从对角线拍摄能使舞蹈在萤幕上看来更有趣,且事实上,许多编舞家也觉得,这种取景角度在美学上的呈现较佳,也比死板的拍法更贴近原作意图。但这却让初始的动作设计完全变形。观看的角度也与原来完全不同!
「时间」(time)是另一个惨遭扭曲的元素。在录像里,慢的变得更慢,快的顿时显得无趣,中板则令人厌烦。极缓的慢动作反而经得起细看,但其显现的控制力却超越了实际的人类体能极限。
或者是因为上述时空感知的综合曲解,在录像中能展现的动作质地变化很少,导致舞作沦为一连串姿势的连续流动。
(待续)
原作|安‧娃向 Ann Vachon 纽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翻译|黄琇瑜 伦敦城市大学艺术评论硕士后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