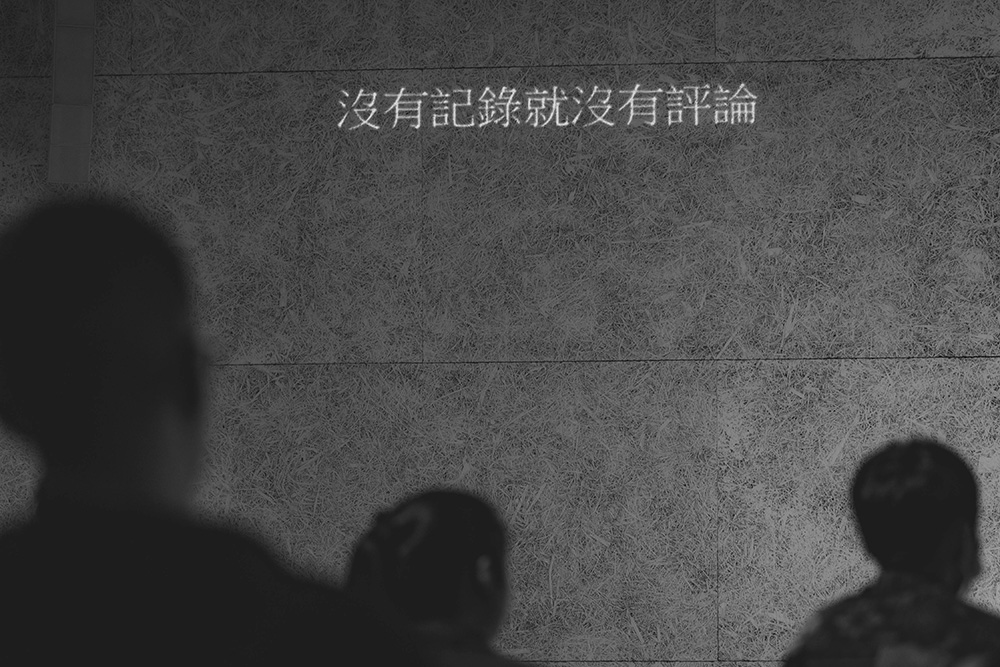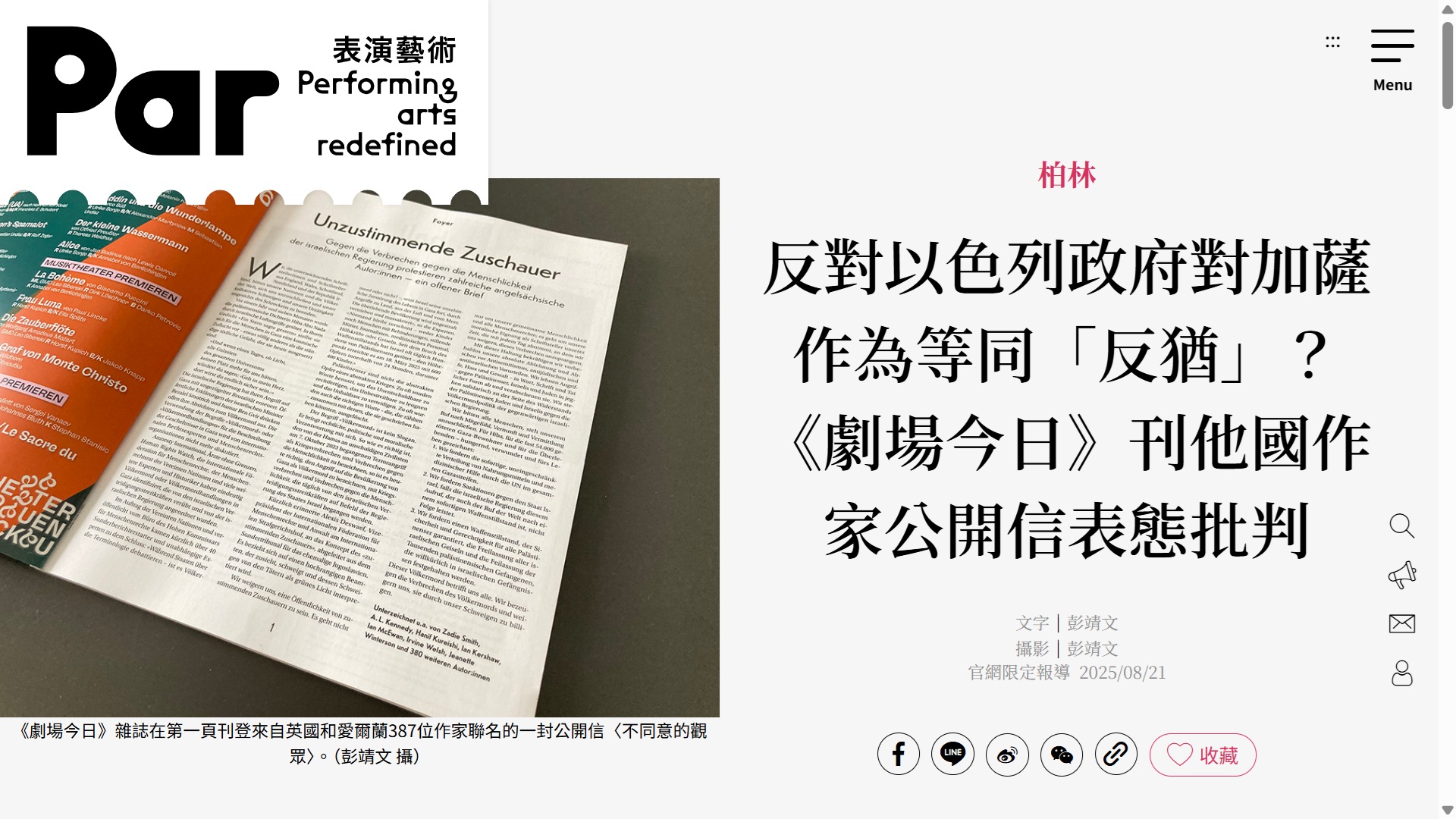张艺谋为走进太庙广场的观众制造了一个东西方艺术交界的海市蜃楼,他使观众不加理智地确信这个正义、温暖、爱情的故事永恒地发生在这里,永恒的歌声早就在重重深殿中涌动。
一九九八年的太庙是巨大的梦境。难以摆脱的魔幻力量和初秋的薰风亲吻过每个人的肌肤,现实的淸醒和梦境的神奇像月夜下明暗交替的光影恍惚迷离。公主华美宽大的衣袖和轻如鸿羽的幔帐被晚风吹拂漫卷,如同〈茉莉花〉的旋律在夜空中飘散流泻。恢宏壮丽的庆典唤醒了早已沉寂凝固的阴冷宫阙,宫墙大殿似乎有了起伏的呼吸,久远的潮水般的歌唱,使沉重的威严的历史在这一刻叹息着复活而来。一只盘旋在观众头上的飞鸟被辉煌的合唱声托起,直入广阔的天宇。
张艺谋为走进太庙广场的观众制造了一个东西方艺术交界的海市蜃楼,他使观众不加理智地确信这个正义、温暖、爱情的故事永恒地发生在这里,永恒的歌声早就在重重深殿中涌动。由于受空旷广场和保护古建的限制,张艺谋不可能沿袭他在佛罗伦斯导演《杜兰朶》时的演出模式,否则很可能陷入单调呆板的僵局。然而观众却发现两个仿造得和周围环境惟妙惟肖的亭子实现了多重舞台的功能,有类似镜头推拉摇移的功效。张艺谋通过两位杰出的舞台美术设计师高广健和曾力,在众目睽睽一览无余的广场上制造了层出不穷的魔术──两个构造巧妙、遍藏机关的亭子带来了丰富流动的舞台语言。张艺谋以雄浑的想像力敏锐地捕捉到广场的天然氛围与基调博大的《杜兰朶》的契和呼应相得益彰。而绚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使外国人也使中国人目不暇接。
传达强烈象征意味的亭子
从第一幕开始,浩浩荡荡层层叠叠的宫廷仪仗就照亮了舞台每一个角落,在惯常的太监宫女、华盖凤辇、文武大臣间,还安排了手持烛光的小和尙,于轻松诙谐中渲染了东方神秘色彩。两个亭子霎时现出华服高冠的太监群像,随着亭子的平移滑动,制造了活生生的古代宫殿生活画卷。在世界各地的《杜兰朶》中,杀手淸一色都是阴森恐怖的,而张艺谋从中国武侠小说里选取了一个出手厉害的小个子形象──在泥塑中破肚而出,耍中国武术,矫健诡诈,在巨大的《兵器谱》展开的十八般兵器中飞闪腾挪。从一页页侧立的《兵器谱》后闪出的白衣女子,代表刀下的亡魂,勾画出死亡的浪漫意境。
亭子在全剧中多处传达了强烈的象征意味。公主让卡拉夫猜谜时,白须白袍的大学士在亭中展读答案;威逼柳儿时两个亭子以逆光凸现狰狞恐怖的黑甲兵;在柳儿自尽霎那又以白甲兵的变化写意肃杀哀痛的氛围;在平庞彭三大臣酒醉后怀想家鄕时,亭子的运用达到精妙的高潮。舒缓的音乐中,如烟如幻的纱帘后是一组诗意葱郁淸淡怡静的画面──荷叶舒卷、村姑袅娜、水流潺潺,鬓影摇曳。乐队和合唱轻柔纯净,如飘浮的气流,与阗阗荷叶如影相随。在随后的三幕夜景中,亭子增加了平面舞台的景深,制造出深宫中灯影重重人影穿梭的效果。当两只亭子串连在一起时,惆怅的卡拉夫从亭子连成的走廊中穿过,倚着木柱唱出著名的〈今夜无人入睡〉。在全剧达到高潮时,两个亭子的门扇骤然拉开,花团锦簇的京剧穆桂英造型群像,长袖纷飞凤冠闪烁,与金璧辉煌的皇帝宝座、色彩斑斓的宫廷队列构成华美夺目的画卷。
早在九七年《杜兰朶》在佛罗伦斯演出时,中国观众无缘相见,只辗转知道罗马报界以空前的热忱、慷慨泉涌的美誉盛赞演出。张艺谋去年的佛罗伦斯版本高潮时同时出现九个舞台──八台中国京剧《龙凤呈祥》、《杨门女将》、《西游记》、《覇王别姬》等连同大舞台达到美艳炫目的极致,而今天的太庙实景《杜兰朶》则添加了广阔神秘的大自然和大气磅礴巍峨雄伟的中国宫殿,因而具有王者风范、中国气派。
舞台成为不可思议的梦境
如此空前的舞台呈现无疑须仰仗一流的舞美设计和制作。张艺谋作为导演,主要监控的也是舞美。在去年义大利演出时的四位舞美,今天只剩下两位:大陆舞美界最年轻最有才华,屡次得奖屡创佳绩的中央歌剧院高广健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曾力。难以想像就是这两位文质彬彬、内敛质朴的设计师实现了张艺谋不可思议的梦境。同张艺谋两年来的合作中,他们最强烈的感受是张艺谋由一个对舞台完全陌生的外行迅速地掌握了舞台艺术的关键。最初的合作过程是张艺谋放任他们去自由创作发挥,在拿来的画稿中一次次否定的同时,逐渐明晰了悟双方心中的追求。在反复的交流中张艺谋每一次都能抓住他们设计中的一个关键思想,并且总是能提出新的思路、新的途径。然而张艺谋只考虑效果,高广健与曾力却要从最艰难、最繁复的操作性上思考,设计也常常陷入无路可走的死胡同。张艺谋曾提出龙和凤的形象贯穿始终,却因最终无法支撑舞台而放弃。当张艺谋断然决定反潮流而行,把歌剧当作京剧时,两人豁然开朗,把角色按京剧行当归类定位,一切都明朗起来。在两年的合作中,他们深深体会到张艺谋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精妙掌握。身为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两人从学画观摩开始被灌输的都是西欧体系所谓洋化教育,对传统文化虽未排斥但至少是漠视的。在设计中,他们常常遭到张艺谋的「警吿」──「又走到别人身边去了,这样不行。」张艺谋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和选择几乎有一种天然的敏锐,一再矫正设计不要落入窠臼。高广健和曾力表示,通过这次设计以后将更加注意吸取传统文化。
两人表示,去年和今年的两台演出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刽子手出场、拔簪子自刎等戏保留下来了;但限于广场条件限制,无法呈现原剧场更诗化的创意。原来的演出在台上另做了八个小舞台展现不同京剧,把一个中国大舞台放在欧洲剧场是他们的想法。由于〈今夜无人入睡〉扮成老百姓的合唱队都摇着芭蕉扇,柳儿自刎后,一把把扇子在百姓手中传递到柳儿倒下的地方,这时柳儿前面的荷花隐没,柳儿的身体和扇子都从舞台纵深消失了。在柳儿曾经倒下的地方,舞台设计打开了一块台板,从台仓里缓缓地升起一把朴素洁白的折扇,一束台仓里照出的白光打在扇子上,扇子孤独地慢慢升向高空。而如今这种意味隽永的唯美设计在太庙无法实现是令人遗憾的。
作曲家叶小纲看过歌剧后连连盛赞「合唱和乐队极为出色,音响控制出色,梅塔的控制保证了演出成功的基础,连独唱也很优秀,歌唱演员都是世界级的,整个合唱音色统一。」至于人来人往的零乱,叶小纲客观地说广场艺术无法避免。「但主要演员舞台调度差,总在台口唱,队列一会儿走一圈,淹没了戏本身。灯光不够亮,没有气势。美国大都会的演出当皇帝出场时极为灿烂,而这一场的演出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中国以《杜兰朶》为蓝本第一次导演京剧的林兆华则并不看好此次演出,认为演出搞人海战术、太啰嗦太碎,倒像展示服装,演员被吃掉了,眼花缭乱没法让观众安静下来。戏本身被淹没了。
戏剧学者沈林则以孩童般的兴奋放宽了戏剧标准:「一看到满台绫罗绸缎衣香鬓影就觉得好玩。这是一场当代社戏(注),不妨用看社戏看庆典的心情看待。我始终很兴奋,戏剧的魅力很强,音乐和歌唱太出色了!」
注:
旧时某些地区的农村中春秋两季祭祀社神(土地神)所演的戏,用以酬神祈福,一般均在庙台或野台演出。一说社为古代划分地区的一个小单位,社中演戏称社戏。
文字|张向阳 北京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