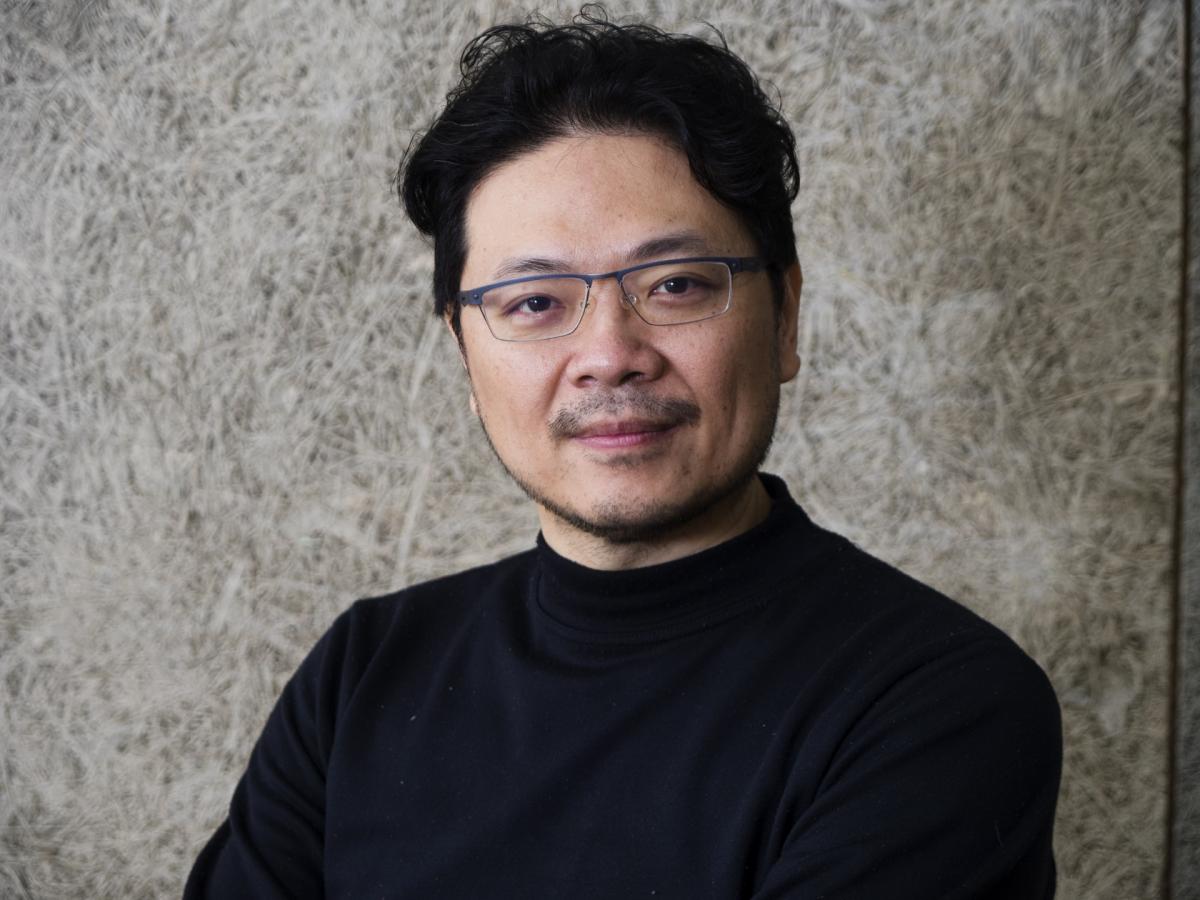这些前辈作曲家们皆追求过西方学院派作曲训练,但此种训练注重创作者的个人独特性,因此作曲家仍必须面对自己文化的根,诸般创作技巧终究不过是他们为原乡发声的路径。他们不仅双耳是经常张开的,所有感官皆是灵敏天线,不论素材是来自身边、远方,或多年前暂搁在记忆中的声音、或来自任何原乡的人事景象启发,作曲家总有办法将其化为音符,让外国人听见台湾,让台湾人听见自己的根。
自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影响所及,音乐创作者书写原乡情怀,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在台湾特殊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从作曲家的写作,听见他们对政治、文化与环境,极为多元的回应。
从「历史」角度爬梳台湾作曲家创作中的原乡情怀,是台湾多部作曲家传记常见的叙述角度。然而作曲家创作时使用素材的方式,不见得皆符合或反映「日治时期」、「二次大战后」、「解严后」等时间刻度;一九七三年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喊出「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舞给中国人看」那个不能大声说出「台湾」之名的时代,虽然已经远去,但如果延用林怀民的民族主义视角,从真正使用「台湾」素材创作之角度切入(注1),看前辈作曲家们如何刻画心中的台湾,或许将另有一番发现与趣味。笔者将以几首常被演奏的台湾前辈作曲家创作,探索他们如何以台湾素材发抒原乡情怀。
引用与再现台湾民间歌谣、曲牌或流行歌曲
这是作曲家最常使用的方式,绝大多数在管弦乐器、钢琴上呈现,但有以下不同程度的做法。
第一种是「旋律完整重现」:如郭芝苑(1921-2013)《古乐幻想曲》为钢琴独奏(1954,引用北管曲牌《水底鱼》)、萧泰然(1938-2015)《梦幻的恒春小调》为小提琴与钢琴(1973,引用恒春民歌《台东调》)、游昌发(1942-)《蛇郎君》为芭蕾舞剧的管弦乐(2010,引用多首原住民曲调)、温隆信(1944-)《初一朝》钢琴三重奏(2012,引用客家山歌子《初一朝》)。从这些乐曲中,皆可听到作曲家完整陈述引用的旋律,再以调性、五声调式或非调性和声或对位手法支撑该旋律,并考量该旋律再现时的变化,也设计变奏、幻想风或对比乐段。
第二种是「提示性的引用」:如李泰祥(1941-2014)《大神祭》(1976,使用一小部分的阿美族《出草歌》)、赖德和(1943-)《乡音》系列,为管弦乐或室内乐所创作(1995年后陆续创作)引用北管戏曲、南管曲牌、歌仔戏曲调等,以及柯芳隆(1947-)《锣声》钢琴三重奏(2005)将北管唢呐旋律作为动机、以钢琴模拟堆叠锣钞声响等。这些作曲家以点到为止的引用,触发原乡情调之后,即专注于演绎该素材,依照自我风格尽情发挥。
当然,「并置与对话」也是前辈作曲家常用的手法:如马水龙(1939-2015)在《无形的神殿》为男声合唱与管弦乐(2003)里,便使用了邹族祭神歌与布农族狩猎歌;潘皇龙(1945-)《普天乐》管弦协奏曲(2006)更完整使用北管鼓吹乐《普天乐》。此二例虽有相当完整的引用,但音响上并置了作曲家对于该素材之想法与评论,因而在引用之外,更呈现作曲家与传统音乐间的对话。最后,还有如「吉光片羽」般闪现引用旋律的方式:如许常惠(1929-2000)《思念的》小提琴独奏曲(1966)呈现恒春民歌「思想起」片段;卢炎(1930-2008)《雨夜花》弦乐四重奏(1987),将「雨夜花」旋律切片与改变音程。此二例中的旋律,散置于全曲各处,旋律碎片的断续呜咽,或许正是作曲家对于原乐曲悲凉意境的诠释。
声响、乐曲形式或声部结构的模拟
台湾作曲家经常在乐器选择上,使用传统乐器编制如锣鼓、唢呐、丝竹乐合奏,或以人声表达诵经、传统戏曲唱腔,或以语言本身趣味呈现等,从「声响」切入传统素材。这些作品的目的非仅为了模拟声响,而是以传统声响为表壳,作曲家自我风格与乐念为内容。在使用传统乐器上,马水龙在《廖添丁》舞剧音乐(1979)创作中使用了大量传统锣鼓;钱南章(1948-)也在《击鼓》击乐合奏曲(1987)引用锣鼓经等。人声使用也是声响模拟常用的手法,许常惠《葬花吟》无伴奏女声合唱曲(1962)以佛教诵经声响为基础结合引磬、木鱼和梵呗、戏曲唱腔和诗词吟诵,以宗教氛围表达曹雪芹黛玉葬花心境;马水龙《我是…》为女高音、长笛与打击乐团(1985)则让女高音以传统戏曲说唱方式演出,以吟唱方式表达马森诗作的哲思。此类乐曲在初次聆听时,或许首先听到的会是传统声响的趣味,但经过反复聆听便能逐渐穿过外壳,直透内涵,得到作曲家传达的意念。
乐曲形式或声部结构的模拟,如许常惠《百家春》以国乐团协奏的钢琴协奏曲(1981)就是使用同南管套曲由慢到快的曲式;赖德和《野台高歌》击乐合奏曲(1999)使用了北管「紧中慢」双层节奏结构。此二曲不但结合东西方乐器编制、引用传统旋律,更显示作曲家在和声与音响之外,构筑了富有台湾传统音乐精神的乐曲形式和声部结构。
多族群文化融合与本土语言歌曲
语言和族群也是作曲家看重的题材,如陈茂萱(1936-)《芋头与蕃薯》钢琴独奏曲(2003)、曾兴魁(1946-)《超级冲突》给长笛、吉他、钢琴、打击与电脑音乐(2005) 描述「319事件」、潘皇龙《阴阳上去》为一位念唱者、混声合唱团与十四位演奏家(1992/1995),歌词拼贴台湾谚语和华语四声音调、钱善华(1954-)《南岛颂》为管弦乐团(2014)结合台湾与南岛原民音乐特色,都是以对照之间产生的趣味,借由音乐描述台湾多元族群环境的现象。
有些作品无法归纳为上述几类,只能说它们具备东方美学与哲学意念,既不特别引用传统旋律,编制可能为东西方乐器的混搭,乐曲形式自成一体,却又呈现著台湾独特的和/汉/南岛/西方文化融合的景象,如:江文也(1910-1983)《台湾舞曲》为管弦乐团(1936)、马水龙灵感来自泼墨山水画的《意与象》为尺八与四支大提琴(1989);卢炎《海风与歌声》为管弦乐团(1987)以管特殊奏法达到音响色彩变化,描写风声浪潮中一段歌声飘过、潘皇龙《迷宫逍遥游》五重奏(1988/98,开放式音乐结构)……这些作品或在调式与节奏中呈现作曲家想像的庶人身体律动、或在音响层次中展现绘画的虚实气韵,或在乐思中透露禅意,或为了声响而将传统音乐语法晕染到所有声部之间。笔者将台湾刚解严时期,作曲家为本土语言写作的歌曲,也视为「使用台湾素材」创作,原因是本土语言受压抑四十载后,作曲家对于写作真正贴近自身语感作品的一种「乡愁」,不仅未消失且愈发强烈(注2)。以创作多首亲切动人歌曲的张炫文(1942-2008)为例,其作品在一九八九年起以河洛话歌词入乐。郭芝苑在戒严时期(1949-1987)使用河洛话创作的歌曲仅艺术歌曲《红蔷薇》 (1953,译有华语版)、电影主题曲《歹命子》(1962)和改编自采集念谣的《一个姓布》(1971)。但在解严后到一九九六年间,郭芝苑便一口气创作约卅首河洛话歌曲与歌谣,好似阻抑多时的乐念一次爆发,歌曲的短小篇幅也成为大众认识其创作最佳媒介之一。
持续寻找自己的时代精神
上列前辈作曲家们皆追求过西方学院派作曲训练,但此种训练注重创作者的个人独特性,因此作曲家仍必须面对自己文化的根,诸般创作技巧终究不过是他们为原乡发声的路径。他们不仅双耳是经常张开的,所有感官皆是灵敏天线,不论素材是来自身边、远方,或多年前暂搁在记忆中的声音、或来自任何原乡的人事景象启发,作曲家总有办法将其化为音符,让外国人听见台湾,让台湾人听见自己的根。
前辈作曲家们的作品,已成为中生代与新生代作曲家聆听经验之一部分;后辈们将持续在创作中追寻自己的台湾素材与时代精神,但或许将多一些自由,少一些乡愁。
注:
- 台湾前辈作曲家以中国民歌或故事为题的作品,或中国作曲家以台湾为名的作品,因篇幅限制暂不在此文讨论之列。
- 陈泗治(1911-1992)于1930年代亦创作河洛语之宗教歌曲,然时空背景不同,故不在讨论之列。台湾解严20年后,不论前辈、中生代或新生代作曲家,采用母语诗作为歌词已是常态,因此也不列入讨论。
参考资料: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之「台湾音乐家群像资料库」musiciantw.ncfta.gov.tw/hall.aspx
简巧珍,《二十世纪六○年代以来台湾新音乐创作发展之轨迹》,2011年,乐韵出版社。
颜绿芬主编《台湾当代作曲家》,2006年,玉山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