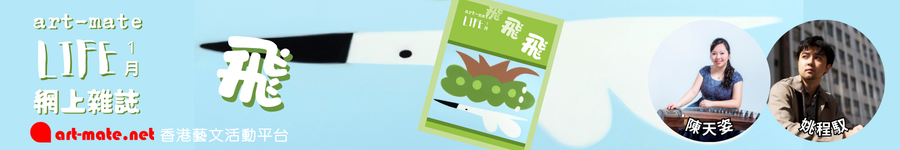谈及亚洲,对提著琵琶,随时准备近身肉搏不同音乐系统的音乐家钟玉凤而言,是个一时难以回应的命题。她说,「亚洲」有点大,有点空泛。在这个词汇的交集里,究竟我们谈的是地理位置、亚洲经验、亚洲文化,还是亚洲认同?
由形而上的概念切入,显然并非实践者习惯的思考路径,但当这些疑问被暂且搁置,回到她与五湖四海不同音乐人对打的实践经验中打捞,却有些共通的主题逐渐浮现,它们仿佛总指涉一种集体的风土喜好与命运牵连。
从经验出发,她如果发现音乐家手里没有和弦,大概就能判断这位乐人来自亚洲或非洲。她说:「和弦不是他音乐处理(的方式),或是说他的直觉。」只有在和欧洲或美国的音乐家合作时,对方才会问要弹什么和弦。
而除了音乐风格的光谱远近外,在过往的合作经验中,她也发现「被殖民」是她与亚洲、非洲音乐人的共同主题,尤其如果和她一样是被归类在传统音乐类的乐手,彼此总会讨论到:「你们如何和西方音乐交手?」在许多国家或学院仍将西方古典音乐奉为主流的情况下,这些音乐人在自己的国家往往是寂寞的,且更吊诡的是,反而去到欧洲,他们才能获得认可与关注。
在爱恨交织的处境里,非主流音乐人不断尝试突围,于外部现实环境与主流交锋,内部同样需极力争取空间。她说,受西方(学院)作曲训练的作曲家,在合法的路径内作曲,「通常技术会写得很难,因为他不了解乐器的性能,然后用西方的理解去写,总之那些东西大部分都让人手受伤。」
在和其他音乐人交流过程中,有时也会相互提到对此的愤怒。回到己身,她则一直强调对当代主流而言,自己走上这条作曲的路径是「不合法」的。她很明白其他人会怎么看,「以作曲的标准来看,我当然是不入流的,我光是一个指法跟一个声音,就成立这件事情,就是不够的。」但她仍然有个冲动,就像尝试改编《百家春》一样,因为这个音乐底蕴与她有关,她很清楚每个音代表什么意思。
她说:「我只是想拿回我被剥夺的权力。」
于这些参差对照的亚洲经验里,可以感受到一种扭曲的状态。音乐人既承继传统,但又需面对族群内部对音乐的无感与疲乏;向外拓展,虽能获得目光与理解,但被殖民的生命经验却剪不断理还乱。总是快人快语的她说:「虽然很扭曲,我们都要面对这个才能……就跟脱皮一样,每个亚洲音乐人都要从这里脱,脱一层很深的皮。」
另一个更大的阴影,她认为是我们集体焦虑于亚洲音乐、亚洲艺术如何被定位。对此,使用琵琶与音乐冲撞多年的她表示:「焦虑解决不了焦虑,如果回到音乐,我就会很自在,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在里面该怎么转译。」
钟玉凤
琵琶演奏家、作曲家,养成自传统音乐,关注古典于当代流动的样貌,创造力是她所在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