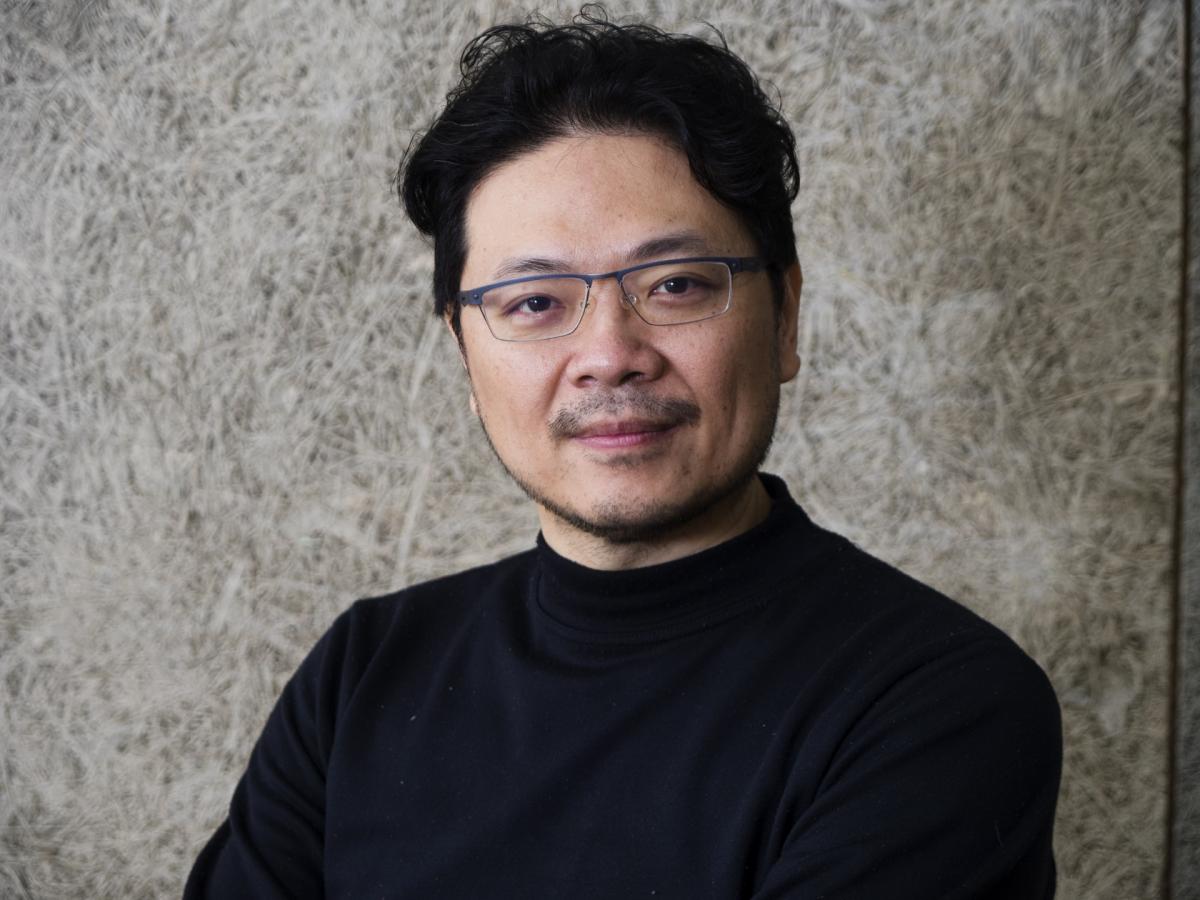這些前輩作曲家們皆追求過西方學院派作曲訓練,但此種訓練注重創作者的個人獨特性,因此作曲家仍必須面對自己文化的根,諸般創作技巧終究不過是他們為原鄉發聲的路徑。他們不僅雙耳是經常張開的,所有感官皆是靈敏天線,不論素材是來自身邊、遠方,或多年前暫擱在記憶中的聲音、或來自任何原鄉的人事景象啟發,作曲家總有辦法將其化為音符,讓外國人聽見台灣,讓台灣人聽見自己的根。
自十九世紀民族主義影響所及,音樂創作者書寫原鄉情懷,應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在台灣特殊歷史背景下,我們可以從作曲家的寫作,聽見他們對政治、文化與環境,極為多元的回應。
從「歷史」角度爬梳台灣作曲家創作中的原鄉情懷,是台灣多部作曲家傳記常見的敘述角度。然而作曲家創作時使用素材的方式,不見得皆符合或反映「日治時期」、「二次大戰後」、「解嚴後」等時間刻度;一九七三年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喊出「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舞給中國人看」那個不能大聲說出「台灣」之名的時代,雖然已經遠去,但如果延用林懷民的民族主義視角,從真正使用「台灣」素材創作之角度切入(註1),看前輩作曲家們如何刻畫心中的台灣,或許將另有一番發現與趣味。筆者將以幾首常被演奏的台灣前輩作曲家創作,探索他們如何以台灣素材發抒原鄉情懷。
引用與再現台灣民間歌謠、曲牌或流行歌曲
這是作曲家最常使用的方式,絕大多數在管絃樂器、鋼琴上呈現,但有以下不同程度的做法。
第一種是「旋律完整重現」:如郭芝苑(1921-2013)《古樂幻想曲》為鋼琴獨奏(1954,引用北管曲牌《水底魚》)、蕭泰然(1938-2015)《夢幻的恆春小調》為小提琴與鋼琴(1973,引用恆春民歌《台東調》)、游昌發(1942-)《蛇郎君》為芭蕾舞劇的管絃樂(2010,引用多首原住民曲調)、溫隆信(1944-)《初一朝》鋼琴三重奏(2012,引用客家山歌子《初一朝》)。從這些樂曲中,皆可聽到作曲家完整陳述引用的旋律,再以調性、五聲調式或非調性和聲或對位手法支撐該旋律,並考量該旋律再現時的變化,也設計變奏、幻想風或對比樂段。
第二種是「提示性的引用」:如李泰祥(1941-2014)《大神祭》(1976,使用一小部分的阿美族《出草歌》)、賴德和(1943-)《鄉音》系列,為管絃樂或室內樂所創作(1995年後陸續創作)引用北管戲曲、南管曲牌、歌仔戲曲調等,以及柯芳隆(1947-)《鑼聲》鋼琴三重奏(2005)將北管嗩吶旋律作為動機、以鋼琴模擬堆疊鑼鈔聲響等。這些作曲家以點到為止的引用,觸發原鄉情調之後,即專注於演繹該素材,依照自我風格盡情發揮。
當然,「並置與對話」也是前輩作曲家常用的手法:如馬水龍(1939-2015)在《無形的神殿》為男聲合唱與管絃樂(2003)裡,便使用了鄒族祭神歌與布農族狩獵歌;潘皇龍(1945-)《普天樂》管絃協奏曲(2006)更完整使用北管鼓吹樂《普天樂》。此二例雖有相當完整的引用,但音響上並置了作曲家對於該素材之想法與評論,因而在引用之外,更呈現作曲家與傳統音樂間的對話。最後,還有如「吉光片羽」般閃現引用旋律的方式:如許常惠(1929-2000)《思念的》小提琴獨奏曲(1966)呈現恆春民歌「思想起」片段;盧炎(1930-2008)《雨夜花》絃樂四重奏(1987),將「雨夜花」旋律切片與改變音程。此二例中的旋律,散置於全曲各處,旋律碎片的斷續嗚咽,或許正是作曲家對於原樂曲悲涼意境的詮釋。
聲響、樂曲形式或聲部結構的模擬
台灣作曲家經常在樂器選擇上,使用傳統樂器編制如鑼鼓、嗩吶、絲竹樂合奏,或以人聲表達誦經、傳統戲曲唱腔,或以語言本身趣味呈現等,從「聲響」切入傳統素材。這些作品的目的非僅為了模擬聲響,而是以傳統聲響為表殼,作曲家自我風格與樂念為內容。在使用傳統樂器上,馬水龍在《廖添丁》舞劇音樂(1979)創作中使用了大量傳統鑼鼓;錢南章(1948-)也在《擊鼓》擊樂合奏曲(1987)引用鑼鼓經等。人聲使用也是聲響模擬常用的手法,許常惠《葬花吟》無伴奏女聲合唱曲(1962)以佛教誦經聲響為基礎結合引磬、木魚和梵唄、戲曲唱腔和詩詞吟誦,以宗教氛圍表達曹雪芹黛玉葬花心境;馬水龍《我是…》為女高音、長笛與打擊樂團(1985)則讓女高音以傳統戲曲說唱方式演出,以吟唱方式表達馬森詩作的哲思。此類樂曲在初次聆聽時,或許首先聽到的會是傳統聲響的趣味,但經過反覆聆聽便能逐漸穿過外殼,直透內涵,得到作曲家傳達的意念。
樂曲形式或聲部結構的模擬,如許常惠《百家春》以國樂團協奏的鋼琴協奏曲(1981)就是使用同南管套曲由慢到快的曲式;賴德和《野台高歌》擊樂合奏曲(1999)使用了北管「緊中慢」雙層節奏結構。此二曲不但結合東西方樂器編制、引用傳統旋律,更顯示作曲家在和聲與音響之外,構築了富有台灣傳統音樂精神的樂曲形式和聲部結構。
多族群文化融合與本土語言歌曲
語言和族群也是作曲家看重的題材,如陳茂萱(1936-)《芋頭與蕃薯》鋼琴獨奏曲(2003)、曾興魁(1946-)《超級衝突》給長笛、吉他、鋼琴、打擊與電腦音樂(2005) 描述「319事件」、潘皇龍《陰陽上去》為一位唸唱者、混聲合唱團與十四位演奏家(1992/1995),歌詞拼貼台灣諺語和華語四聲音調、錢善華(1954-)《南島頌》為管絃樂團(2014)結合台灣與南島原民音樂特色,都是以對照之間產生的趣味,藉由音樂描述台灣多元族群環境的現象。
有些作品無法歸納為上述幾類,只能說它們具備東方美學與哲學意念,既不特別引用傳統旋律,編制可能為東西方樂器的混搭,樂曲形式自成一體,卻又呈現著台灣獨特的和/漢/南島/西方文化融合的景象,如:江文也(1910-1983)《台灣舞曲》為管絃樂團(1936)、馬水龍靈感來自潑墨山水畫的《意與象》為尺八與四支大提琴(1989);盧炎《海風與歌聲》為管絃樂團(1987)以管特殊奏法達到音響色彩變化,描寫風聲浪潮中一段歌聲飄過、潘皇龍《迷宮逍遙遊》五重奏(1988/98,開放式音樂結構)……這些作品或在調式與節奏中呈現作曲家想像的庶人身體律動、或在音響層次中展現繪畫的虛實氣韻,或在樂思中透露禪意,或為了聲響而將傳統音樂語法暈染到所有聲部之間。筆者將台灣剛解嚴時期,作曲家為本土語言寫作的歌曲,也視為「使用台灣素材」創作,原因是本土語言受壓抑四十載後,作曲家對於寫作真正貼近自身語感作品的一種「鄉愁」,不僅未消失且愈發強烈(註2)。以創作多首親切動人歌曲的張炫文(1942-2008)為例,其作品在一九八九年起以河洛話歌詞入樂。郭芝苑在戒嚴時期(1949-1987)使用河洛話創作的歌曲僅藝術歌曲《紅薔薇》 (1953,譯有華語版)、電影主題曲《歹命子》(1962)和改編自採集唸謠的《一個姓布》(1971)。但在解嚴後到一九九六年間,郭芝苑便一口氣創作約卅首河洛話歌曲與歌謠,好似阻抑多時的樂念一次爆發,歌曲的短小篇幅也成為大眾認識其創作最佳媒介之一。
持續尋找自己的時代精神
上列前輩作曲家們皆追求過西方學院派作曲訓練,但此種訓練注重創作者的個人獨特性,因此作曲家仍必須面對自己文化的根,諸般創作技巧終究不過是他們為原鄉發聲的路徑。他們不僅雙耳是經常張開的,所有感官皆是靈敏天線,不論素材是來自身邊、遠方,或多年前暫擱在記憶中的聲音、或來自任何原鄉的人事景象啟發,作曲家總有辦法將其化為音符,讓外國人聽見台灣,讓台灣人聽見自己的根。
前輩作曲家們的作品,已成為中生代與新生代作曲家聆聽經驗之一部分;後輩們將持續在創作中追尋自己的台灣素材與時代精神,但或許將多一些自由,少一些鄉愁。
註:
- 台灣前輩作曲家以中國民歌或故事為題的作品,或中國作曲家以台灣為名的作品,因篇幅限制暫不在此文討論之列。
- 陳泗治(1911-1992)於1930年代亦創作河洛語之宗教歌曲,然時空背景不同,故不在討論之列。台灣解嚴20年後,不論前輩、中生代或新生代作曲家,採用母語詩作為歌詞已是常態,因此也不列入討論。
參考資料: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之「臺灣音樂家群像資料庫」musiciantw.ncfta.gov.tw/hall.aspx
簡巧珍,《二十世紀六○年代以來台灣新音樂創作發展之軌跡》,2011年,樂韻出版社。
顏綠芬主編《台灣當代作曲家》,2006年,玉山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