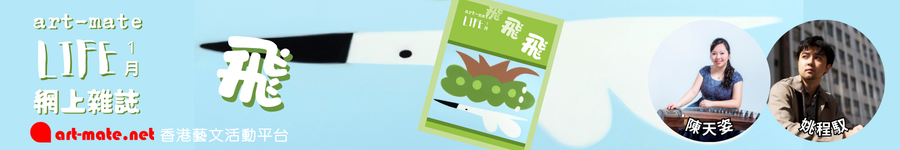周:扣回亞洲作為一種動態的交流平台,我想兩位是用這種方式在實踐跟尋找,建立點和點的關係與網絡,拓展一種亞洲的概念思考。你們怎麼想像與選擇哪些點?這些點在每一次的策展計畫裡所創造出,或是你們提示出來的這些點跟點所形成的是什麼地圖?
鄭:有參照點才能想像,畢竟差異無所不在。做《現實秘境》時,有兩個層面:一是對命題的思考,於是會想可以和哪些地方串連與結盟?這個展覽2018年巡展到首爾,而在首爾展出的選擇,也是有意義的。我希望通過冷戰時期共同位於第一島鏈相似的歷史經驗,擴大視野與討論。柏林圍牆倒塌往往被認為是冷戰結束的歷史時刻,然生活中真是如此嗎?在首爾開幕後的第二天,北韓的首領金正恩跟南韓總統文在寅就在冷戰分治的北緯38度線上世紀一握,那一幕證明了冷戰(及其意識)可能從來都沒有過去。
選擇在什麼地方展覽也有現實因素,比如說當時展覽論壇原本想辦在新加坡,但花費超出預算而作罷。論壇召集人許芳慈推薦吉隆坡,除了經費考慮,多位受邀的新加坡學者也因許多因素使得他們「不在」或已離開新加坡。展覽在首爾和台北、論壇在吉隆坡,台北做中介點,勾劃呈現第一島鏈的各節點所在。雖說如此,我並不會把單一的地理概念當作界定亞洲的唯一面向。另一個例子是我們曾經邀請學者黃孫權,以一年的時間舉辦「亞洲的諸眾與社會運動」講座,對我們來說,這即是以另一種能動性的觀點來切入討論亞洲。
周:這個做法跟立群在牯嶺街的策劃呼應。黃孫權用「諸眾和社會運動」,你們用「民眾」或「他者」。有關亞洲的製作、展覽或行為藝術,都在透過不同方法思考歷史下的他者或民眾為何。牯嶺街常處理到的是東北亞的行動,這在台灣比較少見。例如:邀請的韓國或中國的表演者、身體創作者,都是具有高度歷史省思但處於邊緣的狀態,想請你聊一下這部分。
姚:基本上正是邊緣對邊緣。應對現實的做法,不完全合乎我的想像跟理想,還是不得不從知識體系或實踐體系去面對現實。
前幾年策畫ARTWAVE時就明白,以現場的展演來說,台灣要成就這個介面需要一定的資本厚度,要做到最好的質感與底蘊一定要傾「國家之力」;要成就一個完整而豐實的舞台場景,一定是多方資源湊在一起才能達成。像《長夜漫漫路迢迢》是透過台灣、澳門兩個國際藝術節支撐出來。到《脫北者》(2017-2018)則是靠釜山SHIIM劇團、首爾北韓研究大學深淵研究中心,以及窮劇場與身體氣象館通力所籌備的資源,再集結台灣、韓國和馬來西亞的人力,最後才能在首爾演出。
《脫北者》從王墨林發起創作計畫,我接手首爾的製作後,確認了這個題目。韓國劇場自己一直都沒做,而歐美劇場主導的提案與創作接連實現——可以談光州事件、可以談反美,但還沒有人直接談脫北者?!
以跨文化的立場而言,我們的確是帶著非常關心的視線思考這些問題,去看不可抗拒或是無可奈何的背後是什麼。記得區秀詒在做第一次個展《棉佳蘭計畫》、回到吉隆坡時,跟她走在街頭,看到某些殘痕、線索,或是人群的聚集,這可能導引了我如何關注到移工內部的視線,其實也有一種邊緣對邊緣的感覺。我並不是真的一直活在這種世界裡,卻又因為工作本身的內涵與邂逅所吸引、被影響,也在其中增長智慧,增進理解人存在的意涵。
主持 周伶芝
記錄整理 黃馨儀
時間 2023/09/26 17:30-20:00
地點 立方計劃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