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馨儀
德國羅斯托克音樂與戲劇學院,戲劇教育碩士;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現為應用劇場、文字評論工作者。2015年回台後,持續以戲劇作為媒介,接觸群眾、開啟對話,探索自身與周邊議題。在創作表演與工作坊帶領的實踐之外,期許自己藉由書寫有更多的照見,尋找政治性與美學性兼具的劇場可能。
-
 戲劇
戲劇47條染色體的《嗨姆雷特》 不是模仿,而是活著
秘魯廣場劇團(Teatro La Plaza)《嗨姆雷特》(Hamlet)的初始場景,是一段生產影片:一個嬰兒正被從產道娩出,被接生、斷臍、正式成為獨立的個體,來到這個世界並投入母親的懷抱。而8名表演者們在這過程中陸續登上舞台,共同見證新生命的誕生。 對比被期待的新生兒,這些表演者實屬於「不被期待」的唐氏症患者與智力障礙者。目前台灣平均每1200個新生兒中,就有一位是唐氏症寶寶,孕初期收到的各式產檢資訊中,最被強調的即是唐氏症篩檢。除了政府有補助的初期、第二期唐氏症篩檢,也有非侵入式但較昂貴的NIPT(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 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還有最為準確、卻最為產婦猶豫孕中期是否要進行,須穿入肚腹的侵入式羊膜穿刺檢查。「如果檢測異常到底該怎麼辦?」在進行這些篩檢時,皆能看到已成形、且有心臟跳動的胎兒,生與不生,在產前即為一個龐大且令人不安的議題。
-
 焦點專題 Focus 業界觀點最速報
焦點專題 Focus 業界觀點最速報臺北戲劇獎,他們怎麼看?
劇場專案製作人暨行銷宣傳 鄭涵文:創造更多生態體系與創作思考的對話 臺北戲劇獎的設立,無疑將為台灣的劇場產業注入了一股新的刺激,也肯定會為劇場的生態帶來不一樣的審思,首先想討論的是,我們期待這個獎項鼓勵的目標為何?從現在的獎勵要點來看,仍是落在大方向的「鼓勵優秀從業人員及作品,建立本市當代戲劇之最高榮譽」,而在這樣的前提下,可想見,目前還無法針對想鼓勵或促進發展的目標有很清楚的規劃,希望如同紐約的奧比奬(The Obies),鼓勵藝術新創的實驗精神呢?還是希望如倫敦的勞倫斯.奧立佛奬(The Laurence Olivier Awards)引起戲迷的討論與關注度,並成為票房保證的指標呢?也許現階段,我們可以期待的是,透過臺北戲劇獎的評選過程,創造更多對於生態體系與創作思考的對話,在過程中,逐漸形塑出臺北戲劇獎的指標性目標。 臺北戲劇獎的創始,加入觀眾的評選,也意味著,在市場與創作間平衡的討論,更可能發生在這次評選的思考中,如同導演托瑪斯.奧斯特邁爾(Thomas Ostermeier),便是透過歐洲的多項獎項,脫穎而出後,燙金效應也讓他的演出場場爆滿。但在臺北戲劇獎第一屆的參加辦法中,想先提出兩點問題討論,第一點,設定在典型的劇場空間演出才能報名參加,在現今有愈來愈多非典空間的演出,多元形式反而是被拒絕在外,期待更開放的思考創作的定義,並持續進化跟調整。第二點,用一個最佳劇場設計獎來鼓所有設計群們,更是一大疑問,要如何在不同的材質與媒介,涵括並評斷現今已專業分工的設計,直到產出這唯一獎項?顯然會是一個大困難,可想見,獎項的擴增與評審機制也會是未來重要的討論。 另外,若從生態來思考,臺北戲劇獎的設立,除了鼓勵優秀的創作者外,也提供了一個當下凝聚公眾性討論的重要時刻。正因為如此,如何成為促進劇場生態系交流的平台,不僅僅是獎勵優秀作品,更可能打開業界的對話與合作,都可通過舉辦頒獎典禮的時刻,藉由舉辦各類型工作坊、研討會等活動來實現交流對話的可能性,讓獎項成為一個聚集的平台,共同探討表演藝術的未來思考,並增加市場發展的思維。也許一個獎項很難成為影響生態系的進步,但卻是可視為一段劇場人能被集結討論的關鍵時間,更多開放性的討論與發展。也許
-
 戲劇 文學與劇場的多重互文
戲劇 文學與劇場的多重互文《誰在暗中眨眼睛》既冷且熱的現世關照
10月,連續陰雨瞬間終結了整個夏季的燠熱。在灰陰的日子,走入動見体近河濱的排練場,時間好像跟著緩慢了下來。與導演符宏征的對話,不快,卻深刻,也讓時間更為凝鍊,阻隔外頭的車水馬龍。 在出入之間,尋找原著精神 符宏征凝練的話語,在談到王定國的小說卻有火花迸發。他總是露出興奮的神情,像是遇到知己:「王定國的小說結尾常常會戛然而止,讀的當下會覺得:怎麼會這樣?怎麼不揭露多一點?但這個不揭露也是我做戲的風格,有所保留、有時候不太直接地去留白。」對他而言,王定國的小說平衡很好,故事簡單不複雜,卻舉重若輕,能入世也可以出世;乍看通俗,卻能深刻呈現人心與人性的幽微。作者的情操與人格也在適切的書寫距離中展現。這次的5個小品也以小情小愛為主,格局不大,卻很悠遠。 「這東西,做不好就真的有點8點檔。」他因為實在太喜歡王定國的文字了,更造成前期發展卡關:「卡死在是,我找不出自己的故事,都要跟他的故事走,甚至想說算了,不要變成作品,保持未完成,永遠用讀劇的方式去介紹王定國。讀劇就可以大量使用我覺得裡面很棒的文字。」為了突破己身盲點,符宏征邀請高俊耀加入編劇。 高俊耀不滿足於符宏征選給他的10篇短篇,又自己大量閱讀王定國的其他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尋找新的切入點,尤其鎖定其文字中展現的時代感。此次《誰在暗中眨眼睛》選取原小說集中的〈本壘〉、〈蝴蝶〉、〈六月下午的家〉,並加上《神來的時候》裡〈顧先生的晚年〉與《夜深人靜的小說家》的〈櫻花〉,共形成5個小品。各篇章故事獨立,卻也保留王定國小說裡絕妙的互文,並藉由垃圾車的樂音銜接各篇章。兩人不囿於原著,以忠於原著精神為共識,層層解碼王定國的文字,共同對話。從原著,到劇本,再到演員表演,轉譯的過程也形成一種互文。
-
 戲劇 冷酷又溫柔的「手術」
戲劇 冷酷又溫柔的「手術」《搞砸的那一天》 切片人生、縫合心靈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即將在兩廳院秋天藝術節推出《搞砸的那一天》,從形式與媒材著手,挑戰當代偶戲的可能性,讓操偶台成為解剖台,拼貼音樂與視覺投影,剖開現代化社會的病徵。 從進手術房的那一天開始 雖然《搞砸的那一天》是回應社會的議題之作,初始發想實來自藝術總監與導演鄭嘉音的手術經驗。鄭嘉音原本是健康寶寶,很少進醫院,卻因為子宮肌瘤,在50歲生日那一天被推進開刀房。一進醫院就得被開腸剖肚,而身體被挖開這件事,對她的生命產生了不同的震撼感,也興起了以人體為主題的作品念頭。 在醫院的時間也讓鄭嘉音對醫療器械產生「迷戀」,總是把握時間東看西看、進行觀察。冰冷的手術器材與等待手術的人體,讓她聯想到偶的身體:「對比到偶戲,我們會創造一個肉身 ,肉身擺在那就是肉身,要靠操偶師去操作才會有生命。」但人的生命不僅止於物理性的消化呼吸排泄,更重要的是思想與靈性層面,所以操偶師除了要模擬人體的真實,更要詮釋角色的個性與性格。這些連結,讓鄭嘉音深深著迷。 發展過程中,鄭嘉音由人體運作進一步聯想到社會關係:「人體每一個部件和器官都像一個小社會,所以就想蒐集眾人的故事,讓故事匯集在這樣的人體內部。」於是,她協同文本創作郭品辰,開始整理不同的網路新聞,以及Dcard和PTT的文章,跟演員一起閱讀這些資料。
-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編劇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編劇陳弘洋 努力,是讓我能好好活下去的方式
那一天,台北終於歇止了近兩週的雨勢。雲層厚重,不時飄著細雨。陳弘洋脫下長袖長褲,不畏寒冷在蔚藍的操場上跑起來。黃色的身影在藍色的跑道上躍動著、繞著圈子,也烙印下鮮豔的軌跡,如他的寫作。
-
 跨界 一對一共享流動的回憶
跨界 一對一共享流動的回憶弗蘭塞斯克.薩雷維拉《拾憶》
兼具建築師與舞台設計的身分,創作者薩雷維拉擅長以現地裝置與現場表演與觀眾互動,進一步創造沉浸感受。他將於2022TIFA推出線上互動作品《拾憶》,透過通訊軟體與台灣觀眾交流,召喚回憶並轉化共創;同時他也規劃了《記憶劇場》現地裝置,將展出《拾憶》演出期間所收集到的一些故事。
-
 藝@書
藝@書透過理解藝術,建構公共對話的空間
近年來,「展演」的現身領域變廣,「表演」的場域也更加多元。此現象並不僅是分類範圍的跨界與跨域,更顯示著藝術為了接軌現代社會的不同嘗試。2017年臺北市立美術館的「社交場」即為台灣近年代表性的案例,連結靜態展示(be displayed)與現場藝術(be performed),除了展覽,更串連舞蹈、戲劇與音樂,進行一連串活展示(live exhibition),探索「展示」與「表演」間的共生與共創關係。而此後,劇場性的展演更是大幅度地在各
-
戲劇 在移情與認同的邊界
《恐怖谷》開啟另類的科技展演
自從AI人工智慧讓人造人變為可能之後,探討相關議題的動漫影視創作也前仆後繼地出現,將在兩廳院秋天藝術節展演的《恐怖谷》是少見以劇場觸及此主題的創作,甚至直接「造人」,直接讓擬真的人形機器直接在觀眾面前展演,虛實交錯地探索觀眾的心理認知狀態。
-
焦點專題(二) Focus
沉浸體驗 讓觀眾驚喜、讓產業歡喜?
近年來,「沉浸式劇場」成為表演藝術界的熱門關鍵字,也吸引新的觀眾群。沉浸體驗的熱門,似乎也反映現代科技社會高度線上與虛擬化後,參與者對於體感的復返需求,不只是要購買經驗,更期待著體驗強化,讓沉浸娛樂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實境樂園。而當本即結合燈光、音樂、舞台與文本等表演媒材的劇場亦一起沉浸,是否能為尚無法產業化的表演藝術界找到新的生機?劇場是否能乘著沉浸式體驗的旋風,讓藝術和娛樂商業結合?就此提問,便不得不將眼光投注向體驗設計公司「驚喜製造」陳心龍與劇場團體「進港浪製作」洪唯堯近年的合作。
-
話題追蹤 Follow-ups
差事劇團與再拒劇團的關懷及實踐
該以怎樣的形式回應我們所在的這片土地,連結社會,同時又讓議題演出好看,與創作者的養成脈絡與美學想像高度相關。「差事劇團」與「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逾20年的實踐,雖同樣是長期藉由劇場回應社會現象的劇團,卻有全然不同的創作路徑與嘗試方向。劇場抵達的社會的形式多元,議題、地方、參與都是可選擇的元素,然重要仍是回到創作者自身關心什麼、想說什麼,因著動機,自然會找到述說的方法。
-
焦點專題 Focus
「歷史的返視、評論的在場」第一講側記
2019年TT不和諧開講,以「歷史的返視、評論的在場」為題,由表演藝術評論台策畫,並與《PAR表演藝術》雜誌合辦。表演藝術評論台台長,也是本次主持人紀慧玲,因表演藝術評論台自2011年開台所累積的大量評論書寫,促使其不斷思考這樣的「過量生產」是否有產生實質意義?無論是對評論者、對創作者、對文化政策或是對藝文生態,是否確有產生影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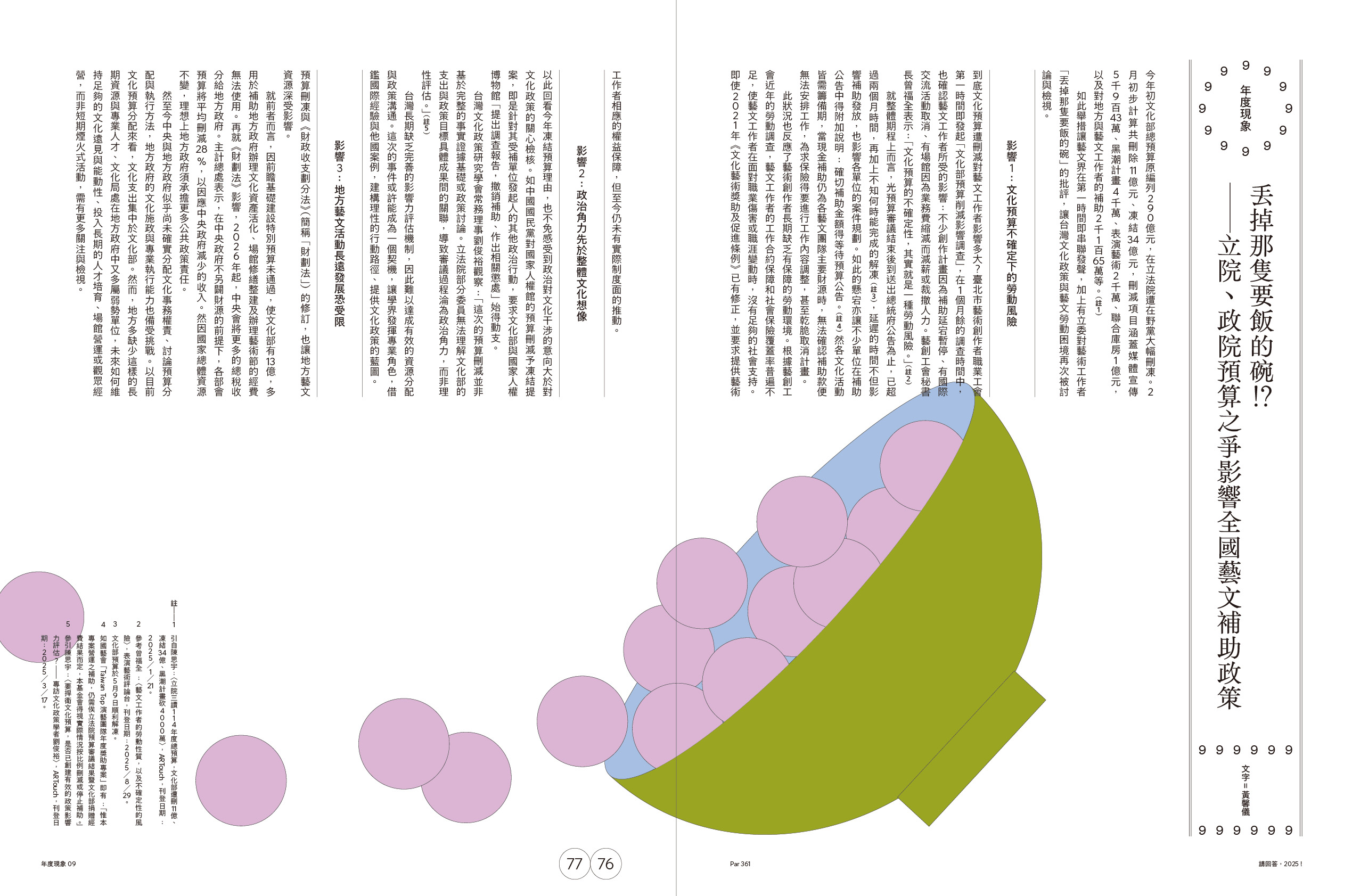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年度現象 09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年度現象 09丟掉那隻要飯的碗!?——立院、政院預算之爭影響全國藝文補助政策
今年初文化部總預算原編列290億元,在立法院遭在野黨大幅刪凍。2月初步計算共刪除11億元、凍結34億元,刪減項目涵蓋媒體宣傳5千9百43萬、黑潮計畫4千萬、表演藝術2千萬、聯合庫房1億元,以及對地方與藝文工作者的補助2千1百65萬等。(註1) 如此舉措讓藝文界在第一時間即串聯發聲,加上有立委對藝術工作者「丟掉那隻要飯的碗」的批評,讓台灣文化政策與藝文勞動困境再次被討論與檢視。 影響1:文化預算不確定下的勞動風險 到底文化預算遭刪減對藝文工作者影響多大?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第一時間即發起「文化部預算削減影響調查」,在1個月餘的調查時間中,也確認藝文工作者所受的影響:不少創作計畫因為補助延宕暫停、有國際交流活動取消、有場館因為業務費縮減而減薪或裁撤人力。藝創工會秘書長曾福全表示:「文化預算的不確定性,其實就是一種勞動風險。」(註2) 就整體期程上而言,光預算審議結束後到送出總統府公告為止,已超過兩個月時間,再加上不知何時能完成的解凍(註3),延遲的時間不但影響補助發放,也影響各單位的案件規劃。如此的懸宕亦讓不少單位在補助公告中得附加說明:確切補助金額得等待預算公告。(註4)然各文化活動皆需籌備期,當現金補助仍為各藝文團隊主要財源時,無法確認補助款便無法安排工作,為求保險得要進行工作內容調整,甚至乾脆取消計畫。 此狀況也反應了藝術創作者長期缺乏有保障的勞動環境。根據藝創工會近年的勞動調查,藝文工作者的工作合約保障和社會保險覆蓋率普遍不足,使藝文工作者在面對職業傷害或職涯變動時,沒有足夠的社會支持。即使2021年《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已有修正,並要求提供藝術工作者相應的權益保障,但至今仍未有實際制度面的推動。</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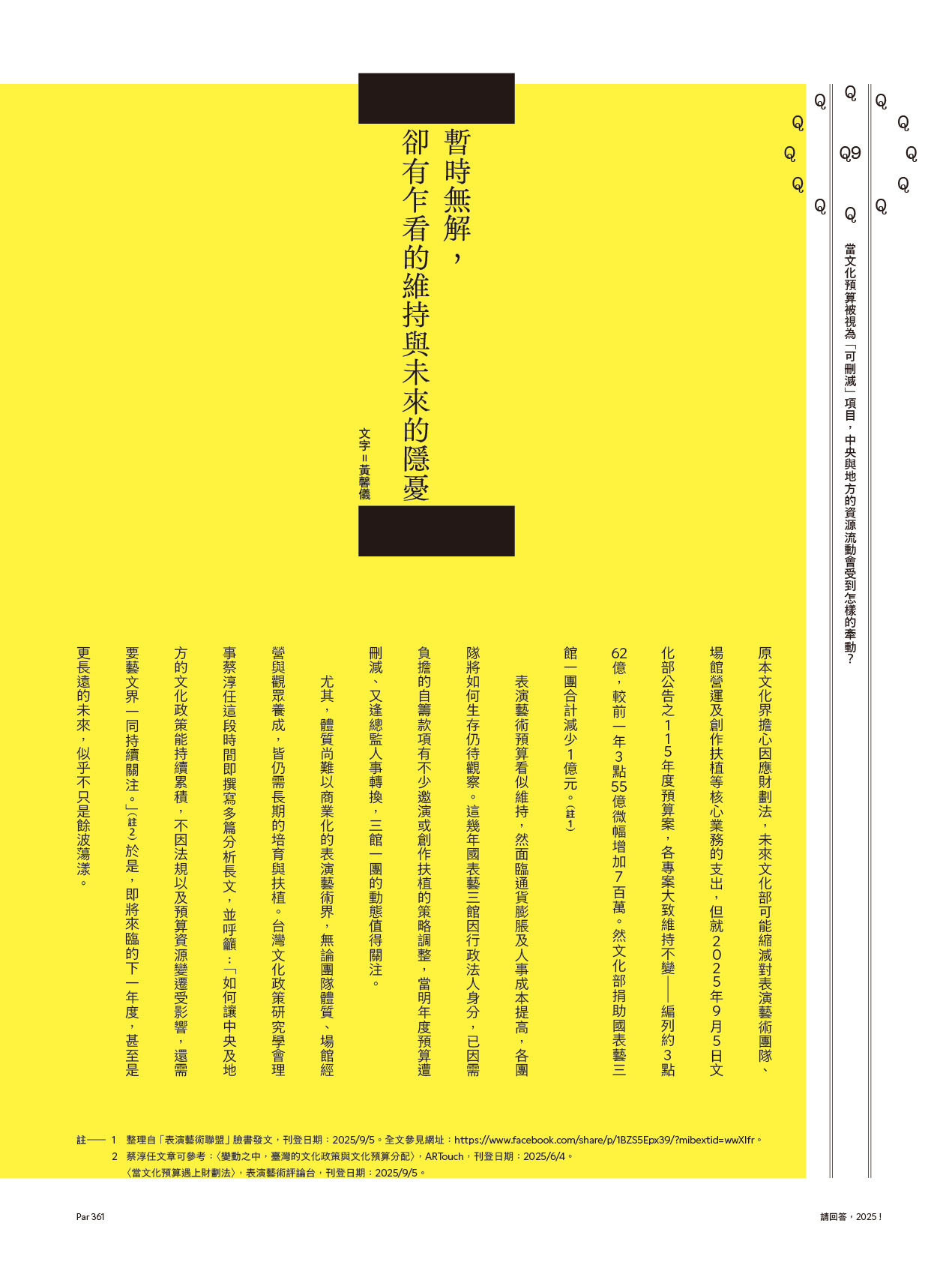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請回答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請回答暫時無解,卻有乍看的維持與未來的隱憂
Q9:當文化預算被視為「可刪減」項目,中央與地方的資源流動會受到怎樣的牽動?
-
 戲劇
戲劇拆解幽微的性與暴力
在2023年6月,由政治界而起,再至教育界、演藝圈、藝文團體相繼爆發的#MeToo事件後,不少案件已進入後續司法程序,性平三法亦順勢而為,終於有所變更修正(註1),文化部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等單位也著手進行涉及性平事件之創作者的獎補助處置。(註2)當體制介入,民眾關注度可能有開始降溫的趨勢,卻也有無法自證的事件漸漸被人淡忘。 隨著這波#MeToo事件的階段性落幕,卻有兩檔作品分別於秋季的高雄、台北上演,深入剖析並探問更難以言說的性與暴力。 性暴力的多元面向 如果要談純粹的性暴力,輸入關鍵字就可以查到定義。維基百科即清楚引述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世界暴力與衛生報告》,將性暴力定義為:「(施暴者)以暴力或脅迫等手段,企圖強迫他人跟自身發生任何形式的性關係、性騷擾、性挑逗,以及販運自身予他人等行為,不論當事人之間的關係為何,且可以發生在任何場所,包括但不限於職場或家庭。」然而落實到生活中,再清楚的定義也會因為人際與社會互動的複雜性,而有模糊不清的地帶像是性暴力也包含言語騷擾和開黃腔等非肢體觸碰的行為,而偷拍和散播私密影像會涉及妨害秘密罪與猥褻物品罪;在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一書問世後,權勢性騷擾與性侵之概念也進入社會大眾視野,使人對性暴力中的權力處境有不同的省思。 在2017年《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之後,台灣社會花了6年的時間,翻湧出自己的#MeToo浪潮。當社會愈來愈能重探性與情慾、討論情感與性教育,亦能開始剖析性暴力的複雜程度。 2023年的#MeToo,更體現了這點。尤其是種種對於師生關係、職場從屬、生涯發展等權勢性侵的揭露,更顯示大眾對於個人的情慾與社會階級結構開始能辯證區分。2003年掀起浪潮的原創影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便是由此出發去探討職場騷擾與權勢暴力;近年亦有再拒劇團的《感傷之旅》(2019)及兩廳院駐館藝術家(2021-2022年)黃郁晴的《藝術之子》(2023),以劇場形式展演論證藝術創作環境中的權力位階與關係暴力。 此波#MeToo亦有始於正常情感關係的受害者自白,由此也帶來個體性意願的界限討論,「怎樣才是合意性行為」成為一個思考關鍵。然而,卻
-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 Feature國家兩廳院:成為連結歐亞的藝術樞紐
2017年,國家兩廳院在30周年之際進行組織調整,在節目企劃部下單獨設立了國際發展組,此舉對應著兩廳院對自身成為「亞洲場館」的定位期待與發展策略:作為台灣最老牌藝文場館,兩廳院長久以來與歐美表演藝術界的關係深厚,並引進了不同的演出與創新概念,卻對亞洲的創作發展與交流十分陌生,也因此開始思考其中發展失衡的成因。 重訂國際發展策略,直面失衡的亞際交流 在此思考之下,兩廳院先於2019年舉辦了兩日的Asia connection論壇,邀請來自日本、韓國、柬埔寨的藝術機構策展人,從他們自身與亞洲藝術家的策展合作經驗,分享對於「亞洲連結」的經驗與看法,相互激盪產生連結的可能形式。論壇中,與會者從製作面與各國文化政治生態開啟認識,卻也發現其實亞洲場館間的相互連結與作品邀請不多, 整體的創作品味更是偏向西方。 國家兩廳院副藝術總監施馨媛表示,19世紀開始的西方現代主義為「當代藝術」創造了一個分水嶺,不在現代主義的角度下發展的當地藝術,都被稱為傳統藝術,而成為所謂的「傳統戲曲」:「所有的當代,不論是舞蹈、戲劇、文本都是以西方的脈絡發展為基礎並作為學習對象,反而因此忽略了亞洲的脈絡。」除了彼此對亞洲藝術家與創作狀態缺乏認知之外,在論壇討論中,兩廳院也發現亞洲缺乏共製的生態系統,無法像歐洲一樣經由共製進行資源串連和發展巡演。為求平衡表演藝術美學的東西方失衡,也希望透過有策略的計畫發展亞洲的共製生態系統,並形成一個交流平台,協助形塑亞洲觀點的作品,因而產生了「亞洲連結:製作人工作坊」(Asia Connection: Producers Camp,ACPC)3年計畫。
-
 特別企畫 Feature 姚立群X鄭慧華
特別企畫 Feature 姚立群X鄭慧華跳脫虛幻的亞洲,以空間策展建構關係的平台(上)
與其說是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理軸線轉移,倒不如說是從地緣到邊緣的批判思維與策展實驗,推使這場對談向多重的歷史經驗開展立方計劃空間的共同創辦人與藝術總監鄭慧華,以推廣當代藝術、整合藝術歷史脈絡、聯繫國際與在地網絡為使命,自2010年起開始營運立方計劃空間,讓此處成為一個展場與講座、交流、資料庫功能的複合藝文空間。而2005年起承接牯嶺街小劇場營運的身體氣象館,則由館長姚立群領軍,著重於小劇場發展的文化整體脈絡,希望開創一個多元面向的創意空間,形塑其公共性,成為「亞洲實驗劇場中心」。 在對談中,兩人分別由電影、劇場與視覺藝術領域交互視野。對他們而言,「亞洲」或許僅是一個虛幻概念,當「亞洲不亞洲」反而更能形成意識形態的抵抗。如同展演空間並不只為展演,卻是檔案的匯聚點,以此建構關係與對話的平台,藉由人與人的相遇迸發可能,讓深度的交流在此發生。
-
 特別企畫 Feature 姚立群X鄭慧華
特別企畫 Feature 姚立群X鄭慧華跳脫虛幻的亞洲,以空間策展建構關係的平台(下)
周:扣回亞洲作為一種動態的交流平台,我想兩位是用這種方式在實踐跟尋找,建立點和點的關係與網絡,拓展一種亞洲的概念思考。你們怎麼想像與選擇哪些點?這些點在每一次的策展計畫裡所創造出,或是你們提示出來的這些點跟點所形成的是什麼地圖? 鄭:有參照點才能想像,畢竟差異無所不在。做《現實秘境》時,有兩個層面:一是對命題的思考,於是會想可以和哪些地方串連與結盟?這個展覽2018年巡展到首爾,而在首爾展出的選擇,也是有意義的。我希望通過冷戰時期共同位於第一島鏈相似的歷史經驗,擴大視野與討論。柏林圍牆倒塌往往被認為是冷戰結束的歷史時刻,然生活中真是如此嗎?在首爾開幕後的第二天,北韓的首領金正恩跟南韓總統文在寅就在冷戰分治的北緯38度線上世紀一握,那一幕證明了冷戰(及其意識)可能從來都沒有過去。 選擇在什麼地方展覽也有現實因素,比如說當時展覽論壇原本想辦在新加坡,但花費超出預算而作罷。論壇召集人許芳慈推薦吉隆坡,除了經費考慮,多位受邀的新加坡學者也因許多因素使得他們「不在」或已離開新加坡。展覽在首爾和台北、論壇在吉隆坡,台北做中介點,勾劃呈現第一島鏈的各節點所在。雖說如此,我並不會把單一的地理概念當作界定亞洲的唯一面向。另一個例子是我們曾經邀請學者黃孫權,以一年的時間舉辦「亞洲的諸眾與社會運動」講座,對我們來說,這即是以另一種能動性的觀點來切入討論亞洲。 周:這個做法跟立群在牯嶺街的策劃呼應。黃孫權用「諸眾和社會運動」,你們用「民眾」或「他者」。有關亞洲的製作、展覽或行為藝術,都在透過不同方法思考歷史下的他者或民眾為何。牯嶺街常處理到的是東北亞的行動,這在台灣比較少見。例如:邀請的韓國或中國的表演者、身體創作者,都是具有高度歷史省思但處於邊緣的狀態,想請你聊一下這部分。 姚:基本上正是邊緣對邊緣。應對現實的做法,不完全合乎我的想像跟理想,還是不得不從知識體系或實踐體系去面對現實。 前幾年策畫ARTWAVE時就明白,以現場的展演來說,台灣要成就這個介面需要一定的資本厚度,要做到最好的質感與底蘊一定要傾
-
 特別企畫 Feature 藝術家回應
特別企畫 Feature 藝術家回應再拒劇團:拒絕現有框架,種下改變的種子
2020年,「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更名為大眾已習慣的簡稱「再拒劇團」。團長黃思農笑稱改名只是因為團名太長,並未正式對外宣告,但更名對團內其實是一種心情重組2018年做完《春醒》,因為製作票房不如預期,再拒面臨高額負債,靠著2019年大量接案與製作,雖然還清負債,卻也感覺疲憊。內部討論著是否要解散或是休息?後來決定乾脆把團名改一改,換一個新氣象。製作人羅尹如亦是在這過量生產的一年加入再拒。 文化政策與勞動環境的惡性循環 2002年成團的再拒,正好經歷了台灣文化體制轉變的時期。90年代中期開始的機構與學院建置、各種補助機制建構,以及法規與場館政策,皆迫使小劇場一同進入機制化建構,少部分劇團帶著社會主義思考,重新「產業化」另途。 在此脈絡下,再拒在2007年做完第一檔大型製作《沈默的左手》後休團一年,確認劇團職業化發展的路線,並將參演者勞動權益納入營運思考。儘管有補助的挹注,每檔製作前皆評估製作規模、預留劇團的行政管理費,仍常入不敷出,只能盡量取得平衡。即使已知製作會賠錢,也不縮減人員工作費。為求反應成本,2013年起再拒自發調漲演出票價,然而因為演出形式使得觀眾人數受限,票價能回收的成本實也有限。 談及現行補助機制與勞動權益,羅尹如表示當目前補助金額無法提高,在僧多粥少的競合狀況下,也讓從業者習慣用低薪評估自己的工作價值,形成惡性循環;而補助金額無法提升,實也受限於文化單位所能取得的中央經費不足。就此黃思農指出當前文化政策上資源分配定位不明的問題:政府一方面希望扶植實驗劇場與具公共意義的演出,另一方面又希望繼續補助商業劇場以形成產業;主要補助單位仍是根據文化政策方向提供補助,並未區別各自補助對象,90年代「小劇場聯盟」就提出的問題至今依然無解。
-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 Feature烏犬劇場X蘇慶元
人稱「小C」的蘇慶元,與烏犬劇場的彭子玲、王少君聽聞彼此已久,但未在現實有實際交集,直到2021年12月悅萃坊舉辦的「部落戲劇」分享中才遇見。同時,兩組人都有不同的心理學背景,和特殊處遇青少年工作。小C為戲劇治療師,工作對象多為早期療癒或依附關係困難兒童與青少年,並多和安置機構合作,以戲劇治療的遊戲切入,帶入象徵、投射、角色扮演,重新建立自己與他者的關係。烏犬劇場則師承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的脈絡,以行動研究與團體動力為主軸,在密集的戲劇營隊工作中,讓孩子認識自己的處境、尋找適合自己未來的改變方案。 本次對談特邀小C與烏犬劇場的彭子玲、王少君對談,以不同的經驗視角回看傳統心理治療框架,從而反思特殊處遇青少年所面臨的制度問題,尋找以戲劇作為方法建構陪伴與關係上的行動可能。
-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 Feature用藝術,與中輟少年重建關係
走過30年的中介教育學校:慈輝班 為協助經濟困難或家庭變故的中輟復學生回歸教育體系,教育部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多元型態中介教育措施」,提供轉銜適應的中介教育,避免中輟復學生再度輟學。「慈輝班」即為其中一種中介教育形式,源自於1994年省政府時期的慈輝專案,專收家庭變故、經濟困難之中輟學生,由教育部補助、提供住宿、生活輔導與多元適性教育。慈輝班的規劃在當時十分另類新穎,也讓國中生能提前接觸到高職的技職課程。目前全省慈輝班有11所,位於嘉義縣番路鄉的民和國中慈輝分校(以下簡稱民和慈輝)即為其一。 民和慈輝以技職教育為發展主軸,白天依照課綱進行學科課程,每週一、四下午則有作為職涯試探的技藝課程,包含烘焙、餐飲、美髮、化工、動力機械與商管設計6個專業。學科課程教師依照教師甄試選填分發,而技藝課程則和周邊的職校合作,或經由推薦尋聘適任教師。另設有夜間課程選修,一方面延續技職科目,一方面則有社團課程,如手工拼布、熱舞、鼓藝和電音三太子,與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以下簡稱青藝盟)的戲劇課程亦在此類別,固定在週三晚間發生。 2017年,因為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牽線,前任校長陳冠伶結識了青藝盟盟主余浩瑋,共同開啟「風箏計畫2.0」,至今已7年。受訪者蔡岳峰當時即擔任民和慈輝分校主任(2014-2018),兩年間與余浩瑋緊密合作。2022年重回主任職位,也將戲劇課程列入推行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