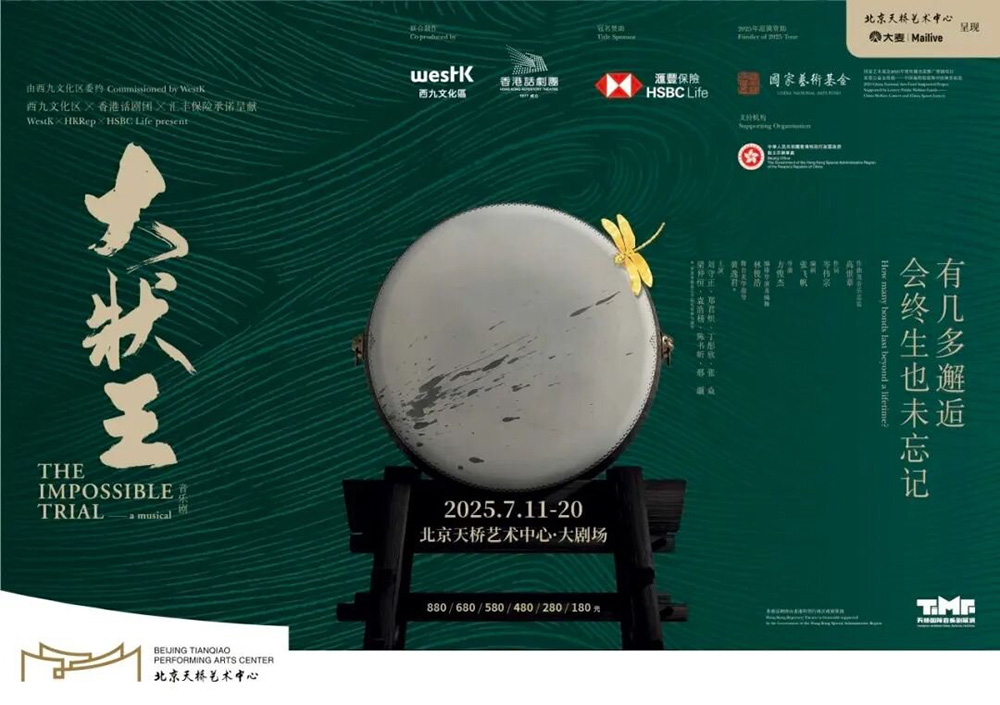2月下旬,北京專做雜技表演、1300座的朝陽劇場推出兩場「脫口秀之夜」,門票秒殺,脫口秀受歡迎的程度已從它的秀場滿溢到不同的劇場了。開年以來的兩個月,北京脫口秀演出超過3400場,占商業演出約43%。如果再討論「脫口秀是不是表演藝術」這個問題,很快地沒進過劇場的年輕人可能都會認為劇場就是演脫口秀的。就像10多年前,很多想投資話劇(舞台劇)的人以為話劇就是開心麻花。與此同時,北京首批25處掛牌的演藝新空間在這個農曆新年期間也貢獻了500多場次的演出,包括正乙祠古戲樓的經典戲曲,三里屯愛樂匯藝術空間,七七劇場的沉浸式懸疑劇等等。脫口秀與演藝新空間代表著北京的表演藝術日益多元化,但也代表著娛樂化表演需求日殷,勢不可擋。另一個史無前例的數字也令許多人驚嘆,2024年北京國家大劇院與天橋藝術中心票房收入雙雙破兩億人民幣,領先全國所有大型劇院。劇院努力往市場營運的道上奔跑。
表演藝術的內容娛樂化、受眾年輕化與劇院營運市場化在表面上看來對表演藝術產業似乎是正面的,因為統計數字每年都是增長的。但是,如果把表演藝術僅僅視為娛樂產業的話,最終這個社會將失去支撐人們對這個世界思考與反省的文化底蘊。藝術仍應該在不同的時代發出不同的聲音,發出自己的聲音,而要做到這些,最重要的就是藝術創作的原創力,也就是有好內容的作品。在北京其實並不缺乏編劇人才的孵化計畫,但大多是為了公部門的文化成績單,形式為上,真正純粹為拓展藝術創作力設想的計畫少之又少。值得慶幸,也很自然的是,大河中總有那麼幾隻小魚逆流而上,在這個講究商業模式與營銷策略的氛圍裡,仍有人關注著藝術本質的原創力,以孵化原創劇本為職志的「聲囂」(Sound & Fury)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