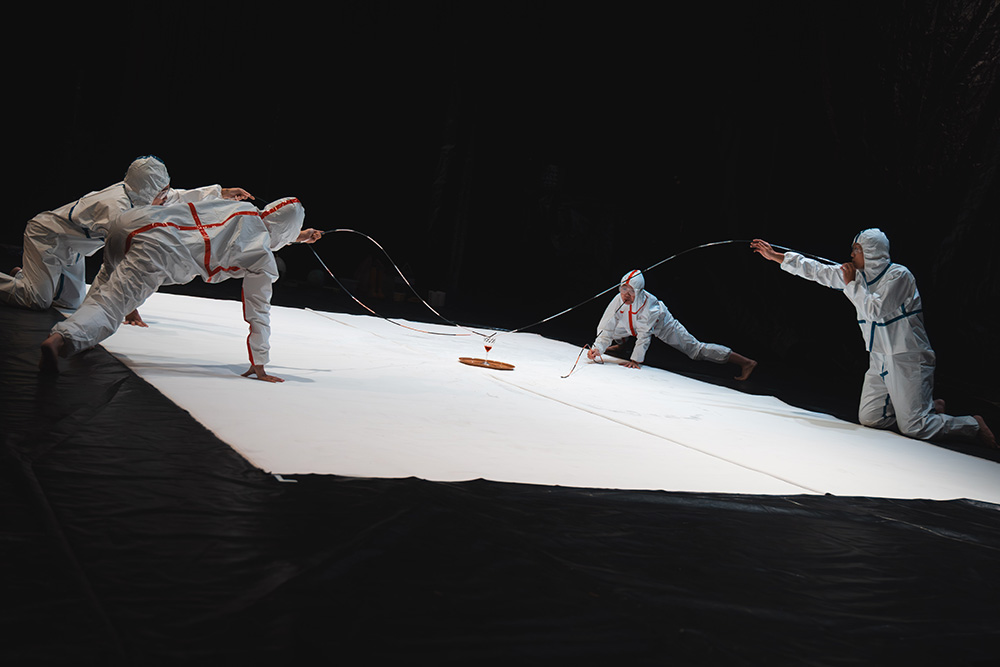馬里奧.貝努西的創作起點
今年27歲,1998年生於阿爾巴尼亞,五歲後移居希臘,2020年畢業於雅典音樂學院戲劇系(the Drama School of the Athens Conservatoire)導演馬里奧.貝努西(Mario Banushi),畢業後隨即以首部作品《妊娠紋》(Ragada)受到矚目,以母親為主角的初試啼聲,一方面讓他得到由希臘國家劇院委託製作第二部曲《再見,琳蒂塔》(Goodbye, Lindita)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奠定了他在包含第三部曲的《仁慈小酒館》(Taverna Miresia:Mario, Bella, Anastasia)的「親情三部曲」)(Romance Familiare),以他成長過程中圍繞在他身邊的女性,處理記憶與親情的母題。
其二部曲《再見,琳蒂塔》獲得塞爾維亞的貝爾格萊德戲劇節BITEF(Belgrade International Theater Festival)特別獎,評審盛讚作品交織於「生命與死亡、社群與獨處,以及世俗與崇高」之間。《仁慈小酒館》以同樣的美學手法,場上在不換景的視覺前提下,設定於四面無窗的浴室,場景在極寫實現場發生,例如浴室中再正常不過的淋浴,卻在敘事行進中,開始疊加出各種或以經驗、或是幻象的其他記憶從縫隙流竄出來,開始充滿空間,也重組浴室空間。眼前仍是浴室的場景,毫無違和地成為送別父親的哀悼之地、成為每一位親族成員最私密的悔恨告解處,也同時是親屬關係中最無法言語、也最不堪面對的衝突角落,每個人在獨處/共處的同一個空間裡,無力招架地接受所有的情願與不情願,進入彼此,再到最後以某種儀式性轉場,打開了也撫平了創傷的缺口。於是原本看似完整支撐、內縮與密不透風的空間,同步地在剝離、揭露、瓦解,不只前者的表象由後者同步構成,任何角色外在上的堅強也由種種脆弱拼組,貝努西毫無畏懼地將寫實主義推至盡頭,顯露其形式本體原初的荒蕪與最終必然觸及的綺想。也就是說,對我而言,與其說貝努西的美學交織於「生命與死亡、社群與獨處、世俗與崇高之間」,毋寧是透過識別前者單方面的限制,而推導至後者的共同現身。就形式上言,《仁慈小酒館》宛如遊走於寫實表演與身體劇場之間,但無疑地,這是一齣徹頭徹尾的寫實表演,只是導演以對親情極致的推敲與扣問,竟以一齣戲鍛鍊、穿透了一百年多年來現代戲劇的(寫實)劇場性,凸顯了附著於寫實上的種種無法再現。

在無法言說之中聽見聲音
寫實之內/外的無法再現,同樣也呈現在《仁慈小酒館》對語言的配置上。這是一齣完全透過角色進行任何語言對白的演出,但演出卻不是沒有語言的構成。從一開場大量的訊息播報,到後來大段吟唱所支撐的音場中,演出完不是不使用語言,或是避開了對語言的需求;相反地,這一齣以極寫實呈現的表演,所指向的語言形式是:所有的角色都充滿語言,卻實則無法言說的處境。
《仁慈小酒館》以缺席的父親鍊結了每一位登場的角色,以唯一的男性(可能是兒子)為敘述視角,開啟了可能是祖母、母親、姐姐、妹妹、姑姑等家族的女性群體與父親與彼此間的相互關係。雖然以已逝的父親為題,但演出反過來仍以悼亡者的現存親族女性成員為景,在看似封閉的、巨大的哀悼中,在彷彿不可回返的記憶中,一步步迎向後續可能的和解與救贖。從私我的浴室,疊加出父親生前所擁有的小酒館之於眾人,暗示了從個人到社群的生命交集,讓演出充滿張力,從原本以為的向內挖掘的個人創傷,不斷蔓生至雙人、三人、眾人間的集體經歷,也因此召喚了觀眾自身的共情。但我認為單純以這樣的閱讀,理解貝努西初試啼聲即獲得極大迴響的原因,遠不僅如此。古往今來的創作者無不處理所謂普世間的共性,如:悲傷、正義、背叛、親情、愛情……,但不是會觸碰到這些共性就能成為好作品。因為巨大的悲傷不僅僅是個人的或是家族的,而是歷史當下時刻的;任何一部歸結於上述情感或價值敘述的普遍性,實則都是在特定的、細緻的現實物質條件上,所得以提煉出的情動力,也是因為如此,真正打動現場觀眾的,不是我們以為的人性的悲傷、不見得是上帝的救贖、不一定是無可取代的親情…,可能是因為共時性地體會了這個共享歷史當下的經驗。

阿爾巴尼亞內亂到移民創傷
文初已經提到貝努西出生於1998年,正是1997年一場趨近國家崩潰的阿爾巴尼亞內亂/戰(civil unrest)後一年,父親的缺席,以及其之於眾角色間(劇中)未明的糾葛與張力,或許可以從歷史所共同結構的情感窺得一二。冷戰結束、蘇聯瓦解,1990年代初,阿爾巴尼亞從原先的社會主義體制轉向市場經濟與民主化,但這一看似世界(資本)自由主義陣營的轉型,以理所當然之姿席捲前第二世界,卻提供了所謂第一世界的各種資本「自由地」結合在地政治寡頭或圈地或設計,在金融監管機制薄弱,在地政府缺乏相對完善的制度與法制條件下,肆意發展。1991 年起,阿爾巴尼亞出現大量「金字塔式/龐氏式投資計畫」(pyramid scheme)——以高利率為誘因,吸引民眾把錢投入。這些以自由經濟為名的投資計畫,到1997年初,估計有近2/3的阿爾巴尼亞家庭因這類金字塔計畫而把資金投入;在種種監管缺失、政府默許、參與的金融組織與銀行能力薄弱下,最終在1997年崩潰(解嚴後的臺灣其實經歷過幾乎一模一樣的事件)。事件導致群眾包圍、攻擊政府、警察機構,軍火庫也遭到洗劫,政府喪失控制、武裝群體廣泛活動、整體社會秩序崩解,造成2000人以上的死亡,大量移民與難民流向義大利與南歐。貝努西的父母親與親族或許就參與了這段歷史,貝努西曾提及:「我的父母相遇時住在阿爾巴尼亞,他們相愛,然後離開阿爾巴尼亞。那些年,在阿爾巴尼亞,戀愛並不容易。不是說『我要他』或是『我要她』、『我們彼此需要』,這麼簡單就可以。所以當邊界重新開放,他們離開阿爾巴尼亞,從阿爾巴尼亞走路到希臘。花了很多天。最終,他們以移民者的身分,抵達希臘。」(據google地圖顯示,從他們原先居住的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Tiranë至希臘雅典Athens的距離是655公里,不眠不休的步行時間是6.3天。)
公主與王子的故事結局並沒有停在抵達希臘。貝努西的父母離婚之後,在他出生前,父親又回到阿爾巴尼亞,之後貝努西由祖母扶養照顧,直到五歲半;然後他又回到希臘與母親和姐姐同住。貝努西在希臘成為「新住民二代」,也同樣遭遇了偏見與污名化;「我同時長成了阿爾巴尼亞人與希臘人,但僅作為其中一個國家的人,我都同樣覺得被撕裂。」《仁慈小酒館》是以一個成長中缺席的父親,卻在葬禮上相聚的家族故事,但說出的不僅僅是貝努西父母親的分離,而更是冷戰後一個原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被所謂以自由世界為名的未來掠奪,同時因現代世界以民族國家為唯一秩序而撕裂的當代故事。《仁慈小酒館》不只是阿爾巴尼亞的故事,也不能只是被看作是一位阿爾巴尼亞裔希臘導演呈現的阿爾巴尼亞文化、民謠、傳說或南歐情調的奇幻劇場。

不是一個樣子,是很多樣子
如果再進一步延伸,我們也會發現冷戰後的巴爾幹半島上,從1992年波士尼亞內戰爆發(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在戰爭期間前往塞拉耶佛,導演《等待果陀》),1998年科索沃危機,科索沃境內的阿爾巴尼亞族與塞爾維亞族衝突下,北約轟炸南斯拉夫。隔年,美國B-2轟炸機在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期間,向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投擲了炸彈。撕裂的阿爾巴尼亞、消失的南斯拉夫、衝突的巴爾幹半島…,一路全景描繪了今日世界。從製作而首演《仁慈小酒館》的雅典艾比達羅斯藝術節出發,使得「劇場」標誌了一個新的認識論,認識文化與藝術的起點。正是透過劇場,以觀眾的情動與共感,重新回溯並加入了世界移民者在遷徙,與遷徙之後無終點的撕裂旅程;儘管是阿爾巴尼亞的移民,位於希臘中心的雅典沒有、也無法置身事外。事實上,《仁慈小酒館》有多少臺灣的樣子。
“The Balkans aren’t just one thing; they’re many things.”(巴爾幹人不是一個樣子,是很多樣子)貝努西曾經在一場訪問中回答提問他如何處理作品中的巴爾幹,貝努西覺得自己是巴爾幹的一分子嗎?他提供上述的回答。我想借用這句話,結束這篇我透過提早認識《仁慈小酒館》,想分享給台灣觀眾的文章。《仁慈小酒館》不是一個樣子,是很多樣子。
(轉載自國家兩廳院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