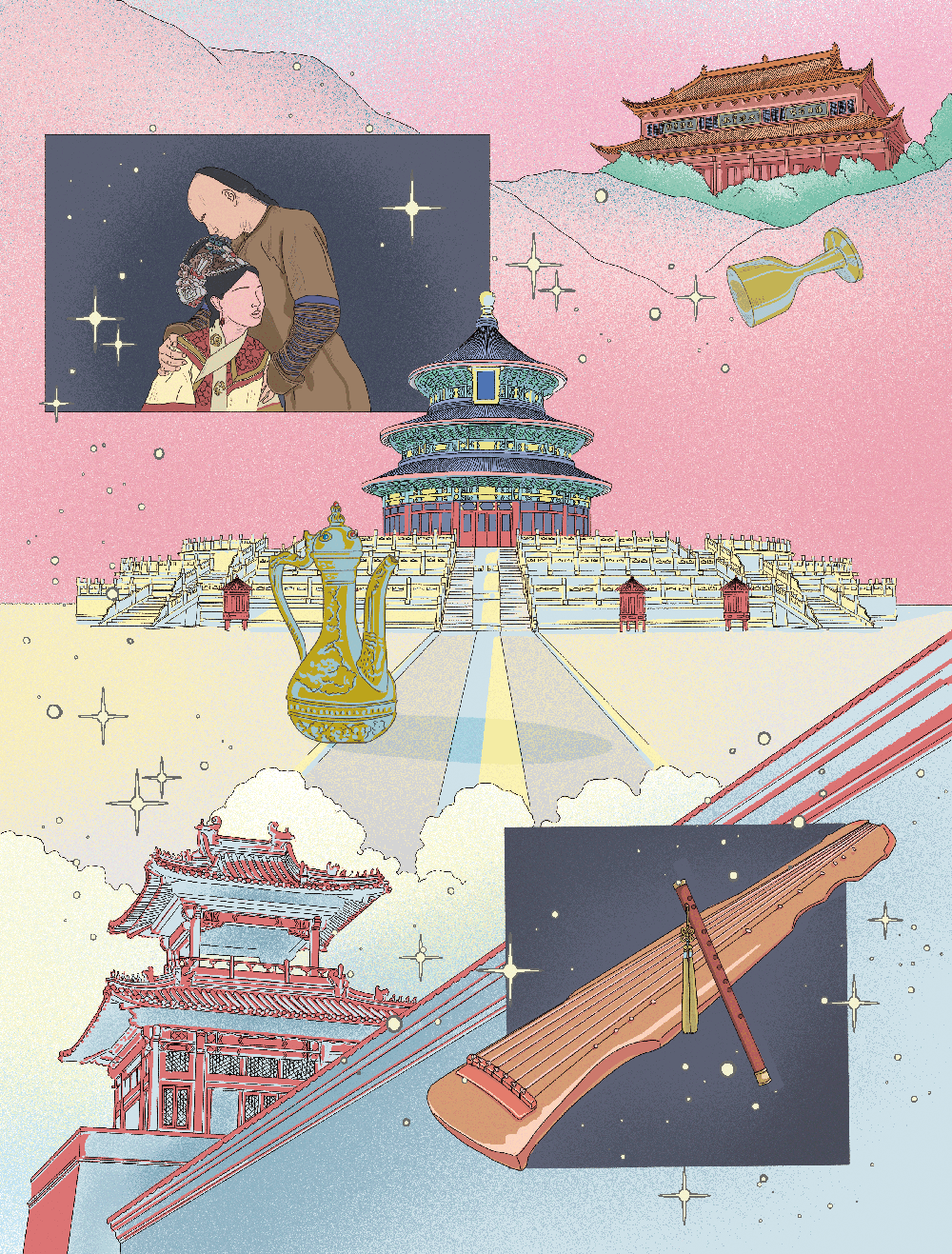Q2:補助再高,終究會有上限。但,這次將用更天馬行空的想像:3位非傳統戲曲出身的青年劇場創作者,以「經費無上限」作為基礎,提出他們各自的歌仔戲創作提案。
近年我參與了兩檔以「人間到地獄」為題的作品,分別是2021年與景勝戲劇團合作的《擺渡.戲夢》,以及2025年與遊戲團合作的採茶戲《閻羅殿AI手冊》。這兩部作品的角色徘徊在陰陽交界之間。在創作過程中,我面臨一個問題——如何在舞台上具象化「地獄」?為什麼我們需要具象化「地獄」?
從「還原」到「轉化」
我在美術班受過長期的視覺訓練,素描、油畫與攝影的「寫真」邏輯,建立在還原現實的慾望上——把一顆蘋果畫得像蘋果,讓觀看能夠立刻辨識對象。
然而進入劇場後,我被另一種表演邏輯吸引。戲曲演員只需一把馬鞭,就能讓觀眾感受到駿馬奔馳;演員一轉身,便能跨越空間與時間。觀眾透過身段、節奏與象徵去補全真實,這樣的「擬態」之美,讓我深刻感受到觀眾的想像力也是創作的一部分。從那時起,我開始思考:舞台的任務不只是還原,而是轉化。
選擇舞台展演的形式
當預算無上限時,如何選擇舞台展演的形式與必要性,反而成為最關鍵的課題。在資源極度豐盛的情況下,如何仍保有敘事的核心與觀看的焦點,是創作者最大的挑戰。
我很喜歡英國舞台設計師Leslie Travers的歌劇設計。他擅長放大必要的視覺元素,例如巨大的雕像或手的意象,使舞台設計具象出「命運」,讓我們看見一個小人物在無形力量之中掙扎、抵抗的空間。這種以簡馭繁的語言,讓空間本身就具有敘事功能。
同樣地,我也受到羅伯.威爾森(Robert Wilson)《歐蘭朵》(Orlando)的啟發。他以光、聲與動作構築出延展的詩意節奏,讓觀眾在極簡的畫面中,專注於表演者的聲音與身體。
我也喜歡日本劇團☆新感線的《骷髏城之七人》。那是另一種極致的戲劇能量——歌舞伎的繁華與暴烈,將節奏推向極限。那種「熱鬧」不只是視覺上的,而是一種生命力的爆發。
我一直喜歡戲曲裡的鑼鼓與節奏,特別是武打片段。那是一種由表演者的身體與樂師的聲音共同創造的張力,既具形式的美感,又蘊含生命的韻律。或許我追尋的,不是「地獄」的具象,而是那股節奏——一種在聲段與身段之間流動的能量,讓觀眾在想像與現實之間,感受到生的狂熱與死的靜止。
這3種力量——構成了我對未來歌仔戲的想像:在極簡與繁華之間、在光與呼吸之間,讓觀眾不只是「看戲」,而是進入一場關於聲音與身體的感官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