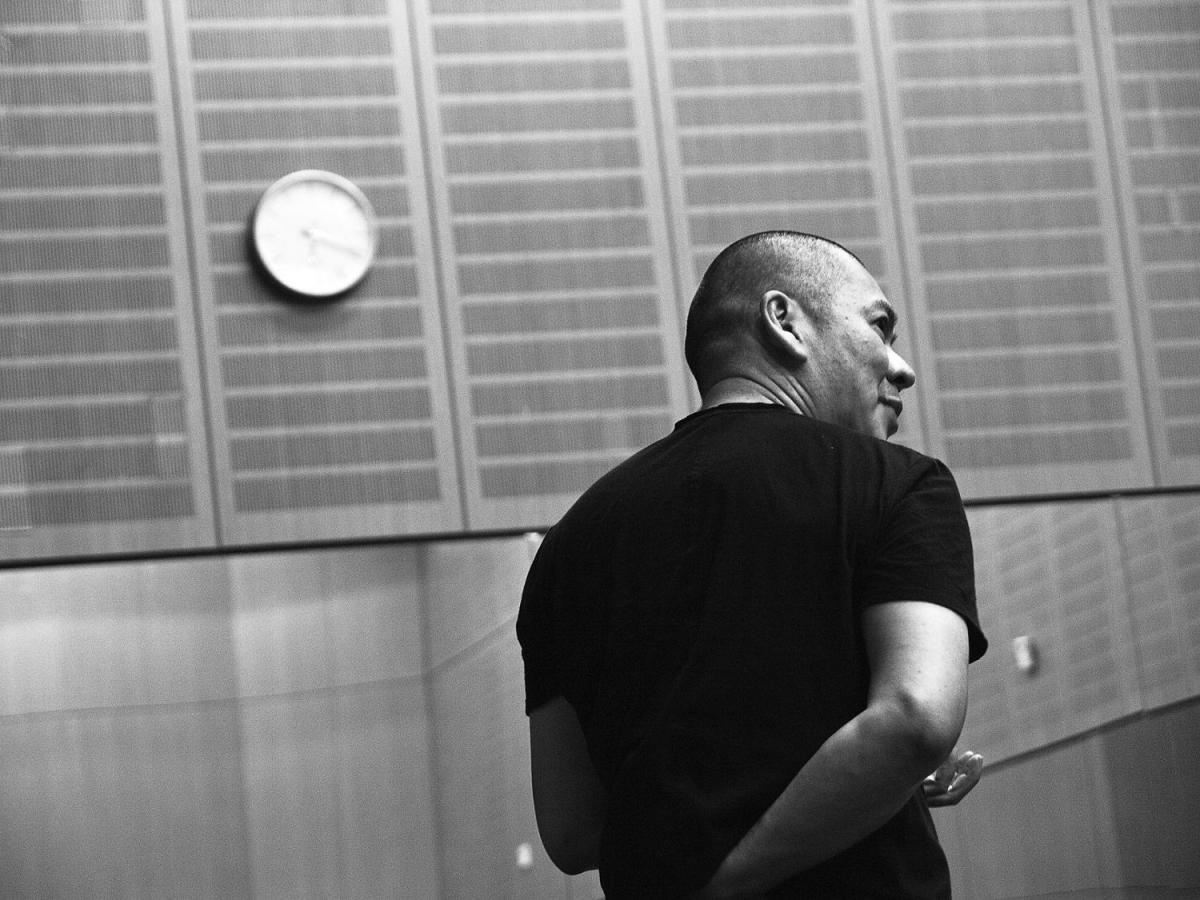鄒欣寧
-
舞蹈新訊 8213肢體舞蹈劇場新作
《極境之旅》 描繪世界巨變後的樣貌
生活在廿一世紀,面對種種末世預言,可能想過,若「極境」不再只是遠在天邊的南北極地,而是明天過後你我置身其間的生存場景,我們將如何面對?生態變遷、氣候異變不只是影像創作或科學研究的題材,更是我們實際遭逢的環境問題,我們的每日生活都是造成這些劇變的小小推手,那麼,我們該繼續無所自覺地走向可能的文明終結,或是下定決心、著手改變? 8213肢體舞蹈劇場年度演出《極境之旅》便從此一議題出發,由曾獲台灣「舞躍大地年度大獎」的美籍編舞家Casey Avaunt編創,與資深音樂人陳世興一同就末日情景發想,更邀請來自美國科羅拉多學院的喬登.布魯克斯(Jordan Brooks)及馬來西亞籍的林志駿等七位舞者,以跨國多樣的肢體和音樂風格,表達創作者想像中世界經歷巨變後的樣貌,呈現出當地球的四季不再是四季,文明不再進步,大自然被人性的貪婪、食慾、懶惰、功名汙染,人類該如何展開更艱鉅的極境生活?
-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或性感或炫技 普羅大眾愛舞「瘋」!
以流行音樂入舞,是大眾最熟悉的歌舞形式。從最早隨電影流行的社交舞,到七、八○年代,透過余光主持的「閃亮的節奏」傳至台灣的西洋流行舞曲,帶動最早的街舞熱潮,因應「勁歌」而生的「熱舞」,構成一般人對舞蹈的主要印象。我們忍不住要問,流行歌舞為何吸引普羅大眾?怎樣的流行音樂會促動人們起舞、如何起舞?流行歌舞和劇院殿堂的舞蹈,真的只能「河水不犯井水」嗎?
-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當嫻雅舞者和狂野熟女相遇……
周章佞 ×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
火紅削肩拖尾長禮服襯出她高貴而優雅的氣質,一舉手、一扭腰,裙襬即隨著跳躍的身體在台上飛揚,轉身成了風情萬種的女伶,瞬間點燃滿腔熱情,她是雲門舞集資深舞者周章佞。從令人著迷的《九歌》湘夫人、《白蛇傳》的白蛇到《行草》的「永字八法」,周章佞以身體律動表現了專注、連貫、停頓與力道,令人驚豔。這次,雲門以十八首流行歌曲入舞的《如果沒有你》,周章佞將以一曲獨舞〈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展現熟齡內斂卻澎湃的情感。
-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佐著流行曲 對鏡子起舞
因為一次在洗澡時哼起白光的〈如果沒有你〉,讓林懷民靈感一動何不拿流行歌編舞?於是過去不強調個人特質的雲門舞者,在新作《如果沒有你》穿上花花衣裳,在流行歌中獨自或雙人起舞,身體質地或仍延續過去,這回卻要跳出屬於自己的新顏色、新表情。
-
即將上場 Preview 新人新視野—舞蹈篇
「女流」當家 譜寫舞蹈新貌
今年的新人新視野舞蹈篇,非常女性!集結了董怡芬、林祐如、余彥芳、林宜瑾四位舞蹈女將,都是近兩年內南征北討、或編或舞的年輕新勢力,這股「女流」將在實驗劇場匯聚出怎樣的舞蹈地貌?如何以創作提出年度總結?令人引領期待。
-
即將上場 Preview 驫舞劇場 & Volume-Collectif
《繼承者》 面對浩瀚的進退冒險
面對一片無涯浩瀚,人行至此,何以為繼?由這樣的一幅畫《霧海上的流浪者》引發,驫舞劇場展開了新的冒險十一月份演出的製作《繼承者》,以連續三週、但週週不同的表演,透過提問、追溯、瞻望,繞著「繼承」的主題各自表述。
-
節目掃描 Performance schedule 廖末喜舞蹈劇場
舞詩不絕 《飄》再現經典
在南台灣持續經營文學與舞蹈相遇創作的廖末喜舞蹈劇場,自二○○二年推出第一部舞詩作品《台灣詩歌的舞蹈漫步》後,每年亦以穩定頻率推出系列作品,並邀請不同編舞家以南台灣詩人創作進行舞蹈編製,近年並獲得李敏勇、利玉芳等詩人對於文學題材的啟發,從而使舞蹈與文學、詩結合的製作展演形態更趨完整。○八年起更與崑山科技大學藝文產業創新育成中心透過產官學的合作,將詩、舞、樂結合影像科技呈現,賦予舞詩不同的面貌。 今年,舞團延續去年將既往舞詩系列選粹演出,再次從歷年經典舞作中精選四首作品《飄》(陳秀喜詩作/蔡秀貞編舞)、《三位一體》(李魁賢詩作/賴翠霜編舞)、《向婆嚎海》(利玉芳詩作/卓庭竹編舞)及《小鬼湖之戀》(魯凱族傳說/胡民山編舞),以情愛為主軸,體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環境間面貌迥異而濃烈的情感。舞作加上視覺藝術、影像科技等創新元素再製改編,延伸創作思維的廣度之餘,也讓當代科技賦予作品新風情。
-
編輯精選 PAR Choice
體驗「即興」冒險 看一場表演「球賽」
將「接觸即興」舞蹈引入台灣的編舞家古名伸,以盛大舉辦的「第一屆國際愛跳舞即興節」紀念自己步入即興的廿虛歲。即興,是表演者不預做編排地在觀眾面前一邊創作、一邊演出,觀眾與表演者一同在表演空間內創造一趟冒險意味的旅程,好比觀看一場球賽。這次的盛會以「流水席」、「大匯演」、主秀「即興舞蹈的光譜」等形式,邀請國內外團隊參與,要讓觀眾親自體驗即興演出的精采多樣。
-
特別企畫 Feature 專訪《只有你》導演
蔡明亮:既然敢邀請我,我就不會客氣
蔡明亮的影像作品以「慢」著稱,工作起來也有著不畏與時間對峙的耐性。這次一口氣執導《只有你》三齣戲,早在半年前就和楊貴媚、李康生、陸弈靜三位演員展開工作。最初聊天漫談,從各自生活中兜成戲的血肉,進劇場後發展出三種不同風味的獨角戲,大為顛覆人們對「獨角戲」看演員詮釋角色、炫示演技的印象。 近幾個月天天進劇場,從下午排到晚上,好不容易抓出時間受訪,蔡明亮一邊用餐,臉上有輕微的倦意,但說起創作衝撞限制之必要,他目光炯炯,坦然直言:「拍電影或劇場都好,既然敢邀請我,我就不會客氣。」 對劇場怎麼個不客氣法?讓演員在台上沉睡可能是其中一種,但為什麼這麼做?蔡明亮眼中的劇場和獨角戲還有哪些可能性?以下是他的現身說法。
-
特別企畫 Feature
穿過螢幕走進他的電影裡——楊貴媚
「燈暗。」算是喊卡了。導演笑著走向慢慢從地上直起身的女演員:「媚,今天前面的節奏非常好」 說著,轉身向我們,像孩子剛順利穿越馬拉松終點而興高采烈的母親:「才剛拿到詞,她好快!」
-
藝活誌 Behind Curtain
工作狂男孩 魏雋展
他可能不是太同意這標題。倒不是工作狂的緣故。 採訪後的某一天和他再見面,我跟他說,你這過日子法,看起來簡直是工作狂。他笑了。 劇場工作狂的必要條件,首先是多重角色扮演,其次是行事曆的空格永遠滿得像快完成的數獨或填字遊戲。 演員魏雋展的工作行程目前排到明年後。剛拍完一支廣告和電視劇,緊接著是十一月和驫舞劇場合作的《繼承者》,十二月則跟無獨有偶劇團的《剪紙人》全台巡演。 導演魏雋展上半年交出了入圍台新藝術獎提名的《耳背上的印記》,十月在牯嶺街小劇場上演的《男孩》,是去年同樣入圍台新獎的《偶戲練習:男孩》重演。 「三缺一劇團」的魏雋展,作為核心團員和主導者,也在對外舉辦的工作坊擔任講師。結束了默啞劇工作坊後,他和團員隨即重排《男孩》;明年的演出計畫《LAB壹號》也已開始發展。 面對這有如板塊持續推擠運動的時程表,他以不變應萬變,讓生活維持得穩定而秩序。這個部分的魏雋展很不男孩,我突然想起幾個劇場朋友開玩笑叫他「阿北」他是那種進劇場後,會找個角落安安靜靜練太極拳的演員。 男孩魏雋展,每日恆常練身體練聲音,吃喝簡單不挑剔,一說話,他獨角戲裡彷彿莎哈札德的說書人躍然成形。男孩作完一齣關於男孩的戲,說是男人了,但我更覺他該變成的,是一隻豹童年時,他總幻想一隻和自己同行的豹,保護他又叫他著迷。或許那才是他真正該成為的模樣。
-
節目掃描 Performance schedule 肢體音符舞團 混搭民俗與詩意
《七里香》 舞出夜市人生
「七里香,既是周杰倫的歌,夜市中賣的炭烤雞屁股,開白花結紅果的小盆栽,也是作家席慕蓉的詩(集)。」 這個舞作說明,開宗明義點出了肢體音符舞團最新的年度公演,有著濃濃的混搭氣息流行樂和常民生活的氛圍中,抹上一點淡淡的詩意和植物馨香,也為向來著重古典與傳統的舞團風格,渲染出五光十色的日常感和現代性。一直以來,肢體音符舞團的作品多從傳統樂舞或民間文化中汲取養分和創作靈感,此次邀請三位卅世代的年輕舞蹈創作者 許瑋玲、林春輝及彭惠君共同創作《七里香》,各自展開舞蹈與典型台灣生活風格夜市的對話。 高中畢業後隻身赴澳洲習舞的彭惠君,以 「夜市」這個連外國人也著迷不已的台灣文化為創作命題,選擇夜市中常見的彈珠檯遊戲,趣味呈現「人生有如彈出的彈珠,不知去向何處」的隱喻;「2011國 際青春編舞營」台灣代表的林春輝則藉由夜市常見的買賣、攤販與警察間你追我跑的景觀,表現不同的人性面貌;仍在學的許瑋玲,以一曲流行歌,舞出夜市中一桌 二椅的種種故事,奇想和取材大眾的角度,也讓肢體音符的新作品,開拓出不同以往的年輕氣象。
-
特別企畫 Feature
性感舞步間 揮灑戲劇張力
創立於一九七八年的西班牙國家舞團,有「西班牙文化大使」之稱,這次來台將演出《佛朗明哥傳奇》與《杜阿利亞舞》兩支舞碼。前者旨在向佛朗明哥傳奇女舞者阿瑪雅致敬,透過男女舞者的對峙和共舞,傳達阿瑪雅兩者兼備的表演魅力。後者則透過大量男女雙人舞,表現飽滿流動的熱情、慾望和生命力。
-
企畫特輯 Special
「桃園縣多功能展演中心」正式營運 讓航空國門之都與表演藝術相遇
人口逾兩百萬人的桃園縣,在民國百年升格為準直轄市後,已成為人口成長最快、也是僅次於新北市的全國第一大縣。容納國際機場和數十個工業區的桃園,近年也在藝文發展上急起直追,二○一○年,文建會補助的「桃園縣多功能展演中心」正式落成啟用,是繼文化局管轄的「桃園館演藝廳」和「中壢藝術館」後第三個藝文場館,無論是場館規模、硬體設備、座位數量上,桃園縣多功能展演中心都以超越前兩座的態勢,爭取全國乃至國際藝文團體的目光。 硬體設備佳 迎接多元展演 多功能展演中心在一年試營運後,歷經各項藝文活動與金馬獎頒獎典禮的籌辦,於今年正式營運。這座外觀呈現科技感的銀灰色建築為地上七層,其主體意象為一自地面盤旋上升的連續律動帷幕,隱喻以航空為發展基礎的城市性格。 此外,展演中心包括可容納一千五百四十八席次的多功能展演廳、錄音室、排練室、展覽空間與戶外展演舞台。更值得一提的是其硬體設備,除了挑高廿五公尺、十八平方公尺見方、側台及後台腹地深廣的展演廳舞台外,也配置了全台第二套電腦吊桿升降系統show motion,由電腦程式設定操作十五道吊桿,提供各類型的劇場和表演需求。 依據中心的遠景規畫,未來希望除了戲劇、音樂、展覽等藝文展演外,將這座多功能的展演空間發展為流行音樂中心和文化創意產業中心,辦理大型演唱會或國際性演出,吸納台灣北區的觀眾人口,以徹底落實這個一千五百席次大型場地的功能。 環境劇場打破空間 精采表演接力到十月 為了慶祝正式營運,桃園縣多功能展演中心也特地於夏日舉行一系列老少咸宜的劇場藝術推廣和演出活動。該系列以打破既定演出空間、表演可自由移動的「環境劇場」為主要概念,先於七月廿六日起一連十天舉行工作坊,廣邀劇場工作者彭雅玲、鴻鴻、王榮裕、郎亞玲、蔡柏璋等授課,帶領對表演藝術有興趣的參與者走進劇場、認識劇場。 自八月份起,更有聲動樂團、在地搖滾樂團、及德國triosence爵士三重奏與蕭煌奇、官靈芝跨界合作之「秋天聽見鄧雨賢」爵士音樂會、舞鈴劇場、當代傳奇劇場等不同領域的表演節目,一路接力聯演至十月。首先登場的是聲動
-
舞蹈新訊
年輕舞者登台競藝 雙舞盡展芭蕾風華
被譽為「台灣有史以來最好的芭蕾伶娜」的台北皇家芭蕾舞團團長吳青口岑,自高中赴美習舞,接受完整的西方舞蹈教育,亦多次在國際舞台上以優異演出獲 得好評。她返台後主持台北皇家芭蕾舞團,深感台灣芭蕾舞蹈人才的培育和登台機會艱困,從二○○九年夏天起,固定舉辦全國芭蕾舞大賽,以不同年齡層級的學生 為參賽對象,挑選經典獨舞片段競賽。 今年邁入第三屆的全國芭蕾舞大賽,將分兩天舉行初賽與決賽。承襲過往慣例,在芭蕾競賽之外,台北皇家芭蕾舞團亦將於決賽當天頒獎典禮後進行舞團公演,今年推出作品有《三部曲頌》與《日正當中》兩支,由藝術總監吳青口岑以拉赫瑪尼諾夫的Symphonic Dances, Op.45與柴科夫斯基The Dance of the Clowns等曲為靈感進行編創。前者依據舞者年齡的差異,在技巧、表現力呈現出循序漸進的層次;後者則隱伏舞劇的角色情境,卻不突顯敘事情節,形式上更近於現代芭蕾,充分展現了吳青口岑作為芭蕾教師與資深舞者對芭蕾技巧與大師音樂的理解力,也頗能反映舞團長期栽培舞者的成果。
-
舞蹈
極簡之中 舞動生命捲軸
「玫舞擊」藝術總監何曉玫再度發表的新作《紙境》,跳脫過去作品以台灣社會現象入題、拼貼、情感濃厚的風格,而以較純境簡約、跳脫敘事的抽象形式展現。舞台被紙包圍,舞者著白衣或黑衣,在如同捲軸的紙捲上,勾勒出無止無境的動態時空
-
舞蹈 舞蹈空間《風云》 楊銘隆又展「東風」
霸王別姬後 舞出歷史外的新選擇
睽違六年後,編舞家楊銘隆與舞蹈空間舞團的「東風系列」再度出手,與臺北市立國樂團合作,演出以「霸王別姬」故事為主題的新作《風云》。除了有北市國樂師與舞者的即興互動,還在原有的故事結局外,另外發展出楚霸王和虞姬的不同結局。
-
舞蹈 台北室內芭蕾舞團 經典在地新繹
余能盛版《吉賽兒》 鐵工廠的貧富之戀
台北室內芭蕾舞團藝術總監余能盛,今年別出心裁地改編法國經典浪漫芭蕾《吉賽兒》,將故事場景搬到台灣一座鐵工廠,四位主角化身成鐵工廠內各層階級,仍圍繞在因社會階級、貧富不均而發生的愛情悲劇,以及詮釋吉賽兒至死不渝的愛情。
-
舞蹈新訊 雞屎藤新民族舞團府城三部曲完結篇
「昭和摩登.府城戀歌」 老百貨公司中的懷舊戀曲
近年於台南持續耕耘在地民族舞蹈的雞屎藤新民族舞團,繼《臨水流殤婆姐、南音與藝妲》、《海安夢華錄那年,府城煙花燦爛》兩部以藝妲與府城老商業中心海安路為題材與背景的舞劇作品後,這支「庶民三部曲」系列的尾聲,搬演的是日治時期南台灣第一家百貨公司「林百貨」中售貨小姐的生活記憶與時代印象。舞作中充滿濃厚的日治時期氛圍,文夏、陳芬蘭等人演唱的台語歌謠,搭配日人移植西方的「摩登文明」:洋裝、美容等,打造出極為鮮活的舞台場景。 藝術總監許春香是資深民族舞蹈教師,致力於從受不同文化薰陶的台灣舞蹈中,提煉出屬於在地的民族舞蹈,府城歷史則是她最主要的取材來源。在《昭和摩登.府城戀歌》中,她以曾任林百貨電梯小姐的母親之戀愛故事為藍本,從電梯小姐每日的工作動作中汲取、發展出肢體語彙,同時走訪地方耆老,取得大量資料,揉合編創成這齣府城摩登文明史的舞蹈作品。台南場更選在歷史悠久的「全美戲院」演出,增添不少懷舊風情。
-
舞蹈新訊
再現嬰兒油之舞 光環《陂塘》舞動池中生機
提到光環舞集,多數人不約而同浮現的印象正是舞者周身沾染嬰兒油,在油光與汗水之間進行各式翻滾堆疊的動作。藝術總監劉紹爐從早年「氣、身、心合一」的肢體概念,發展出獨特的嬰兒油劇場,取材上則歷經鄉土與人體脈輪潛能探索等階段,近年更自客家文化與劉紹爐在新竹縣客家村成長的個人經驗著手,編創《山歌踏舞》、《身音body sound》等作。 此次推出的年度公演作品,延續客家系列,將舞台上的嬰兒油風景轉化為月光下的客家陂塘農家灌溉用的池塘,本就充滿了形形色色生物鳴叫浮游的生態風景,而油亮的舞者們時而幻化為池塘中的水生植物,時而是匍伏於自然天地間的戰士,在肢體與聲音的流動間,貝多芬《第五號鋼琴協奏曲》扮演提點的角色,呈現出客家農莊風景的恬靜與生機之際,亦展現了走入熟成期的舞團表演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