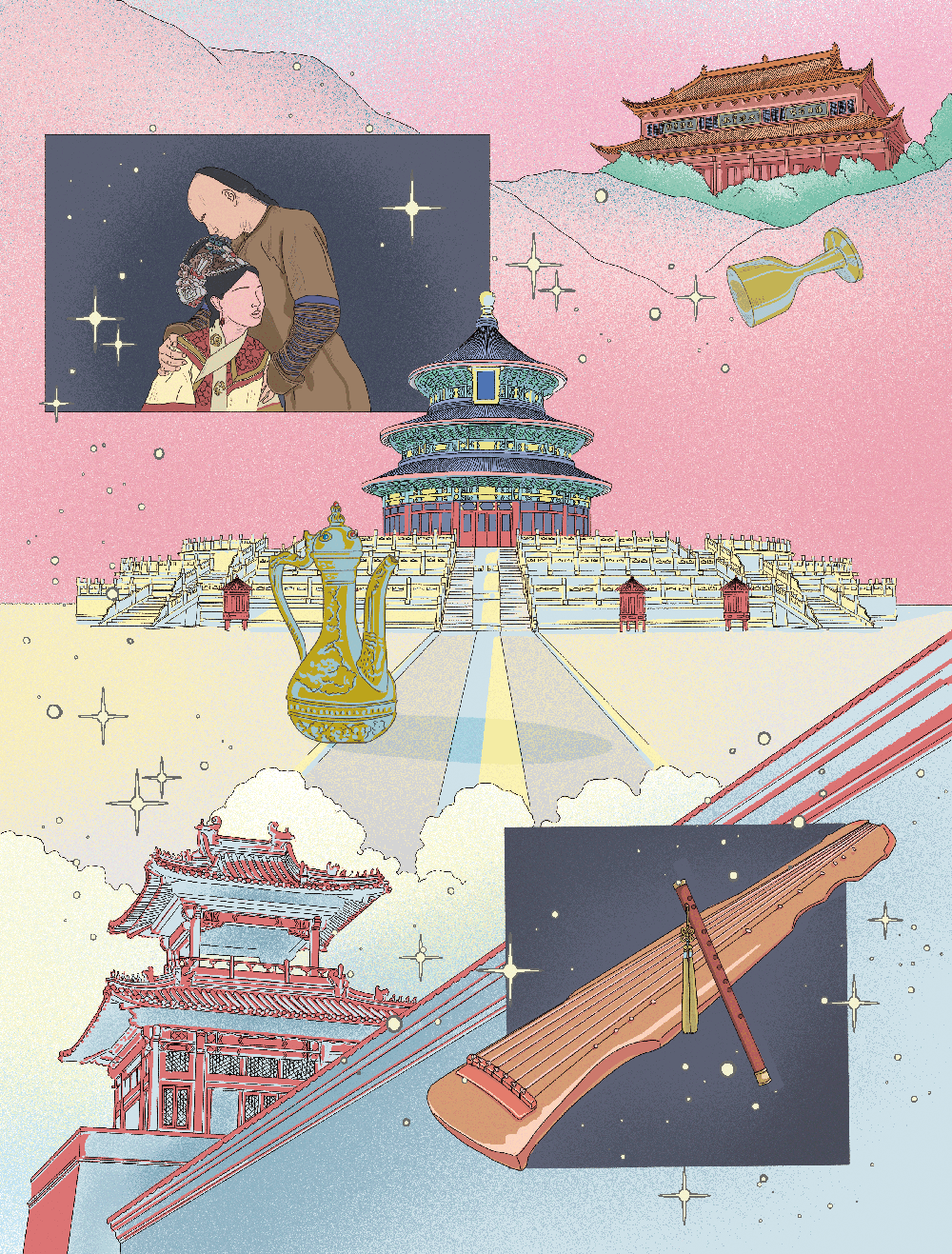面對一片無涯浩瀚,人行至此,何以為繼?由這樣的一幅畫《霧海上的流浪者》引發,驫舞劇場展開了新的冒險——十一月份演出的製作《繼承者》,以連續三週、但週週不同的表演,透過提問、追溯、瞻望,繞著「繼承」的主題各自表述。
法國聲音團隊Volume-Collectif x 驫舞劇場
《繼承者Ⅰ》
11/10~13 19:30
《繼承者Ⅱ》
11/17~20 19:30
《繼承者Ⅲ》
11/24~27 19:30 台北 華山1914文創園區東二館
INFO 02-29674495
讓我們從一幅畫說起。一八一八年,德國浪漫派畫家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繪製了《霧海上的流浪者》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畫中,一個成年男子背對觀畫者,高踞於岩崖之上。在他面前是浩瀚的山巔雲海,虛渺、龐大的雲霧,從他眼前一路綿延至廣遼的天際。
在他身後的我們,無從得知他以何種神情面對眼前驚人的遼闊,卻被這幅畫喚出心中的震懾。那是人置身於龐大物事之下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感到自身渺小,彷彿隨時會被無邊吞噬,泛起一股恐懼;另一方面又情願臣服於這片大,當它收攏包圍自己,平和與寧靜油然而生。
有些人可能會浮現另種猶疑:見識了這般懾人的景致,豈能掉頭回歸原處?
這是臨崖的召喚,驚奇的冒險。驫舞劇場藝術總監陳武康和團長蘇威嘉,就在這召喚之下,邀集周書毅、魏雋展、王靖惇、Shai Tamir等表演者,與聲響藝術工作者澎葉生(Yannick Dauby)、蔡宛璇、法國團隊Volume-Collectif等,展開一場浩大費時的冒險,他們把這場表演的臨崖體驗,命名為「繼承者」。
三週三部曲 主題「繼承」內容不同
陳武康描述,《霧海上的流浪者》帶給他最大的思考,在於「態度」:「站在懸崖邊看前方的海,有點像是未來,大師們給你的養分和靈感,只能帶你到岸邊,接下來呢?要往前還是往後?」
「我自己想往前。」陳武康肯定道。但邁步之前,檢視自己作為繼承者究竟繼承了什麼,是必要的。也因此,《繼承者》連續三週的展演內容全然不同,在不同的時間脈絡下,透過提問、追溯、瞻望,繞著「繼承」的主題各自表述。
「我們的身上都繼承了很多東西,但未必意識到。我感覺繼承者很慘,因為不知道自己被什麼影響,也無法決定下一步要去哪裡,只能照著自己現在的模樣繼續走下去……」蘇威嘉看待繼承者傾向悲觀,個人的渺小、孤單,不只映現於時間的洪流中,也與《霧海上的流浪者》中人和空間的對比緊密呼應。
因此,在非劇場的巨型空間表演成為必然。蘇威嘉與陳武康不約而同回憶起,到華山探勘場地時,看著周書毅在偌大的烏梅酒廠中跳舞,如此孤寂、無助,「卻又安全」,陳武康說。而蘇威嘉形容:「這麼大空間放一個人在那邊,本身就動人。」
時空架構確認後,回到表演的編排。第一週著重「提問」:「我繼承了什麼?」,將近十位表演者在酒廠不同角落同時起舞,用身體彰顯問題,尋找答案。觀眾沒有固定的觀賞座位,可隨意遊走,自行選擇觀看對象和內容,「比如書毅在我面前跳,後來他走了,下一個人過來,這時我面臨一個抉擇:要看誰?跟著書毅走,或是留下來看眼前的人?」
第二週著重記憶的回溯,同樣是個人片段的呈現,展演空間則不同於第一週,被打造成宛如上古時期的洞穴,透過燈泡浮動隱約的光線,表演呈現出遠古壁畫般的質地,強化「觀看過去」的氛圍。
第三週,繼承者們在溯源之後,不免對身為渺小的個人感到「人生不過如此」的絕望。這週表演,觀眾將回到傳統坐在固定位子的觀賞,表演也從前兩週不同身體質地的摸索,轉而以舞蹈為主。「其實還是要走下去,不斷在路上找到值得留戀的片段。」陳武康為這趟為期三週的表演歷程,下了如是結論。
溝通一種「看的方法」
驫舞劇場對於《繼承者》設定的目標,不只是精神上的身世溯源之旅,更希望藉這場展演,對舞蹈結構、表演和觀看的關係提出更大膽的挑釁和質疑。
最明顯的首先是巨大而難以聚焦的空間,陳武康坦率地說:「如果我把力氣花在聚焦上,那在這個空間演出就沒有意義。」他解釋,不希望炫示舞蹈技巧,博取觀眾目光,而想透過跳舞去經歷、發現一些人生過程。
也因此,他不諱言當然可以聚焦畫面、營造意象,但那「太取巧」,他甚至以舊作《速度》的編排為例,「結構上百分之七十模仿Pina Bausch,遊戲、舞蹈、遊戲、舞蹈……可以讓觀眾看三個小時,時間很快過去,眼睛很舒服」,但重複前人形式,顯然不是驫舞繼續創作的理由。
「不可否認我們的表演tempo(節奏)會有點平,但我不想用戲劇效果吸引觀眾注意。我想擺脫那個,讓很多事情同時在場上發生,而觀眾要看到什麼故事,全憑他自己摸索。」陳武康說。
再好比音樂,驫舞自《骨》(2008)開始與澎葉生合作,之所以長期與專攻「聲響」而非「音樂」的澎葉生合作,「因為他的聲音會幫忙排除情緒,製造更多想像。」陳武康直言:「音樂會騙人。我們不要觀眾被音樂牽著走。」
他舉例,如果場上有兩個人互相推擠,配上琵雅芙(Édith Piaf)的香頌,可能就會製造出某種黑色喜劇的效果,那樣一來,觀眾很難留意推擠的細微動作,「就算舞者跳很爛、時間感跟音樂感都錯,還是會過關,觀眾就被音樂騙過了。」
此次澎葉生和Volume-Collectif的聽覺創作甚至不依循「繼承者」此一概念,而是運用各種空間聲響,加上蔡宛璇運用工業物件的空間裝置,從視覺與聽覺創造出異質感受。雖概念不同,表演者的演出內容卻能在「對位」的形式下,與聲音呼應不同的心理、關係,讓觀眾自行察覺箇中趣味。
陳武康坦承,自己看表演的習慣是「一旦看懂就不想看了」,「我想我們的責任是,努力去開發一些不同的形式,本來我們就不該造成觀眾太舒服的觀看過程。」
《繼承者》早前曾在花蓮舉行一場實驗中的呈現,名為「開拓者」。這個名稱或許更貼近他們對於自己的期許,眺望著無邊風景,向前走去,或許一條路,就這麼被他們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