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密歐與茱麗葉
-
 藝號人物 People 英國編舞家
藝號人物 People 英國編舞家馬修.伯恩 引爆青年震盪,讓經典活出當代模樣
劇院群聚的倫敦西區,英國編舞家馬修.伯恩(Matthew Bourne)的名字代表著驚喜。將經典芭蕾舞作賦予當代的改編與詮釋,是他獨樹一格且風靡西區的標誌。1995年他推出全男性芭蕾舞者版本《天鵝湖》(Swan Lake),天鵝成為充滿攻擊性的強壯生物,王子更愛上男天鵝,對比過往的柔情詮釋,柴科夫斯基的音樂在有力的肢體表演下展現全新風貌,隔年就獲得英國劇場奧利佛獎;兩年後前往紐約百老匯巡演,更獲得美國劇場界最高榮譽東尼獎導演與編舞的肯定,成為21世紀初的重要舞劇經典。 然而馬修並沒有在高峰停下腳步,而是放手展開一系列充滿野心與挑戰的創作,他成立的「新冒險舞團」至今已推出35部舞作,其中由馬修擔任導演與編舞的有13部,包括改編經典的《剪刀手愛德華》(Edward Scissorhands,2005)、《灰姑娘》(Cinderella,2010)、《睡美人》(Sleeping Beauty,2015)、《紅舞鞋》(The Red Shoes,2016)等,以及即將在今年巡演至亞洲的《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2019)。而集口碑與票房於一身的馬修,也在2016年獲英國皇室授予爵士的榮譽。 從小種下的創作啟蒙 1960年出生,成長於英國倫敦,裨益於地緣,馬修成長過程就常跟著父母造訪電影院和劇院,他回憶:「印象中他們沒有太多錢,所以我們總是坐在最頂層,最便宜的座位區。」然而馬修正式學舞的時間相對地晚,22歲才進入倫敦拉邦中心,畢業後跟著拉邦中心的過渡舞團(Transitions Dance Company)進行兩年的巡演。很多人以為他是先跳舞才編舞,其實不然,馬修早在5歲就開始頻繁參與社區、學校的大小演出,儘管沒有正式學過表演,但他從小就會試著用不同的方式處理演出,「換個方式試試看」的念頭可說是他編舞的啟蒙,過程中他也一路自學舞蹈,直到長大才正式進入學校學習。而父母為他培養的看戲興趣,則是他從小就身兼影迷、戲迷,最終更投入劇場工作的重要啟發。 隨著他為電視、劇院和其他舞團的編舞工作變多,表演次數減少,最終他在1986年創立公司開始個人創作。如今64歲的他,依舊充滿熱情地表示,這是他一直以來最喜歡做的事,未曾改變。
-
 戲劇
戲劇愛在戰火蔓延時
莎士比亞《羅密歐與茱麗葉》所描述的是年輕戀人間,5天短暫又純粹的愛情,快速燃燒得熾熱毫無保留,有如火樹銀花的煙火,在夜空中燦爛奪目,又隨及消逝。因此羅密歐與茱麗葉即使是悲劇,亦讓人感到就是在最美的時刻停止,永恆不渝的愛情才被完整保留下來。但如果羅密歐與茱麗葉未死,繼續存活下來,兩人的愛情面對現實的考驗,時光的消蝕,是否仍能始終如一,初衷未改? 日本導演野田秀樹的專訪中,談及他對於一直想做《羅密歐與茱麗葉》後傳,兩個美麗的人死去後,兩家和解結束了戰爭。但是隔天呢?一星期、一個月後呢?真的從此不再有紛爭了嗎?(註1)以此作為《Q:歌舞伎之夜》編導的動機,野田秀樹將愛情「加框」置於戰爭的襯底,用來呈現人類戰爭的輪迴,絕不會因一椿戀人的悲劇而終止,隨時隨地都會因慾念、仇恨、貪婪而烽火再起,戰鬥蔓延。戰爭的議題有其普遍性,亦可延伸至現當代,無論是二戰後蘇聯移送日本關東軍的戰俘,到西伯里亞苦役勞動,饑寒交迫、客死他鄉;到現今烏克蘭戰爭,俄羅斯與烏克蘭成千上萬的士兵與平民彼此殺戮戰死。戰爭更具備其象徵性,作為灰飛煙滅時代的意象,唯一碩果僅存、永遠不變的就是愛情。就像是Queen皇后合唱團所唱〈Love of my Life〉,如此末世警示紛擾崩壞的世界裡,唯有愛才有了生存的意義。 《Q:歌舞伎之夜》將莎士比亞《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架構,移轉到日本12世紀末期,平安時代源賴朝與平清盛的源平合戰,由活下來的愁里愛與被流放孤島的瑯壬生,試圖回到過去,改寫原先命定的悲劇。這樣有如電影《回到未來》的情節,野田秀樹並未落入老哏,兩人並非真的穿越時空,回到過去,而是在一封空白的信紙上,由後來的愁里愛與瑯壬生跳脫出來,成為故事的敘述者,自由穿梭反覆述說,來重新面對舊有的記憶,重建過去的時光。
-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請回答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請回答當大船入港……商演浪潮下的台灣劇場現場(上)
Q7:大型商業劇場大量來台,對其他類型表演藝術及國內團隊是否產生排擠效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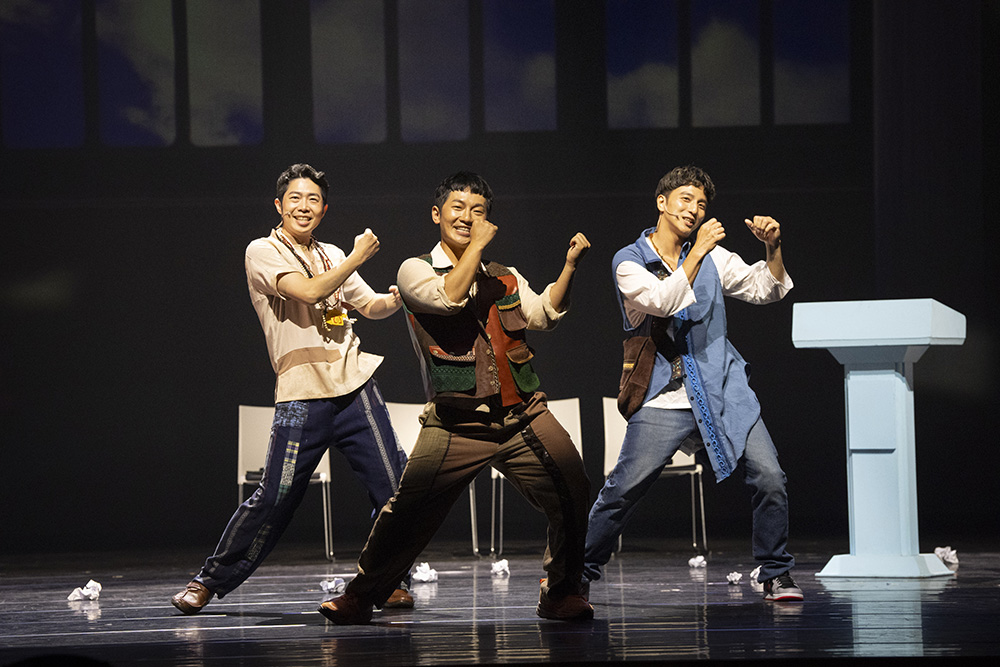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請回答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請回答當大船入港……商演浪潮下的台灣劇場現場(下)
Q7:大型商業劇場大量來台,對其他類型表演藝術及國內團隊是否產生排擠效應?
-
倫敦
劇場裡拍出新種莎劇電影《羅密歐與茱麗葉》
疫情迫使劇場工作者開始嘗試用新的媒體創作,而過去這一年也證明了網路和影像擴大了作品的受眾。大部分劇場人還是相信「現場」的不可取代性。
-
焦點專題 Focus 當樂聖遇上莎士比亞
穿越時空的共鳴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在德語地區興起的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及莎士比亞熱,身在這樣的熱潮中,貝多芬也被莎劇描述的豐富世界與人性情感所吸引,除了自身擁有多版本的莎劇全集德文譯本,還數次想送莎翁全集給心儀對象,可見他也是鐵粉之一。而他也常以莎劇場景或角色編織入樂,《科里奧蘭》、《羅密歐與茱麗葉》、《哈姆雷特》、《馬克白》、《暴風雨》等,都能在其經典中覓得蹤跡
-
企畫特輯 Special 法文音樂劇《羅密歐與茱麗葉》經典再現 初代羅密歐魅力襲台
達米安.薩格 升格人父 唱出無悔真愛
繼二○○七年、二○一六年兩度來台巡演後,今年五月,重新打造、全新製作的經典法文音樂劇《羅密歐與茱麗葉》將再次於國父紀念館登場,這次最令劇迷驚喜的,當屬初代羅密歐達米安.薩格的強勢回歸。相較於首版演出時的青春無敵,現在已卅六歲的達米安.薩格已經升格人父,「現在的我,終於知道什麼是『真愛』了。」他說,「作為一個丈夫、一個父親,在這麼多年之後,我可以驕傲地表示,我切身了解《羅密歐與茱麗葉》所說的真愛是什麼。」
-
企畫特輯 Special
羅密歐與茱麗葉 永恆之愛
二○○七年首度來台,音樂劇《羅密歐與茱麗葉》在台灣掀起一股法式音樂劇風潮,多首劇中歌曲〈愛吧〉與〈世界之王〉等也成為音樂劇迷的心頭至愛。暌違台灣近十年,這齣法文經典音樂劇將再度造訪,以新穎的演員組合,讓台灣觀眾在法式香頌與精湛歌藝演技中,重溫莎翁筆下的永恆之愛!
-
特別企畫 Feature
永恆之愛 何須長久 《羅密歐與茱麗葉》 Romeo & Juliet
「姓氏本無意義, 我們所稱的玫瑰,換個名字還是一樣芳香。」 身為古今中外最家喻戶曉的情侶檔之一,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戀愛有許多經典的橋段,讓你我都非常熟悉:石破天驚的一見鍾情、月黑風高的樓台私會、橫刀奪愛的癡心絕對、不被允許的狂熱愛戀、陰錯陽差的致命誤會在愛情這朵玫瑰面前,血緣家族、毒藥死神都不具意義。 這個四百多年前的古老文本,匯聚了所有通俗愛情劇的元素,不僅在劇場,也延伸至電影、舞蹈才華洋溢的創作者們把玩這些莎翁留下的元素,一再淘洗愛情的純度。 英國皇家芭蕾舞團遠渡重洋,帶來編舞家麥克米倫的全本舞劇,探勘角色內裡,不只探索年輕男女瘋狂熱戀,也逼視少女茱麗葉在這堂戀愛課中的成長。本刊除了專訪新上任的藝術總監凱文.歐海爾與擔綱演出男女主角的四名舞者外,也深入莎翁的愛情觀,在浦羅柯菲夫的音樂響起之前,且讓我們看各領域創作者如何對《羅密歐與茱麗葉》提出嶄新詮釋。
-
特別企畫 Feature
情若真 不必相見恨晚
莎士比亞的作品跨越空間與時間,雅俗共賞,除了四大悲劇外,「愛情」也是他作品的重要元素。有什麼比起包藏著死亡威脅的愛更教人醒腦的?莎翁透過戲劇媒材興風作浪的悲歡離合,無不是希望深化現實生活中的人性尊嚴,光輝文藝復興「以人為本」的思想,從悲劇宿命中淬煉出最直最真的愛。於是,只要曾經擁有,何必一生一世?
-
特別企畫 Feature
兩大家族人物關係圖
-
特別企畫 Feature 戲劇篇
保留原著框架 大玩形式讓你溫故知新
改編《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戲劇,也許轉換時空、語言,但基本上仍然是對偉大愛情的歌頌,以劇中設定家族的對立製造了衝突的根本,一波三折的陰錯陽差,加強了戲劇的張力,用青春的生命去衝撞封建的體制,是這個悲劇中最大的衝擊,幾乎所有的改編都掌握的這些原則,各自發展出其變形。
-
特別企畫 Feature 電影篇
從寶萊塢到僵屍片 電影史中的不朽之愛
根據統計,取材或改編自《羅密歐與茱麗葉》的電影,起碼也有一百部之多。《殉情記》的經典版本有一九五四年雷納多.卡斯特拉尼版,及一九六七年柴菲雷里重拍版。甚至形式上從動畫玩到寶萊塢,甚至變成了好萊塢的僵屍片,兩大家族間的隔閡,玩到人鬼殊途的境界,電影對於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改編,令人嘆為觀止,同時也延活化與延續了莎士比亞的經典,歷久而不衰!
-
特別企畫 Feature 舞蹈篇
「戲劇化芭蕾」扣人心弦 精緻舞劇傳世不衰
《羅密歐與茱麗葉》改編成歌劇或電影都極為成功,但要創作成舞劇則有相當難度。編舞家拉孚洛夫斯基與音樂家浦羅柯菲夫攜手合作的版本,攀上蘇聯時期「戲劇化芭蕾」的創作顛峰。而這次來台演出的麥克米倫版更是舉世公認的傑出舞作。這一切視覺上形象化的描摹,加上聽覺的深刻幫襯,讓舞劇《羅密歐與茱麗葉》永垂不朽。
-
特別企畫 Feature 芭蕾編舞家
麥克米倫 凝視現實的眼睛 以舞蹈回應時代
終其一生,這位被稱為「激情詩人」的編舞家都戮力拆解芭蕾語彙,將這個高雅殿堂的藝術推往寫實、社會性的方向,不可避免地招來了正反評價。反對者認為芭蕾因講究規矩法則,天生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度;支持者讚揚他的芭蕾不只是童話故事的藝術,而如實地刻畫了人性的脆弱,勾勒出時代的面貌。
-
特別企畫 Feature 專訪皇家芭蕾舞團四位舞星
人生閱歷豐富舞作生命 全身散發耀眼光芒
二○一一年曾經來台,帶來古典與現代芭蕾作品的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當時演出引起熱烈回響。二○一四年再次訪台,帶來古典芭蕾的經典名作《羅密歐與茱麗葉》,團內菁英舞者盡出,特別令人期待。本篇特別介紹這次來台的四位重要舞者他們的舞蹈歷程。
-
企畫特輯 Special 當莎士比亞遇見現代法國新舞蹈浪潮
羅密歐與茱麗葉 Roméo et Juliette
坐落於瑞士日內瓦新廣場(Place Neuve)的日內瓦大歌劇院(Grand Thtre de Genve),與日內瓦音樂院、維多莉亞音樂廳(Vitoria Hall)、拉特美術館(Muse Rath)毗鄰而居,旁邊更有喀爾文創辦的日內瓦學院(現為日內瓦大學),是日內瓦舊城區的重要文化勝地。 日內瓦大歌劇院 早在一七六六年,日內瓦就擁有一座三層、約八百人席次的歌劇院(Thtre de Rosimond),然而劇院短短營業兩年就毀於祝融;一七八三年在新廣場蓋起了另一棟歌劇院,因此被稱為新劇院(Thtre de Neuve),然而隨著時代演進,狹小的新劇院舞台已漸不符合演出需求,耗時近十年的徵稿、募款與施工後,新劇院被拆除,在原址新建的日內瓦大歌劇院(Grand Theatre de Genve)終於在一八七九年開幕,以巴黎歌劇院為範本,採用第二帝國建築風格,內部裝潢金碧輝煌,為歐洲最大、最豪華的歌劇院之一。 浴火重生與芭蕾舞團的誕生 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當劇組人員正在準備華格納歌劇《女武神》第三幕的場景,一場大火意外摧毀了大半個劇院;在劇院關閉七年後,整修工作終於開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日內瓦大歌劇院重新開幕,演出法文版的威爾第歌劇《唐卡羅》;在歌劇院重新開幕之際,劇院也組織了駐院的職業芭蕾舞團,請來了世界知名芭蕾女伶、法國芭蕾舞團(Le Ballet de France)的創辦人嘉寧・夏哈(Janine Charrat)擔任藝術總監,之後曾帶領過舞團的世界級藝術家,還包括蘇黎世芭蕾舞團藝術總監派翠西亞.娜麗(Patricia Neary)、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聖馬丁劇院芭蕾舞團藝術總監奧斯卡.阿萊茲(Oscar Ariz)、加拿大蒙特婁大劇院芭蕾舞團藝術總監潘科夫(Gradimir Pankov)等,而現代芭蕾舞之父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於一九七○至七八年亦曾受邀擔任藝術顧問。在他們的帶領下,舞團以簡潔俐落的現代與新古典芭蕾風格著稱,網羅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舞
-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特別企畫(二) Feature癡戀迷戀熱戀 一場盲目遊戲
本文分析的三個劇本,乃是走出《羅密歐與茱麗葉》那莽撞的少年熱情之後,一般青年男女都可能經歷的「純愛物語」。莎士比亞以最世故的眼光,為我們剖析愛情的澄澈樣貌,於是也在沒有其他雜質的情況下,呈現了他心目中的「愛的本質」:一場不可靠的遊戲,但是,值得全力以赴。
-
 藝視窗 News
藝視窗 News藝術+科技 怎麼玩? 2007台北數位藝術節「Openplay」
【台灣】 藝術+科技 怎麼玩? 2007台北數位藝術節「Openplay」 當藝術碰上科技,會有多好玩?2007台北數位藝術節將要帶來一場結合「藝術」與「科技」的新媒體慶典!11月23日至12月2日以「玩開 Openplay」為主題策劃了國際邀請展、數位藝術作品表演、藝術創作論壇、台北數位藝術獎四大活動,展演最流行、最hot的數位藝術新趨勢。參展藝術 家和作品包括紐約塗鴉研究實驗室(Graffiti Research Lab)的《雷射塗鴉》、西班牙龐部法布拉大學「互動音訊」團隊的《互動音樂桌》、日本東京大學的阿法羅.卡西那立(Alvaro Cassinelli)的作品《時間投影機》、加拿大團隊拉斐爾.迪安哲亞、麥斯.狄恩,以及麥特.唐納文合作的《電動椅》,倫敦的隨機國際 (Random International)的《光之滾刷》以及華倫蒂娜.芙斯科(Valentina Vuksic)的《哈迪斯可》。詳見網站:http://www.dac.tw/daf07。(廖俊逞) 文建會2007舞躍大地舞蹈創作比賽即將決選 睽違兩年的「舞躍大地舞蹈創作比賽」,今年在文建會主委翁金珠的支持及中華民國舞蹈學會理事長賴秀峰奔走下,終於恢復辦理。本屆比賽類別僅有「藝術創作 類」,取消原有的「全民舞蹈類」,且該舞蹈創作必須是從未正式發表過的作品。初選日期為10月30、31日,初選入圍的三十個作品,先頒發新台幣一萬元獎 勵金,並將於11月17、18日假台北市社會教育館城市舞台舉行決選,將選出八個作品,得獎作品將於12月2日、8日分別在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文中心演藝 廳及國立台灣交響樂團中興堂巡迴演出,歡迎索票入場。(周倩漪) 【國際】 國際劇評人協會泰莉獎候選名單出爐 隸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劇評人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Cr
-
特別企畫 Feature
創作者說話 音樂劇當橋樑 傳達「愛」與「包容」
被譽為法國「韋伯」的傑哈.皮斯葛維克(Grard Presgurvic),今年四月帶著法國流行音樂劇《羅密歐與茱麗葉》來台演出。這齣首演於二○○一年,改編自英國文豪莎士比亞的經典,在這位出身流行樂壇的作曲家打造下,成為一齣橫跨古典樂、現代搖滾以及工業舞曲的流行音樂劇,也為法式音樂劇樹立新指標。究竟,流行音樂元素為何形成法式音樂劇的重要精神?法國音樂劇和百老匯音樂劇又有何不同?在本刊特約採訪黃楓皓的專訪中,我們請傑哈.皮斯葛維克現身說法。


















